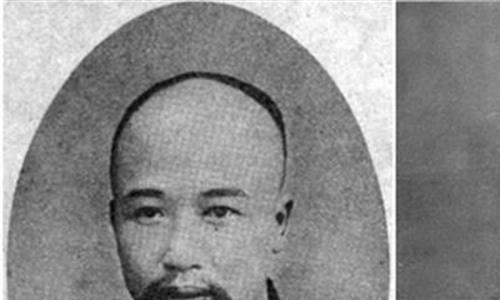俞樾之子 发生在章太炎与俞樾之间的“谢本师”事件
因什么而“谢”,不仅仅是品位,还关乎人格。
传统中国人比较尊敬老师。宋时,杨时与朋友游酢有次去见理学大师程颐,碰到程颐闲目养神,他与游酢侍立不去。程颐发现他们时,门外的雪已下了一尺深。这就是著名的程门立雪的故事。然而,老师与学生毕竟是两种生命个体,有时难免发生思想上的冲突。当矛盾无可调和,也就会出现“谢本师”现象。
“谢本师”中的“谢”,不是“感谢”,而是“谢绝”、“辞谢”的意思,说得痛快一点,其实就是要跟老师决裂,不再承认自己是某人的门生。
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谢本师”事件发生在章太炎与俞樾之间。1890年,时年21岁的章太炎到杭州诂经精舍受业,章太炎的业师是诂经精舍山长俞樾。俞樾是清代著名朴学大师,学问极其渊博,他非常欣赏章太炎的学识和才华,曾将章太炎在诂经精舍所作的几十篇“课艺”收入《诂经精舍课艺》。
然而,俞樾毕竟是一个深受正统意识形态影响的老先生,他对章太炎出校之后结交维新人物、倡言革命、剪掉辫子等举动极为不满。1901年,章太炎去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拜访住在苏州曲园的俞樾,俞樾声色俱厉,对章的行为大加指责。
这一点,章太炎在《谢本师》一文中有详细记载:“复谒先生,先生遂曰:‘闻尔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
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对俞樾的指责,章太炎很不服气,当即反驳说:“弟子以治经侍先生,而今之经学,渊源在顾炎武,顾公为此,不正是要使人们推寻国性,明白汉、虏分别的吗?”意思是,他的反满意识符合经学精神。
口头反驳还觉得窝囊,章太炎又写下《谢本师》一文,宣布离开师门。不过,此事发生后,两人并未真的断绝师生关系。
俞樾还是把章太炎看作门生,1901年8月,以《秋怀》四首索和,章太炎也“如命和之”,表示要将以前的不快“相忘于江湖”。1907年俞樾去世,章太炎作《俞先生传》,虽然文章中不乏微词,整个基调却充满敬意。
章太炎寓居上海期间,有次专程赴苏州凭吊俞樾故居。看到大厅中一幅写着“春在堂”的横额,认出是先师俞樾的遗墨,立即命同行的陈存仁点起香烛,行三跪九叩之礼。走到左厢房,章太炎辩认出这是他旧时的读书处,请房主拿出纸笔留字,房主只有笔墨而无纸张,章太炎在墙上留了两首诗,黯然而别。
20世纪40年代,沈启无也有过一次“谢本师”的举动。刘宜庆《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介绍:沈启无是周作人的学生,曾与俞平伯、废名、江绍原并称“周门四大弟子”,此人最初对周作人亦步亦趋,周作人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一职,沈启无担任伪北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兼图书馆主任,但沈启无觉得周作人给自己安排的官职太小,对周深怀不满。
1943年8月,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在“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发言,称周作人是“反动的老作家”,只会“玩玩无聊的小品,不与时代合拍”,应该对他作“无保留的激烈斗争”,沈启无以“华北代表”的身份也参加了这次在日本举行的会议,回国后,他以童陀的笔名,在《文笔》周刊创刊号上发表文章,观点与片冈铁兵一模一样。
片冈铁兵对中国文学并不了解,周作人觉得他的观点很奇怪,现在看了沈启无的文章,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奥秘。周作人一怒之下发表《破门声明》,将沈启无逐出门下。沈启无也不甘示弱,在《中国文学》(1944年5月20日)发表诗歌《你也须要安静》:“你说我改变了,是的/我不能做你的梦,正如/你不能懂得别人的伤痛一样/是的,我是改变了/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重负/我就封闭我自己所应走的道路。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谢本师”的举动,只是没有使用“谢本师”的名义而已。此后沈周两人怨仇越结越深,各自在文章中讥讽、攻击对方。
认真观察一下上述两次“谢本师”事件,我们不难看出它们的本质区别。章太炎的“谢本师”为公不为私,所以,他不得已的“辞谢”里有对师恩的念念不忘和对老师出自内心的敬重。这样的“谢”虽然也是悲剧,但沉痛中自有一份温暖,能够得到后人充分的理解和尊敬。
而沈启无的“谢本师”却完全源于个人的私欲,而且这私欲还与他们师徒在民族大义上的失节联系在一起,因此,其“谢师”也就“谢”得鬼鬼崇崇、有气无力,完全是一场闹剧,师徒都被后人看不起。
“谢本师”本身无所谓对错,因什么而“谢”却标示着一种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