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 陈巨来与《安持人物琐忆》
《万象》杂志自一九九九年的第一卷第四期上,开始刊载陈巨来先生的《安持人物琐忆》,我接触得比较晚,新近才见到一些,感觉非常有趣,便又陆陆续续地找来拜读了其它几篇,随着陈先生从容澹定并略带嘻谑的文字,令人想见昔时书画篆刻界名人的种种风神,他们的音容笑貌宛在目前,而其间所述及的逸闻佚事,几可称作是新版的《世说新语》。
在近现代史上的上海,陈先生是典型的亭子间里的名士,他的声名斐然,多半源于他那雍容华贵、严谨工稳的篆刻技法,尤其是元朱文印,出入秦汉窥视宋唐,为乃师赵时棡称许为“篆书醇雅,刻印浑巨,元朱文为近代第一”,是赵氏最为得意之门生。先生一九零五年生于浙江平湖,原名斝,字巨来,号塙斋,别署安持老人,以“安持精舍”为书斋名。
陈巨来学篆刻,先后师从嘉兴陶惕若及鄞县赵时棡,并由赵师的绍介结识吴湖帆,相继从友朋处借得汪关《宝印斋印式》及平湖葛书征所辑《元明清三代象牙犀角印存》等印谱,潜心研索,朝夕临摹以为日课,使得印艺突飞猛进,渐臻炉火纯青之境地。
其元朱文清丽圆润、典雅精致,体貌端妍而神完气足,于是名声渐著,引来国中各大图书馆及书画名手请其刻制元朱鉴藏印,若画伯张大千、吴湖帆、溥心畬等用印,出于陈手者甚多,他生平刻印的数目据说在三万以上。
著有《安持精舍印话》二卷及《安持精舍印存》。当代印家韩天衡将陈巨来的元朱文印比拟为“俊俏生旦”,洵为的评。 《安持人物琐忆》,让我们见识了陈公除却印艺之外的文字风采,偶一读及,颇有生面别开之感。
缘于处在书画场中,他所交接的也多是彼时圈中的名公巨卿,内中红颜也不乏其人,譬如张大千、吴待秋、冯超然、周炼霞、庞左玉、陈小翠以及袁寒云等四大票友、冒效鲁等十大狂人诸位。
“琐忆”中所谈及的多是人家的日常琐碎事体,诸如周炼霞行为不羁自云有面首十人、庞左玉气量偏狭好吃醋、陈小翠作诗喜抄古人旧句、张大千待友至厚却极为好色等等,像描画周炼霞的一段就十分有趣:“她有名句至多,有一词中有二句云:‘但使两心相印,无灯无月何妨。
’李祖韩特嘱大千与郑午昌二人各绘春画二段,合装成一手卷,其引首即请她写此二句,她欣然书之。自吴(吴湖帆)周(周炼霞)相合后,吴词大半得她润色,周画却大大进步。
她画鸳鸯,绝妙绝妙。尝与吴合作,吴画重台蓬密叶下,周画二鸟交颈游泳其间,均四尺整幅。” 以上内容属于琐屑不堪论的范畴,陈先生喋喋地说来,有点像唠叨不已的男人婆,看得多了,总难免嫌他太罗嗦饶舌,但这些事情毕竟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光阴的流转而越发显得有韵味,我等晚辈读来,真有些“闻听白头宫女细说天宝遗事”的感觉,不禁感慨今夕何夕了。
陈先生作文的手法,可称独树一帜。他毕竟是老辈人物,善谈掌故、言辞幽默,古雅之文风时可得见,不过对于文章法式似乎并不讲究,多不假思索信手写来,每每是文白夹杂雅俗互见,文句结尾喜用“了”字,俚词俗语在文中也间或有之,是见情见性的率真之作。
据见到过“琐忆”手稿本的周黎庵先生说,《安持人物琐忆》全文均为蝇头小字,不但通篇没有标点、没有划分段落,连最起码的眉目——文章标题也阙如,最终有劳编者为之附加。
陈先生的这一做派,可谓空前绝后了。此外,在“琐忆”中,陈氏乐于挖掘彼时男女间的风流韵事,并以之为消遣的谈资笑料,给人的感觉像个老顽童,可见老辈风流。
比如《记螺川事》中,谈及女主人公周炼霞泼辣不经之事,刻画其人有若河东吼狮,颟顸霸道,以及与诸多男士之感情纠葛,读后当为之一笑。
在陈巨来所记的十大狂人中,徐邦达先生为殿后者。这位现今书画鉴藏界的泰山北斗式人物,印象中时常身着一白袷长裳,执一长杖踽步行来,有若游天之云鹤,似乎神仙中人。而在陈的笔下业已摇身一变,回复到了他的青少年时期。
陈巨来记载关于他的前朝遗事颇可一读。“邦达自小即以东涂西抹,学画为乐。其表兄名孙元良,乃赵门弟子,余师弟也。故以孙之介,始认识之。时邦达只十二岁,一见余即探怀出名刺一纸,视之,徐荃,邦达也。
老三老四地与余连称久仰久仰,余为之竟瞠目不知所对了。余戏询之曰:尊名荃,与邦达,有何关系?他云:我要合黄荃与董邦达为一人呀。余云真乃雄心壮志,可嘉可嘉。但只觉好笑不已耳。”这段描绘得着实风趣,刻画出了徐邦达的少年老成和嬉笑姿态,其言语略无忌惮,可见邦达先生年少时即自视甚高矣。
想像中的陈巨来,既然所刻印章珠圆玉润、窈窕可观,则其人当是有如玉树临风、隽逸倜傥的,但据说他身材短小、面庞尖削,脸色煞白而体不胜衣,脖颈间居然没有喉结,说话的声音却高而亢,未免有些令人失望。
说句题外话,这一点似乎与遐庵叶恭绰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叶氏身材也极为短小,但他每当挥毫濡墨之际,则必书擘窠大字,力大无比也。
有人说陈巨来的行为多有怪诞不经之处,但我们见到的都是他臧否月旦别人的文字,关于他本人的言行,则少有人述及,不知是否像辜鸿铭那样古怪,如果有知情者发掘出来,一定会很好看。 解放后,陈巨来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与吴湖帆、谢稚柳、唐云、叶潞渊、贺天健、钱瘦铁、周炼霞、陈小翠等共事。
除了当行本色篆刻之外,他的书法和绘事也颇可叹赏,曾见到他所书楷书四条屏,用魏碑笔法,寓圆于方、刚健浑厚,丹青则人物、山水皆能精擅,绘制一达摩讲经图,达摩端坐枯松虬枝之上,线条历练简约,大有可观处。
在所作书画中,陈巨来常钤有一印,谓“石鹤子”,或许是他的另一个别号了。对于演剧唱戏,他亦是行家里手,于京昆二剧之戏中三昧多有体察,和当时的演艺界名流袁寒云、张伯驹、俞振飞等多有交接,这一点,在《记所见的几个名票友》中记述周详。
前几天翻看周黎庵先生所著《向晚漫笔》,《陈巨来与浙派篆刻家》一文中语及陈巨来之佚事,提到《安持人物琐忆》的最初稿本是陈公亲手交予北山翁施蛰存的,其时陈施二人一同关押牛棚之中为难友,陈惟恐来日无多,便将此稿托付北山翁,殷嘱倘有机缘一定为他出版。
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周黎庵往施蛰存处谈天,恰恰谈到陈巨来,因周黎庵当时在上海古籍社工作,施蛰存便将陈之所托转托于周。
周先生见文稿内容虽大有兴味,但恐怕出版社不愿承担,也就搁置下来。九十年代初期,辽宁《万象》创刊,向周征稿,周忆及尚有陈之《安持人物琐忆》可堪刊用,也便作了顺水人情。
陈巨来此稿,由其本人,到施蛰存,到周黎庵,到《万象》编者,过了三道关方得剞劂广布,足见其出世之不易也,可叹也夫! 《安持人物琐忆》的面世,引领我们见识了当时的种种人物形态,读罢几欲满浮一大白。
前几天有朋友询问“琐忆”是否已结集出版,他也很想购藏后细细品读。不知道可有好事者来做成这一桩好事,以便让喜好它的读者手执一卷,很过瘾地来饱饱眼福呢? 在陈巨来题赠“友声仁兄”的一组长诗中,末尾有这样的四句:“座中多半历江山,读书岂徒窥户牖。
如今惜别别如何,绿酒红灯引兴多。”诗句描摹的意境与他在“琐忆”中回想友朋的情状有契合之处,不免让人感伤。“我辈意气想感通,论交何必群居同。即今所处亦各异,随分努力皆豪雄。”如今,陈巨来已连同昔时座中的诸多好友别我们而去,斯人已去矣,后辈复登临,他高超绝伦的书画印艺当将长存于天地间,为后来者瞻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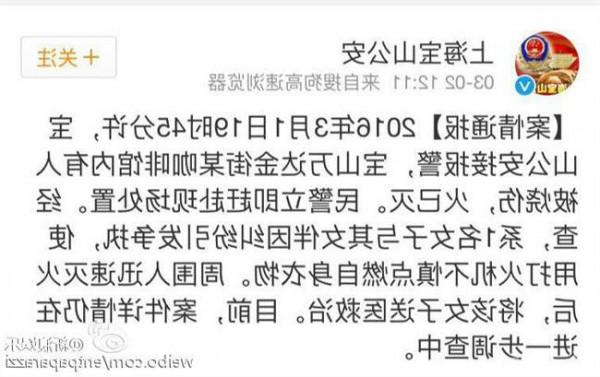


![>感动中国人物刘金宝 [2013感动中国人物事迹]2013感动中国人物罗阳事迹](https://pic.bilezu.com/upload/8/4b/84b4a50ea1289cf5226889472bdd06d5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