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索拉作品 作家刘索拉:用作品表达音乐 将音乐融入作品
“对音乐变态的迷恋让我能够不停地写故事。”刘索拉说。
20世纪80年代,当时专业音乐界对现代音乐创作的压力,成了刘索拉写作的原因。刘索拉想,要是大家听不懂,就用文字来解释解释?
没想到,音乐大家还是不懂,倒把她自己给解释成了一个作家,为什么作音乐反而成了大家的疑问。她曾经用“对等”来形容文学和音乐在生命中的比重,并且形象地比喻:“我不过是一个装着它们俩的容器。”
若你再追问刘索拉:它俩在容器里打不打架?她会爽朗大笑:亲密赛过一家。它们曾经大打出手,现在不打了。
《迷恋·咒》(作家出版社)是刘索拉继2003年《女贞汤》后首部长篇小说。小说以美国曼哈顿为背景,采用“黑色幽默”的笔法,勾勒荒诞现实中的荒诞人物与荒诞事件。《迷恋·咒》中,刘索拉将爱情、婚姻、情欲、音乐、迷恋学说打碎,重新拼贴组合,只有她能将如此世俗的人类情感讲述得如此疯狂生动,自由而不拘一格,并富有哲学探索精神。
在《迷恋·咒》一书中,描写了很多种的迷恋,对音乐的迷恋、爱情的迷恋、智慧的迷恋、自己的迷恋、身体的迷恋、异性之间的迷恋等。“Fascination(迷恋)其实是多意的,不仅仅是迷恋,还有意思是为之兴奋、不可遏制的被吸引、表示对强大诱惑力的不可抗拒感等等。
所以这个字没有什么特别不可思议的,只不过是我们不常用这种词来表达自己的状态。”刘索拉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一个修表的工人,一天到晚琢磨表,挣不了多少钱,但是每次修好一块别人的表都有一种满足感,就是对表的结构本身有一种迷恋。
多分析一下他的心理,就是他被表的结构魅力给征服了。是这种迷恋精神成全着一个修表匠的技巧、一个画家的造诣、一个音乐家的修养、一个先知的智慧等等。
在《迷恋·咒》中,刘索拉赋予一些音乐理念新的诠释。她认为如果只允许某一种音乐存在,就等于把音乐的生命树杈都砍了,让它半残废地活着。“如果谁老是逼着你变得更‘正常’,那才是在杀你。川菜好吃就是因为全是不谐和的调料,偏激得有味道,但是哪天谁说因为川菜不健康,要把川菜馆子都关了,全四川的人都吃白水煮菜不放盐,那不等于要杀了全体四川人么。”
刘索拉在作品中用女主人公音音和婵不同风格的演奏展示着她对于两种艺术观的表达。音音的音乐中“杀人的能量”只供“自杀”;婵的音乐却能“杀死”他人。刘索拉认为,音音这个角色的创作状态,更接近艺术“原创”状态。
既音乐与思想过程有紧密联系。如果用现代音乐或者爵士音乐为例,当某种不合常规的声音出现在人们的耳朵里,常常被保守人类称为对音乐的威胁和挑战。但其实这些声音的产生,更是创作者本人对自己的挑战,由于作曲家或演奏家出于对某种声音的追求,不惜搭上一生性命来寻求某种对于他们来说的艺术完美性。这种例子可以在很多艺术历史中看到。
画家、作家的例子也很多。婵这个角色,更是某种主流意识的体现。无论她怎么表面看起来很有艺术风格,但内心是很主流的,艺术对于她来说是装饰,是她给自己的身份定位,并不是她真正的灵魂。有人认为这个角色是消极的,但仔细读,这个角色比谁都积极。
她不仅用别人的音乐为自己找到定位,还知道用时尚来包装形象,知道评论和传记的重要,必要时刻还能把人置于死地。可悲的是,这类人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比比皆是。她演唱什么音乐其实不重要,因为仔细读去,你会发现,首先那音乐不是她的,其次,她对死亡的眷恋也不是真的,否则她不会那么真的热爱她自己的传记。
用作品表达音乐,或者将音乐融入作品,是刘索拉一贯的笔法。在刘索拉既有的作品中,小说中均有很多音乐的元素,而在《迷恋·咒》中,还有《生命树》作为人体艺术的表现。对此,刘索拉当然也不无用意。因为生命树的说法,在中国的道教、东方佛教以及古代埃及神话,基督教、犹太教等等都存在。
简单地用中国说法,就是人身体中间的中脉。中脉像是大树干,各种脉络交接,就是树杈。这棵大树主宰着人的性命,甚至欲望。在小说里,由于是音音与塞澳的作品,所以更加意味一种生命能量的结合。
有人称刘索拉是一位天才作家,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引领先锋与时尚的作派。其实,无论在结构和语言上,她一直不停地尝试,写作时做种种的试验。很慢地摸索写作风格,看很多书,学习很多别人的经验,给自己指定不同语言和风格目标。
在《迷恋·咒》的写作中,刘索拉觉得自己达到某种随心所欲的状态,她看到自己的小说人物们在眼前自然地走来走去,自己则跟着他们,看着他们,听着他们,也听着自己,然后纪录下来。不但写作过程轻松顺利,写完之后周围的朋友看完都觉得轻松。好像刘索拉的语言和故事对于大家都没有压力了。
20世纪80年代,《你别无选择》的发表使刘索拉进入写作,并使她变成了一种当时的先锋派符号化人物。如果说当年人们不能解释某种事件的时候,只能用“先锋”一词还情有可原,那么如果今天还用这个词来套用艺术作品,就显得套用者可怜了。一直生活在音乐和文学的两栖思维状态中的刘索拉,其实更多的时间是在音乐上,对于文学,是凭着对语言的直觉。
“因为文学可以想到就写在纸上,更容易直接体现出来;而音乐更难体现,所以大家对我的文学就更容易接触到。写音符,要变成声音出来,即便我可以即兴演唱或演奏,不公开演出或者录音别人也听不到,这中间就多了很多的创作过程。
这就是作音乐的难处也是魅力所在。”刘索拉说,一部大型乐队作品就是一部小说,但是小说可以在家里写完发表,马上被读者看见,乐队作品则要经过乐谱,乐队排练,然后演出;演出完了,要录音,或者不录音。最终到了听众耳朵里,听者要自己会思索,因为音符不具体给人故事,不象看小说,作者把故事全讲清楚了。
所以音乐和习惯把话说清楚的思维方式是有距离的。对她来说,作音乐和同时写文字,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功利性没有什么关系。比如,文学发布会后她马上进录音棚,琢磨怎么合成别人演奏的录音,她可以来回听着几个音来抛光演奏者的音色,好比一个钟表匠,没有什么更深刻的意义,就是因为高音太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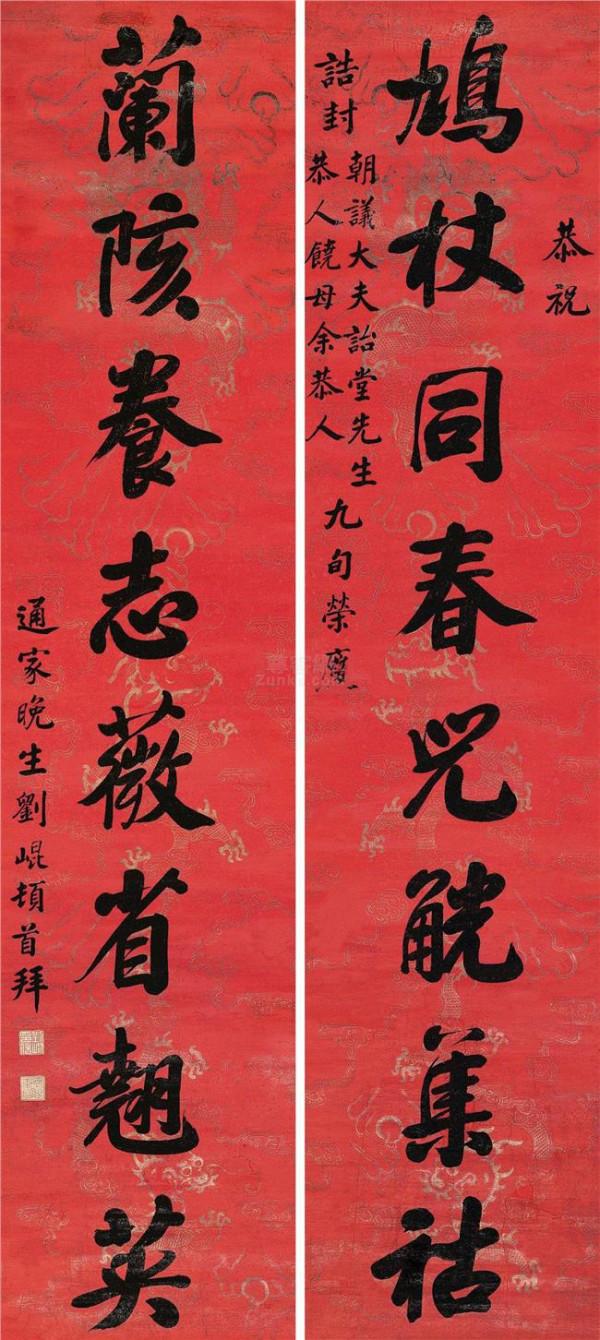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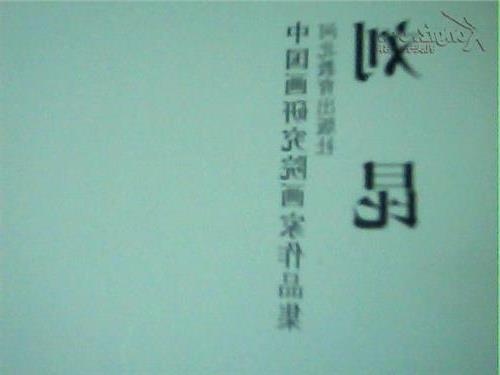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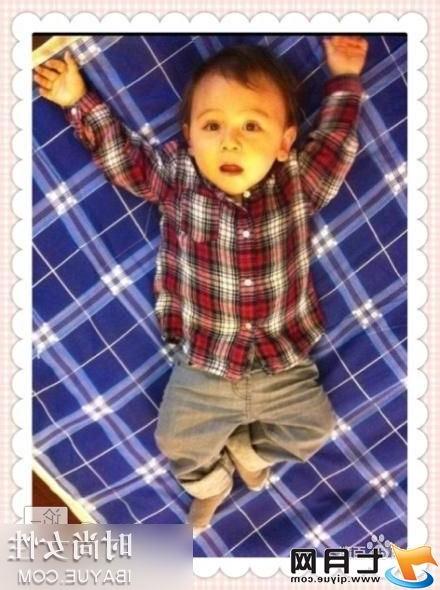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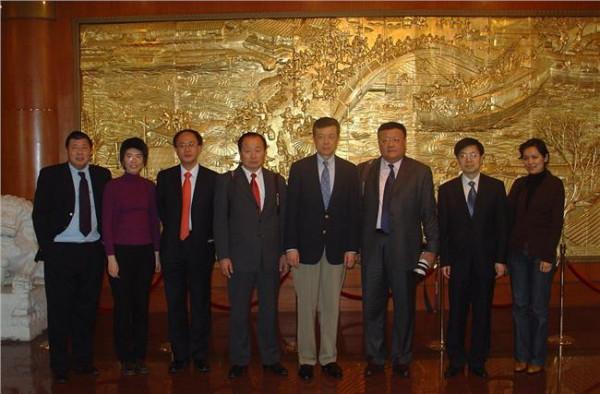





![>刘西拉的妻子 [上海教育]上海交大刘西拉教授:做名赤诚的教育“老兵”](https://pic.bilezu.com/upload/2/8b/28ba7ecbefbe7252fcd596d903899472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