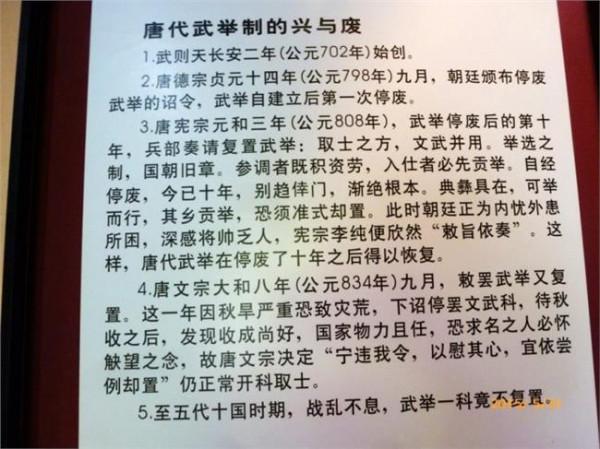董玥许纪霖 许纪霖:近代中国双城记中的知识分子
近代中国一南一北双城,为新崛起的知识分子展现了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空间,历史所留下的不同城市传统至今成为京沪两地文化人无法逾越的“围城”。
近代中国读书人的活动空间,有一个不断城市化的过程。随着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的崛起,大量的新式学堂在城市出现,无论要接受新式教育,还是谋求新的发展空间,士绅都不得不往城市迁移。知识精英的城居化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
传统士绅之所以有力量,乃是扎根于土地,与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有着密切的血肉联系。晚清以后,精英大量城居化,移居城市以后的知识精英,逐渐与农村发生了文化、心理和实体上的疏离。那么,这些城市化的近代知识分子,与城市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南北迥异的地方社会
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是不平衡的,地方差异、南北差异之大,形成了极大的落差。上海与北京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两个最大的都市,一南一北,互为“他者”,无论是城市形态、社会分层,还是城市景观、文化风格,都呈现出鲜明的对比。同样,从晚清到民国,两个城市的知识分子的内部构成不同,因而与城市社会的关系也迥然有异。
这两个城市的比较,一个世纪以来永远是人们乐此不疲的话题。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如此说:
上海与北京,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各有其挟持之具,恒处对峙地位。惟北京为吾国首都者五六百年,故根深蒂固,历史上已取得政治资格……抑专制之世代,有政治而不认有社会,盖视社会为政治卵翼品,不使政治中心点之外,复发现第二有势力之地点,防其不利于政治也。
惟上海之所以得成为社会之中心点,其始也,因天然之地理,为外人涎羡。其继也,又因外人经营之有效,中经吾国太平战事,而工商乃流寓,乃相率而集此。而其最大原因,足以确立社会中心点之基础,与政治中心点之北京有并峙之资格者,则实以租界为国内政令不及之故。
在不少幅员辽阔或者文化丰富的国家内部,往往有两个中心:美国有纽约和洛杉矶,俄国有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德国有柏林和法兰克福,英国有伦敦和爱丁堡,澳大利亚有悉尼和墨尔本,日本有东京和京都。而在中国,北京是传统的政治中心,上海则是晚清之后崛起的社会中心,分别成为近代中国南北政治与文化的象征。
作为一个有着七百多年历史的帝都,除了明朝之初和国民党南京政府两段短暂时期,元朝至今的北京城,一直是在皇城根下。北京的政治,发达的不是地方政治,而是帝国政治、国家政治。
天子脚下,地方即国家,国家即地方,地方被笼罩在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作为一个政治首都,北京城到晚清之后,城市商业有很大的发展,却缺乏近代的实业和金融业(近代北方的金融与实业中心在天津),只是一个消费性的传统都市。因而无论是城市绅商、资产阶级,还是职业群体和自由职业者,与上海相比都远远不够发达。
晚清之后的北京也形成了地方社会,由士绅与商人组成,并形成了地方精英管理公共事务的有限格局,但北京并没有像上海那样有强大的地方自治势力。研究近代中国绅商阶层的学者马敏发现,清末民初的地方市民社会,有两种不同的组织形态,一种是以地方自治公所为主轴,以商会为后盾,进而联络各新式社团、公司、商界,以上海为主要类型;另一种是以地方商会为中枢,依靠纵横交错的民间社团、公司、商界的网络而形成,苏州、天津、广州、汉口等城市皆属后一类型。
显然,拥有地方的自治机构的上海是强势的市民社会,而以商会为中枢的地方自我管理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士绅为核心的管理型公共领域”,只是到了民国时期,商人代替了绅商成为城市管理的主角而已。
北京显然是第二种类型,而且因为其社团、商家和公司比天津、汉口等工商城市不发达,因而北京的地方社会要薄弱。在1920年代,有“北京商家泰斗”美誉之称的孙学士,连任三界北京商会主席,是京城地方精英领袖,但他在全国并没有知名度。
诚如1920年代北京城市的研究者史大卫所指出的那样:在北京,强有力的政权所控制的是一个虚弱而柔顺的社会,“北京的地方精英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中扮演着政治调适者的角色,他们既没有虚弱到需要习惯性地卑躬屈膝来满足上层精英的要求,也没能强大到将挑战权威的举措上升到要求独立地方自治的程度”。
而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社会中心,是一个具有全球化背景的近代大都市,不仅具有强大的资产阶级,而且在城市的变迁之中发展出丰富发达的社会网络。更重要的是,从晚清开始,上海作为一个有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通商口岸,控制城市的政治权力一直处于竞争性的多元状态。
无论是英美、法国和日本的外来列强,还是清廷或后继的各路北洋军阀,谁都无法完全控制这个东方第一大都会。在权力竞争的空隙之中,反而为地方社会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可能性,也留下了地方自治的发展空间。
清末民初的中国,同时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趋势,一个是近代国家权力向基层的渗透和扩张,另一个是地方绅权为核心的“封建”势力的崛起。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之间既有互动,又有冲突,呈现出复杂的权力交错面貌。
以清末开始的地方自治为例,就具有双重的性质,一方面国家权力以地方自治的名义向地方渗透,另一方面地方名流借助地方自治试图获得相对于国家的地方公共事务的自主性。上海史研究者李天纲引用梁启超的话指出,有两种不同的地方自治,一种是政府助长者,另一种是自然发达者;近代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属于第一种,而上海属于第二种。
由于全国一半以上的贸易、关税、工商业资本、金融存款、银行总部和交通工具都集中在此,上海俨然成为“经济中央”,非各种政治势力能独自驾驭,日益强大的社会生长出地方自治的要求。
上海的地方自治,其欲望和力量并非来自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而是从以强大的经济力、文化力和关系网络为后盾的城市社会中生长出来,于是便具有持久的冲动和爆发力。
从1900年到1937年时期的上海地方自治,经历了两上两下的波折。第一波地方自治高潮从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05-1909)到自治公所(1909-1911)、市政厅(1911-1914),以李平书为首的上海地方士绅通过这些前后相继的自治结构掌控了上海华界的地方公共事务,并且在辛亥革命年间的上海光复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1914到1923年间,因为地方自治受到袁世凯及其北洋政府的打压相对衰落,其间的工巡捐局虽无自治机构之名,却承担了若干地方自治的功能。
第二波地方自治的高潮始于1923年上海市公所的成立,与全国的联省自治运动恰成呼应,一直到1927年国民党统治上海结束。上海特别市建立之后,南京政府以“一党治国”的理念加强对上海的直接控制和管理,自下而上的上海地方自治运动遂告挫折。
然而,即便在1914-1923年和1927-1937年这两个低潮时期,虽然不复有法定的地方自治机构,但下节将看到,上海各界的地方势力依然在商人阶级和知识阶级领导之下,通过商会、教育会以及其他城市的“权力文化网络”,力图表现出独立于中央权力的城市意志,并且在北洋时期数度挑战北京政府的中央权威。
一元化的上海与二元化的北京
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究竟如何?他们是游离于城市“权力的文化网络”之外,还是镶嵌于其中?简单地说,近代北京是一个知识分子与地方社会相互隔绝的二元化城市,而近代上海则是文化精英与地方社会密切互动的一元化都会。
北京与上海,不仅在于一个为政治中心,另一个是社会中心,而且在近代历史之中,同时又一个是学术中心,另一个是文化中心,这便形成了两地知识分子与城市社会的不同距离。京城从历史上来看一直是官僚士大夫的栖身之地,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国立大学以及教会大学云集北京,形成了全国公认的学术中心。
京城知识分子的主体是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立大学任教的学者专家。这些国家精英继承了帝国士大夫的精神传统,他们所关怀的除了专业趣味之外,便是国家与天下大事,而与地方事务基本无涉。
董玥的研究发现,京城知识分子即使是观察自己所生活的城市,通常也从国家视角出发,所欣赏的多与帝都有关的建筑景观、皇家园林,如故宫、天坛、颐和园等。
京城的知识分子有强烈的抱团意识,但这些文人团体通常不是为国家法律所承认的正式职业社团,而是带有传统士大夫色彩的非正式交往社群,在“五四”时期有领导启蒙运动的《新青年》群体,启蒙阵营分裂之后,京城知识界分化成胡适、丁文江为首的《努力周报》群体、以周氏兄弟为领袖的《语丝》派和欧美海归博士为主的《现代评论》派。
到1930年代,《努力周报》群体扩大为《独立评论》派,从《语丝》中分化出来的本土化京派文人组成奉周作人为精神领袖的《骆驼草》群体,而另一批留洋归来的京派作家以林徽因的“太太客厅”为中心,形成了前有《学文》杂志、后有《文学杂志》的同人圈子。
由于京城的报业和出版业远远比不上上海发达,故这些京城知识分子皆以非商业化的同人刊物为中心,京派文学的代表《文学杂志》竟然还是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
民国时期的北京知识分子与京城的地方社会基本绝缘,与当地的士绅、商人等地方社会网络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他们都是国家级学术精英,甚至在国际上著名,生活在国立大学的象牙塔中,自成一个文化王国。与京城知识分子关系最密切的,当属天津《大公报》。
《大公报》虽然发源于天津,却是一张全国性大报,其关心的主要议题并非地方事务,乃是国家命运和世界风云,于是与京城的知识分子一拍即合。《大公报》很有影响的副刊“星期论文”和“文艺副刊”的作者,大都来自于上述北京知识分子各大圈子。
“星期论文”与胡适为首的北平自由派走得很近,而“文艺副刊”仰仗的则是出没于“太太客厅”的京派作家。在1930年代的北平(北京),他们形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舆论的公共领域”和“文学的公共领域”。
但北京的公共领域与以《申报》为代表的上海公共领域不同,其背后缺乏资产阶级为核心的市民社会支持,散发着纯粹的知识分子气息。这些以国立大学为背景、掌控了全国知识话语权和舆论主导权的大知识分子,因为与国家权力(南京政府)、国际资本(由庚子赔款为来源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和全国性大报(《大公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更具有古代士大夫的清议色彩,其与近代的城市社会是游离的,与城市资产阶级更是隔绝的。
而在近代市民阶层面前,他们依然保持着传统士大夫的矜持、清高和傲慢。
对于京城知识分子与市民阶层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董玥有如此精妙的分析:
在北京,并不是很多人都能享有像知识分子那样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占据着社会等级中的高阶,社交圈里都是和他们认可、欣赏同样的社会地位象征的学者名流。这样一种环境给他们以安全感,让他们觉得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他们不断地批评政府,这说明他们相信自己的学术知识工作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如果在上海他们会有做“他者”的感觉,在北京他们则是主人,而北京的本地人才是他们眼中的“他者”。
北京城中的“新知识分子”并不是像本雅明眼中的波德莱尔那样的漫游者或城市闲人。
他们不是人群中的诗人,他们甚至根本就不在人群中。他们与本地人的接触止步于拉着他们足不沾泥地穿街过巷的洋车夫之间往往不大顺畅的沟通,他们很清楚这种隔阂的存在,但是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严重的问题。
细读北京的文化人有关北京城的文字,会发现他们的内心对这座文化古城充满了故乡般的柔情。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都于1920年代末在上海生活过,但他们不习惯上海的商业气和美轮美奂,无法融入这座东方的巴黎,始终有疏离感,是城市的边缘人和漫游者,于是在1930年代初纷纷回到北平。
只有在北平,在北大、清华、燕京、辅仁这些象牙塔中,才不再有在上海那样的疏离感,感觉自己回到了精神的故乡。
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不会说一口京片子,但依然感觉自己是城市的主人,反而将真正的北京人视为“他者”。北京文化人与城市的联系是情感的、审美的、纯精神性的,北京城之于他们是精神的乡土,是地理化的家国。北京象征着心灵之家和中华国家。但家国之中所缺少的,恰恰是上海独有的城市认同。
相比之下,对于上海文化精英来说,上海既不是家,也非国,她就是一座现代大都会,一座有着自身肌理、血脉和灵魂的城市。近代中国的学术中心在北京,但文化中心却在上海。学术中心以大学、研究院和基金会为基础,而文化中心多的是近代的报馆、书局、商业杂志、电影业和职业教育。北京知识分子的核心是学者专家、大学教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