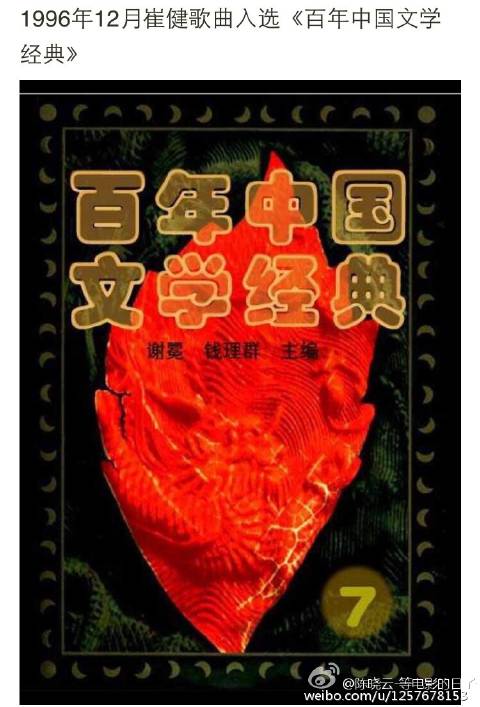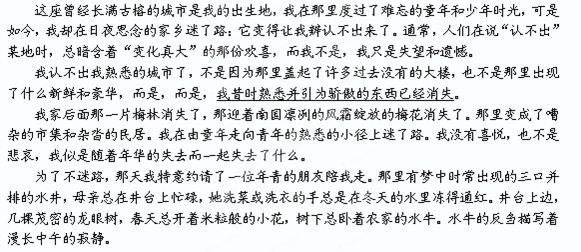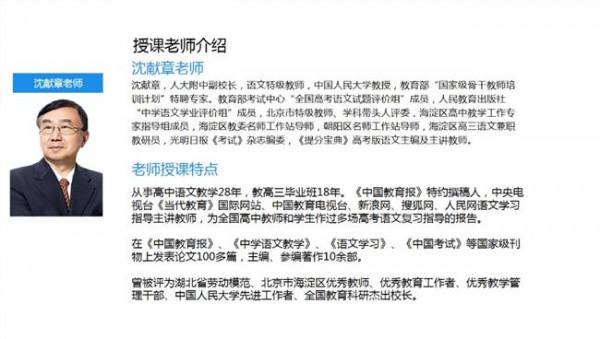谢冕把日子过成诗阅读 谢冕:把日子过成诗(图)
“尽量不要打扰我的学生吧,他们太忙。”当我提出要侧面采访他的学生时,谢冕特意叮嘱。
谢冕的学生,大多活跃在当今学术界。
学生张志忠说,谢先生尤为可贵的,是他对青年诗人的全力扶持,30余年间,他为青年诗人撰评作序,不遗余力,这在当代诗评家中可以说是为数不多。“早些年间和先生交谈,我曾经劝他,不用这样来者不拒地接待和支持每一个来访者、来信者,这样的杂事太多,沉不下心来,会妨碍做更重要的学术研究。”
“不能把青年人挡在门外啊。”那些来自远方的访客和书信,在谢冕这里都得到了热情的回响,不管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还是诗人们自己印刷的作品集,不管是有过一面之缘,还是素不相识,在他这里都不会碰壁。
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形,一位不知名的青年诗人去世,他的哥哥为了满足逝者的心愿,将其诗歌编成集子,到谢冕这里求序,他欣然允诺。
在谢冕这里,与青年诗人的交流,并无等级差序,首先是一种情感和诗性的撞击。就像鲁迅当年,为那么多的青年作家写序,称赞他们的生命热力。而被鲁迅评价过的青年作家,有许多今日已经湮没无闻,但是,文学评论毕竟不是选择“绩优股”和“潜力股”进行投资,扶植新人,推荐新作,以“新松恨不高千尺”的迫切,为新人新作推波助澜,为当下文坛留下参差错落的风景,这才是真正有见识、有热情的大家风范。
学生们常笑谢冕是“守财奴”,每次上北大取信件,总会拿一大包回家,看过后整整齐齐地摆放一旁,不舍得丢掉。“反观诸己,若不是当年先生不弃草芥,把稚拙愚钝的我收留在门下,耐心提点,对先生来说,不过是少了一个来自古城太原的弟子而已,而对我自己,人生的轨迹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改变,学术之路会走得异常艰难吧。”谢冕惜才,张志忠上学时常在先生家吃饭,受到很大关照。
“老孟”,这是谢冕对学生孟繁华的称呼,二人相识32年。多年前,在北大有个批评家周末,开始前,谢冕随意自如,谈笑风生,学生们则自在率性,书生意气,师生间的谈话海阔天空。一旦正式开始的时间到了,顿时安静,“老孟还没来?等等老孟,他说来的。”谢冕的话音刚落,孟繁华就气喘吁吁地进来,一副庄严而厚重的样子。谢冕笑着说:“老孟来了,大师来了,我们开始吧!”孟繁华朗朗大笑,算是对先生的回答。
谢冕对待学生一向宽厚温和,但也有发火之时。1992年,谢冕让孟繁华第二天陪他一起买《新青年》杂志影印版,但当天从意大利使馆来了位学习当代文学的学生,孟繁华便把先生交代的事情忘了。“先生当时很生气,教育我要对他人的事情言而有信,要有时间观念。”事后,孟繁华骑车又去买了一套杂志,从此再没爽约过。
高秀芹,谢冕最小的学生。她读博士时,正值谢冕63岁,毕业后与先生交往甚多,一些诗歌活动都会见面,她认为先生没有老过,保持了最好的活力,堪称“行走的诗人”。“他能看到学生的优点,毕业时不限定我们的论文题目,但要求学生从宏观的角度叙述细节。”
毕业后,学生们虽然在不同领域发展,但谢冕总是惦记,时不时就聚一下。在高秀芹眼中,谢冕本身就是一首诗,“与他在一起,我们都是老的,他是诗歌的孩子。他一生都在呵护着诗。”谢冕为诗歌奔走,不喜欢说不,而且都会给予最炽热的关爱。各地的诗歌活动,但凡需要他,从不推脱。
“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谢冕常开玩笑说,自己好读书,但不求甚解,“我翻得不够,到了这个岁数,应该多到图书馆看书。”
人的知识面是不断翻书翻出来的,让谢冕得意的是,他曾经读过一个面包车的书,记过大量笔记,还将感兴趣的内容装订成册,随时翻阅。因为如果不阅读作品,在新诗领域就不配有发言权。
读过许多书,但谢冕并不想写专门的文章来论述自己的观点,“我写了也没人理嘛。”话虽这样说,但他是不会去做“锦上添花”的学问的。
谢冕常常会引用诗人济慈的一句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把名字写在水上。”像他这样的人,几无占有欲,对于知识、名气、权力,甚至于“来自他者的认可”等抽象的东西,全都无欲无索。
这样一个大热天,谢冕在家里完完整整地穿戴着干净的衬衫、鞋,手腕上还戴了手表,一副要外出的样子,他坐下来之后,裤腿缩了上去,露出深蓝色袜子,脚背上有一个大洞。
谢冕在北大畅春园的家,书籍几乎占据了所有空间,另有一尊拜伦雕像。这样一来,他的房间就显得格外拥挤,外人来了总会一不小心就碰这碰那。所以,每逢送客,他都要谨慎地提醒:“小心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