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格格的真名叫什么 你童年的伙伴叫什么名字
这几天看桑格格的《小时候》看痴了,一直哈哈哈哏哏哏笑个不停(当然,动情处也会偶尔挤两滴猫尿儿)。还剩几页都舍不得看了,好像看完她我的童年就没得了(请允许我慢慢从半调子川味变回正宗大馇子味吧,哈哈),虽然童年已经离我远去好多年了。
我开始好生回忆我的童年,于是乎,我和我进行了一次采访式的问答。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你童年的伙伴叫什么名字?”。 这个问题问得太泛泛,太不专业。
可我还是堆起一鼻子褶认认真真地想了想。 由于我家住在马路边上,我妈看我看得严,但只要逮着机会我就溜出去和附近那帮娃娃们耍。
可我觉得她们一点都不好玩,动不动就“我给你告我妈去”,“我妈不让我跟你一起玩”,“你把吃我的小淘气儿吐出来”……哼,真小家子气,虽然当时我也才屁大点儿。
就这样,我跟她们就不友好了。 我哥长我四岁,跟他出去玩我妈是从来不管的,充分表示了对他的信任。
但他利用了我妈的信任带我混迹了多少次游戏厅这一“不良场所”啊!他有好几年的时光生活在姥姥家,而从我家到姥姥家以龟速步行也只要三分钟。可想而知,我俩是多么有时间成天混在一块儿呀。 姥姥家的前面就是一座山的山顶,我们都叫它“小山儿”。
小时候,小山儿上的树密密匝匝的,又粗,林下花花草草也茂。现在的小山儿不知是中了什么邪毒,瘦了几大圈,头发也稀疏了不少,面色焦黄,一点都不葱郁了。
我看到都伤心了。哇哇哇。 听大人说黄皮子夜间进到人家院子里吃鸡,白天就在小山儿的洞洞里。
我哥就带我去逮黄皮子。他说我走路动静大,吓着黄皮子了,所以才看不到它。可是我听他的动静比我还大哩。结果我至今也没见过黄皮子长什么奶奶灯样。
冬天最好玩。整个小山儿都盖了一层厚厚的白棉被。我和哥抱一大堆长长短短压扁的纸壳箱子到小山儿。为了彰显兄妹俩的团结,无论多么短的纸壳,我们都要坐在一张上,从上往下放。
在前面的一个要把握好“方向盘”,死抓纸壳边儿不撒手,所以坐在后面的经常被中途丢下,惨兮兮地看着司机像蛤蟆一样翘着两条腿扬长而去。冲到平地还要滑老远。
再拎着纸壳从旁边开辟一条雪路爬上去。如此这般一趟一趟。最后,裤兜子里,鞋窠子里全都是雪。帽子也疯丢了,手套也疯丢了。太阳落山了。我和哥就拎着残破不堪的纸壳子大鼻涕咧泻汗吧流水地回家去了。
那次我和哥在舅舅家,哥趁我卖单儿,往床上毛绒玩具狗屁股上喷了两下香水,对我说:狗放屁都是香的。我不信。
靠前一闻,果真是香的啊。转过头,用无限崇拜的眼神看着我哥:哥,你咋啥都知道呢?真厉害。我哥双手抱膀儿,鼻孔冲着天。 我哥简直太博学了,我处处都爱学他。
他就说:“跟人学,长白毛。白毛绿,吃狗屁。屁眼儿长个小机器……”我不明白了。小机器是个啥东西?难道是痔疮? 我哥也有很尿泡儿的一面。
胆子小,天黑以后就不敢上厕所了。总要我陪他。有时候我还要吓吓他。哈哈。这一点着实让我嘲笑了好久。听我妈说,我的脐带剪下来放火墙子上了,所以我才这么傻大胆儿。
我想一定比那更高,没准儿它长了翅膀飞到天上去了呢。我哥的脐带一定是被我大姨塞到灶坑里去了。哈哈。 我小时候爱攒钱,放在钱包里厚厚一沓。
面值都小小的,从一毛到五毛,偶有个把成块的。哥知道以后,就千方百计想把我这点积蓄鼓捣到手。于是,隔三岔五卖给我点小东东,要价都是五块三块的。
后来我们俩的交易模式逐渐成熟。他向我一使眼色就出去了,我则稍待片刻后揣着事先装在兜兜里的钱去我家房头儿的窄道跟他接头。凡是他卖给我的东西,我到现在都如数家珍并纪念性地保留了其中几样。一个是滴水形的“水晶石”,价值5块。
我后来知道那不过是从毛衣链上卸下来的还算光滑却浑浊的玻璃块。另一个是一种已经在这个星球上绝迹的物种遗留下的十分罕见的珍贵的化石,名字叫做“恐龙蛋”,价值15块。其实它不过是一个花色特别的卵圆形石头。
还有一个绝对国宝级珍品------一个正面刻着一位面容慈祥形象光辉的老人,并刻有如下字样:“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背面刻着中国地图的------金------牌,价值同样15块。
当时我这个不怎么灵光的脑子里只闪了一个念头,我发了。而丝毫没有质疑我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共同致富的崇高“善意”。因此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哥去游戏厅消遣的盘缠都是他妹供应着。现在看来,我哥从小就很有生意头脑嘛,为了骗他的傻妹妹是煞费苦心啊!
虽然我哥贯穿着我整个童年时期的记忆,但鉴于以上他欺诈我的行为,我还是决定:他的名字不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继续想呀想呀想,终于想到了答案。我童年的伙伴,最忠于我的伙伴,叫锤子。
对。就是那个铁头木把的锤子。 我这个人,从小就很隔路。我妈到现在都纳闷儿:人家孩子看动画片入迷,连饭都不吃。
你可好,从小就不爱看。其实我也不解。而且我也不擅长跳皮筋一类女娃娃的游戏。难道我小脑不发达从孩提时代就有所表现?那不爱看动画片是咋回事呢?莫非大脑发育也有问题?想不通啊想不通。还是说锤子吧。
别看我木头瓜子脑袋一个,但玩起锤子来可厉害着呢。什么大的,中的,小的。什么方头的,圆头的,我都鼓捣过。
锤子的功用在我的小手里发挥得那叫一淋漓尽致。拿纸壳子往板子上钉,板子往板子上钉,纸壳子往木头上钉,板子往木头上钉……只要能钉进钉子的我都钉。把它们钉在一块儿再拆开。如此反复,乐此不疲。最后这些都满足不了我寻求新鲜的小小欲望了。
于是开始往仓房的门梆和门槛上空钉。由于门是活动着的,我必须高难度地用两条小短腿儿夹住,再颤颤巍巍地钉。可能是技艺高超的缘故,几乎没有砸手的记录呢。真为我自己骄傲。对应锤面的另一端都是带豁儿的,用来起钉子。
我就这样,钉了起,起了再钉。有时候钉子弯了,就把它拔出来,拿到水泥地上砸一砸,直到砸溜直儿了再把它钉进去。经常是一把锤子一根钉子玩半天或者一天。第二天继续玩。看嘛,要不说我是个有毅力的人喃!
后来跟妈妈去单位玩,我发现了一样十分神奇的东西------腻子。黏黏糊糊的白色东东,拿腻抹子舀一小坨盖住钉子,再上下左右使劲刮哧刮哧。
钉子帽及附近凹洼处就这样瞬间与一大张板子融为一体。等腻子晾干,上油儿。最后真的连白色补丁都消失不见了。除了神奇,我简直都找不到其他词语来感叹了。
我深深地被这一套完美的“工艺”所打动。我轻轻拽了拽我妈衣角:妈,你给我拿点腻子回家呗。我妈可能觉得这是社会主义腻子,拿不得。我的小算盘就这样落空了。于是,现在每次回老房子看,仓房门槛子上依然千疮百孔,惨不忍睹。
怪谁?怪我妈。哈哈。 上小学时每年寒假学校都组织我们上街义务除雪。同学有带斧子的,有带铁锹的,有带扫帚的。
只有我,带了把锤子。我带锤子可是经过一番慎重考虑的呢。第一,斧子有刃,我怕伤到自己,更怕伤及无辜;第二,铁锹把长,拎着费劲,拖着噪音忒大;第三,扫帚枝枝叉叉,以我一小脑不发达的人容易被它绊倒,卡掉门牙多影响形象。
综于以上原因,我觉得只有锤子既携带方便又有它独到的用处。老师恨恨地瞪了我一眼:×××,你拿个牛眼珠子大的锤子是来干活的吗?老师说这话我就不乐意了。我怎么就不是来干活的了?老师你也忒没有劳动常识了!
不知道用锤子砸紧实的雪再拿斧子凿更容易除吗?再说了,你侮辱我的锤子我也就忍了,干嘛还侮辱牛啊?我从小可是坐着外公的牛车长大的。在我心里,牛眼珠子那是多么大的球球呢。忽闪忽闪的。 我对锤子简直有种无法言述的情怀。
貌似我的描述为我的童年增添了不少暴力色彩。
好吧。暴力就暴力。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想起顾城的一首诗“你推动木刨,像驾驶着独木舟,在那平滑的海上,缓缓漂流……刨花像浪花散开,消逝在海天尽头;木纹像波动的诗行,带来岁月的问候。
没有旗帜,没有金银、彩绸,但全世界的帝王,也不会比你富有。
你运载着一个天国,运载着花和梦的气球,所有纯美的童心,都是你的港口。” 木刨也是我喜欢的物件。小时候见姨夫耳朵后别着铅笔,一双勤劳的手缓缓推动着木刨,我觉得帅极了。
可是我们家没有那么多木料让我推,又要经常磨刀,那样就更暴力了。所以我依然不二心地摆弄着我的锤子。 假如我也能拥有一块紫檀,一定会把它凿成锤子,伴我左右。
那样,我就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就写到这吧。
晚安,我童年的伙伴。晚安,我的童年。 童年,永不说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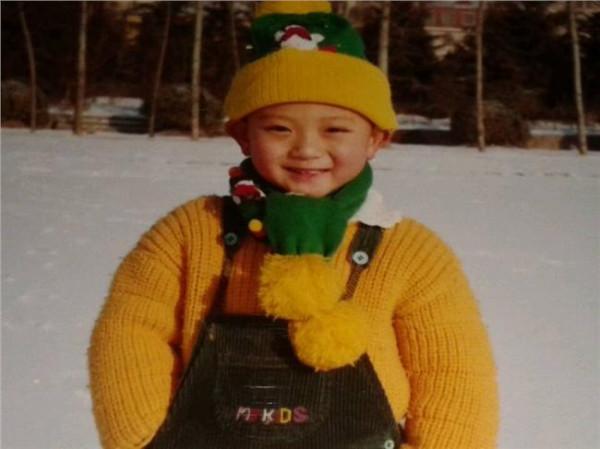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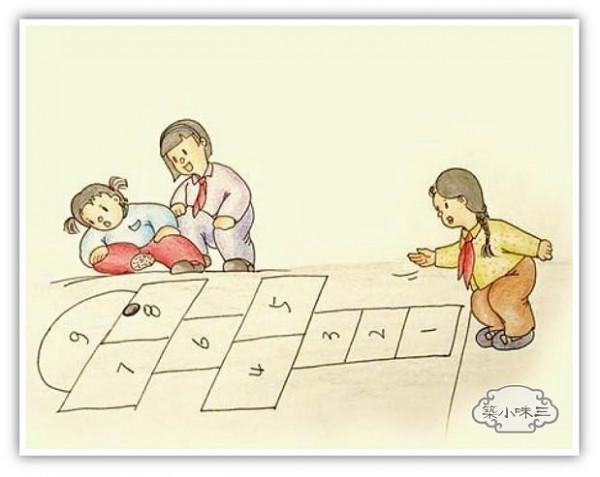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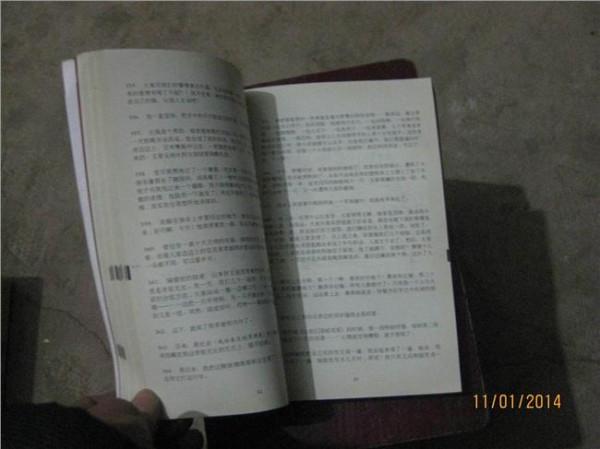
![>桑格格黑花黄 [读书]桑格格新作《黑花黄》童心不改](https://pic.bilezu.com/upload/0/44/0447630180c7d78e492e2e6041ff23a3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