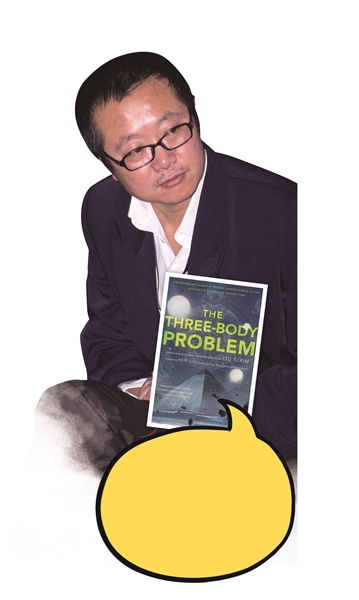曹乃谦复选 曹乃谦入选诺奖复评 “一个真正的乡巴佬”
马悦然在《温家窑印象记》一文中写道:“村里的光棍们最喜欢吃的是油炸糕,最盼望的就是娶个女人。村里的人物多半是一些年轻的或中年的光棍,除了渴望吃饱以外,他们都渴望着跟一个女人睡觉。光棍们把跟女人‘睡觉’说成‘做那个啥’。在温家窑娶一个女人要花两千块钱,光棍们穷,买不起女人,就只有跟自己的妹妹,或者跟自己的母亲‘做那个啥’。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就得找一个母羊来代替女人。”
“温家窑”有三十户人家,一共不到两百个人,出现在曹乃谦小说里的男女,老小在内有五十几个人。丑邦、愣二、温宝、黑蛋、贵举老汉和下等兵,这些人和他们的故事都是马悦然熟悉的。
愣二的原型是村里的二明(化名),喜爱村里的一个比他小三岁的姑娘大兰,自己也知道人家不可能嫁给他,只盼着她不要被别人娶走。有一次植树时,二明指着地上的脚印对曹乃谦说:“曹队长,我一看这就是大兰的。你看,5个脚趾头就像是5颗豆。”二明的耳朵有点背,经常“嗯?嗯?”的,人们说他反应慢,有点儿愣。
因为性欲的压迫二明有时会发疯。他发疯时母亲就让他父亲到离村比较远的煤矿去找大儿子要钱,父亲过几天回家,愣二就好了。村里人不清楚愣二愣得好好地咋就给疯了,也不清楚愣儿疯得好好地咋就又不疯了。除了愣二,还有黑蛋。
他花了1000元钱给儿子买了个女人。因为价钱低,黑蛋就答应让亲家每年把自己的老婆接回家去,“用”她一个月。温孩总算是娶上了女人,但那个女人不跟温孩好好过,平时把红裤带绾成死疙瘩硬是不给解,还一个劲儿哭。
温孩去问妈,妈说:“树得刮打刮打才直溜。女人都是个这。”温孩听了妈的话,回家就揍女人。有听房的人传出说:这下顶事了,温孩压在女人身上就“做那个啥”,还说:“日你妈你当爷闹你呢,爷是闹爷那两千块钱儿。”
曹乃谦说:“我写的是真人,真事儿。我想告诉现今的人们和将来一百年乃至一千年以后的人们,你们的有些同胞有些祖先曾经这样活着。”
马悦然读到曹乃谦小说的感觉是:“一看就发现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值得翻译的作家。”
马悦然请他在山西的朋友李锐打听曹乃谦是谁,刚好李锐跟曹乃谦很熟,回话说:“大同的一个警察。”
2004年5月,马悦然有机会跟李锐到吕梁山去,在李锐“文革”时期插队的山村邸家河住了几天,回到太原时约曹乃谦见面。曹乃谦把小说《温家窑风景》交给马悦然,总共三十篇。回到瑞典不久,马悦然就把那些小说翻译成瑞典文出版。
远在瑞典时,马悦然常常写信跟曹乃谦打听小说里的那些人,这个生活得如何,那个过得怎样。为了回答他不断的提问,曹乃谦就不断去温家窑。有一天他告诉马悦然,愣二的原型二明已经不在人世了,而且至死也没娶到女人。隔了好多日,马悦然再没来信。曹乃谦有些后悔不该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他。
突然,有一天马悦然来信说:“咱们一定得去给二明上上坟。”就这样,2005年10月21日,马悦然从瑞典坐飞机到北京,然后又坐公交大巴从北京到了大同。
一行数人,在曹乃谦家吃完“迎风面”,就向“温家窑”出发。
到了温家窑,吃完晚饭,马悦然和曹乃谦踩着月光来到二明在树林里的坟地。
马悦然说:“二明,你看,我们来看你来了。”他的声音有点哽咽,“二明,让乃谦给你唱个要饭调吧。”
曹乃谦就对着二明的坟头唱:
山在水在石头在,人家都在你不在;刮起东风水流西,看见人家想起你……
唱了四句,伤感得唱不下去。曹乃谦停下来的时候,看见马悦然掏出手绢在擦拭眼泪。
“逢酒必喝,喝酒必疯”
曹乃谦站在瓦房的土墙根儿下跟村支书丑邦说话。天气很热,他撩起衣服,亮出厚肚皮上的一道两寸长的疤痕。“哥现在是个没胆的人,奇怪的是没了胆哥反倒是啥也不怕了。”曹乃谦拍着肚皮说。
34年前,曹乃谦第一次走进“温家窑”时,迎接他的也是丑邦,那时候他是怕的。
当时做着警察的曹乃谦被分配到村里给知青带队。“贫穷是‘温家窑’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人们都是穿得破破烂烂的,像要饭鬼。社员们住着低又矮的窑房,看不到砖瓦,全是土黄的颜色。那里的人好,男女老少都是笑笑的,很和善。但也很委琐,称呼我都是‘您,您’的。常跟我一块儿玩耍的那几个年轻人也都是这么称呼我。”
知青点儿只有8个知青。曹乃谦主要是让他们吃饱吃好不要想家,一年来平安无事。那7个女知青都是小孩子,最大的才17岁。当时有政策,劳动够了5年的,年龄够了22岁的才有可能被招工。一些想着被招工的大龄女知青,才想着法子跟带队的套近乎。而那些跟女知青发生了关系的带队队长们,都是利用女知青想当工人的心理去引诱她们。当时对这类事情处理很严,跟破坏军婚一样严厉。
当年知青的排房共10间,后来卖给了村民,东边的5间让村民拆了又重盖了,没有了排房的样子。另有5间还在,曹乃谦买下了两间。其中有一间正是他当年给知青带队时住了一年的那间。买下来是为了做纪念。再一个是,也真的想常回去住住。以后再回去,也就有了自己的家了。
曹乃谦在温家窑呆了一年。记忆最深的是“打平花”。每隔那么二十多天,几个光棍,有从家拿莜面的,有拿山药蛋的,有拿麻油的,凑在一起饱饱地吃一顿夜饭。肉是肯定没有的,但有时候喝酒,酒往往是曹乃谦给供应。吃喝完就唱要饭调。人带点酒意,唱出的要饭调那才叫好。在雁北地区,“要饭调”也叫“讨吃调”、“挖莜面”、“烂席片”、“山曲儿”、“酸曲儿”,是讨吃的人跟人要饭时唱的那种歌儿。
“逢酒必喝,喝酒必疯”,这是曹乃谦为人所知的作派。只要喝了酒,就亮开高嗓唱要饭调。
唱吧唱吧唱吧。在温宝家的炕上,丑邦举着酒杯让曹乃谦唱。温宝家的窗台上坐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和女人,他们都鼓动曹乃谦唱要饭调。
牛犊犊下河喝水水, 俺跟干妹妹亲嘴嘴。井拨凉水苦菜汤, 不如妹妹的唾沫香。葱白白脸脸花骨朵嘴,你是哥哥的要命鬼。你在圪梁上我在沟,亲不上嘴嘴招招手……
曹乃谦亮开嗓门唱。这些要饭调被他唱过无数次。
让曹乃谦忘不了的是,在他唱要饭调的时候,那些喝醉酒的光棍们互相抱住直亲嘴。
1988年,37岁的曹乃谦跟人打赌,开始写起小说。“温家窑”是他写的第三篇小说。作家汪曾祺在《北京文学》组织的笔会上看到曹乃谦的小说,大加赞赏。“这种生活是荒谬的,但又是真实的。这是苦寒、封闭、吃莜面的雁北农村的生活。只有这样的地区,才有这样的生活。”因为写小说,曹乃谦跟汪曾祺成了忘年交。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的三十篇小说就这样陆续写出来,通过《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和台湾的《联合文学》发表出来。同时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选刊选载。
他是偷过来的孩子
然而,从1996年的下半年开始,曹乃谦就完全停止了写作。原因是母亲有了病。
“那天中午下班回家,见门反锁着。母亲看见我,把门打开,放我进了家又赶快把门拨住。我问发生了什么事,她摆手不让我说话。整个中午她都不说一句话,只是打手势让我不要出声。下午我下班回来,一进门,她撸起我的袖子,边哭边说,‘我看把俺娃打的。
看把俺娃捆成啥了。’第二天她就疯得更厉害了。上午叫着我隔壁院邻居去西门外找我,她说我的招人(招人是我的小名儿)在西门外让人杀了。邻居们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跟她到了西门外,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
她这是得了幻视幻听恐怖症。凡是她幻觉出来的影像,都是她的宝贝儿子发生了恶性事故,杀了剐了,捆走了活埋了,而她还要把这当成正在发生的真实事件。第二次她又这么说,邻居们不跟她去了,她就自己拄着拐杖提着菜刀去解救我。
后来,她又幻觉出,应县老家来人要抢她的小招人。我女儿听说奶奶病了,来看望她,她一看见我女儿就说,‘赶快把你爸爸抱过来。快藏盖窝后头。’她已经又把我幻觉成了7个月的从下马峪村里偷出来的那个婴儿了。”
曹乃谦出生在山西应县下马峪村的一户农民家里。“一个叫换梅的31岁的女人当时格外地看好我,从田里劳动回来饭都顾不得做,先得来抱抱我才算。她有时候就把我抱到她家,还经常搂着我在她家过夜。我跟她不认生,无论她把我抱到哪里我都不哭。
那一天的凌明,村里人大都没起来。她在毛驴肚下做了个吊床,把一个小包裹和我放在上面,就牵着驴出了街。村外,有个人远远地喊说,换梅大清早去哪呀?芽她说我老常借人家的驴,给人家放放去。出了村,她把我解下来抱在怀里,用柳条当鞭子,骑着驴就急急地往北赶去。走出二十多里她下了驴,用土块和树枝把驴轰打着上了回村的路,抱着我急匆匆地步行向北走。
“她用两条腿一直行走了两白天一黑夜,把我带到远离家乡二百多里的地方,在大同城安家落了户。
“这个叫换梅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大贵人,但是她疯了。”曹乃谦说。
怕母亲跑出街发生别的什么事,上班时曹乃谦只好把她锁在屋里。隔一会儿就从单位回家露露面,好让她看见她的宝贝儿子还活着。
“每当我看见她神色紧张地扒在门玻璃焦急地往外瞅望、看见了我她又痴傻地笑着的样子,我的心都要碎了。”
现在曹乃谦正在写关于他母亲的一部长篇小说,篇名就叫《母亲》,已经写了快一半。
几乎是在不经意间,曹乃谦的小说开始出版。《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先后在瑞典、台湾、中国大陆出版。
作家李锐说:“经过多年的周折、埋没、等待,他的小说终于出版了,终于跟读者见面了。这也终于见证了一个道理:好小说好文学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三级警督曹乃谦经得住时间考验,他只管写作,不管文坛。他的职业仍是警察,他在公安局的办公室紧靠着厕所,臭气不时扑鼻而来。
“尽管我也搞过刑侦工作,但没打过嫌疑人。有的人搞逼供,那是他没本事。我是以理服人,也以礼待人。这样嫌疑人就服你,愿意主动跟你讲真话。再一个是,我认为罪犯也是人,我们不能因为有管他的特权,就欺侮他、打骂他。
我张不开那口,我也下不了那手。我还有个习惯做法是,每要将嫌疑人送进看守所前,总给他吃一顿好饭,我问他好吃饺子还是包子,好吃米饭过油肉也行。他好吃啥给他买啥。我的意思是:对不起,因为我侦破了这个案件,让你进了看守所,请你原谅也请你理解。”
现在曹乃谦每天会在半夜3点多起来写作,写到5点半妻子醒来时就关机不写。早6点前就到单位,写毛笔字。写到8点开始工作。午休是必不可少的,一年四季都这样。
“白天我不写作,再有时间也不写。这是个习惯,从写第一篇时就养成的习惯。当时我是偷偷地写,怕人知道我是在写小说,就连妻子我也没跟她说。”
“反正是不让人看。我的看法是,写小说就像是在生孩子,生孩子总是不想让人看。”曹乃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