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旅之思——读夏磊散文集《秋以为期》
以代际来划分,夏磊应该算是新生代作家了。在新生代的散文创作中,一直存在着对叙述的迷恋——新生代散文热衷于书写个人经历,表现作者的日常生活体验,个人体验的“现场感”使他们更多地关注自我的生存状况。于是,对个人生活轨迹的描述和感悟,成为新生代散文不可或缺的创作资源。
阅读夏磊的散文集《秋以为期》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对生命体验的放大和凸现。作者从对自然风物、文化遗存的观照中生发出对于历史、人生的体悟和哲思,通过对细节的把握和主体情绪感觉的拥入,咀嚼生命的况味,以始终“在路上”的姿态寻找心灵的安顿,正像他自己所说,“这几年,我开心地在做一件事,走路和读书”,“我要让心灵跟着自己的脚步,从一个远方走向另一个远方;让心灵随着自己的眼睛,从一个千年掠过又一个千年;让心灵融进自己的泪水,为每一个值得感动的东西去放肆地感动”。
于是,作者走进了《边城》和湘西所营造的柔美情境,由对沱江与凤凰的体验和解读贴近了沈从文与他的文学世界(《月碎沱江》);他书写六朝以来的脂粉风流,俯拾起散落在夫子庙、乌衣巷和秦淮河上的历史记忆,用古人诗词的楔入和历史典故的穿插传达出幽深的历史感(《岁月秦淮》)。
在我看来,夏磊的散文显然并不在“不大容易看懂”的范围之内,这与作者丰赡的学养以及对历史、文化的偏爱有关。他从湘西、秦淮、富春江、江南古镇、书院等场景入手,展开对其背后传统文化积淀与地域文化特质的感悟和思考,对典故、诗词的信手拈来构成了相对厚重的文化内涵。
情感与文化、自然的对接让文章显现出灵动而丰富的意蕴,在个人体验的附着下,物象与事件被作者的情绪、意志操控和改造,成为凝结着个人独特感受的心灵的外化,这不仅极为容易地使读者产生了代入感和认同感,也成为夏磊散文的个性之所在。
《夜饮富春江》《沧浪浮生》和《寂寞的书院》等作品呈现了夏磊散文的突出特征,即情(作者的意绪、情感)、景(自然场景与历史场景)、文化在文本中的交融。《夜饮富春江》从观富春江夜景说开去,由富春江联想到生活于江畔的隐士严子陵,从而引起作者对隐逸文化及中国文人品格命运的思考。
他将隐士称为以归隐保持其操守并怀有大抱负的有志之士,把隐逸看作是一种人生理想与人生追求,认为“恰恰是这批隐士,常能临危受命挺身而出,他们代表着民众和志士的心声,融合着自己对于政治和历史的思考”,“他们都胸藏万仞,志在千里”。
在严子陵身上,作者看到了中国文人的节操,“他的并不复杂的生命历程所表现出来的全部精神就是不慕虚荣,不怵权贵,淡泊名利”。
《沧浪浮生》将沧浪亭与《浮生六记》勾连在一起,从观赏沧浪亭生发出对《浮生六记》中男女主人公生活场景的再现。通过在沧浪亭现实场景的映托下复原《浮生六记》中所描述的场景,作者将事件的真实让位于个体体验的真实,意象的创造和场景的再现呈现出主观化、感觉化的特点,在文本中开拓了一个自由的想像空间。
如果说沧浪亭的疏淡清朗和《浮生六记》的恬适汇合在文本中,使淡、闲、雅的文化韵味淌溢出来,那么对鹅湖书院的叙述则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
作者以鹅湖书院的盛衰落笔,通过对朱熹、陆九渊“鹅湖之会”因缘、轶事的讲述,展现了鹅湖书院与儒家文化的血缘关系,并从鹅湖书院的衰败发现了中国文化尚虚轻实的缺失。“忽然觉得,书院就像一个背对我们的老者,岁月无情地改变着他的躯体,但我们却永远看不到他的眼神。
这眼神,可能是平静的,或者,也可能是略带感伤的”,在作者的笔下,鹅湖书院承载着传统文化的沧桑命运,它的兴盛和颓败正是儒家文化在不同历史语境下从自我革新到自我束缚的缩影。
在这本《秋以为期》里,我读到最多的是“老家”,那个叫做八卦洲的地方。无独有偶,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故乡一直是新生代散文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江西散文而言,乡土记忆也总是萦绕在作者的笔尖,孩提的懵懂、挥散不去的往事、古朴的村镇构成了他们的写作中一幅特异的图景。
我将此归结为现代性的征候。从成长背景看,新生代散文作家群体都经历了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面貌和社会心理的巨大变更,在代际的划分上,他们这一代人面对的是传统价值观念的解体和新的价值观念的建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内在观念冲突,因此也被认为是“信仰危机”的一代。
这一点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为对于城市和乡土的双重困惑:正如海德格尔对现代人处境的判断——本真性存在的丧失使我们“无家可归”,对于这些作者而言,正处于这样一个进不来、回不去的尴尬境地中,他们漂泊在城市里,试图融入整个现代都市文明中,却又无法摆脱对个体独特性的坚持,而在这个喧嚣轻浮的时代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城市生活的冷漠的旁观者,但又对正在被现代文明改造的故乡抱有疏离感。
所以,新生代作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常常陷入自我定位的矛盾。从这一角度出发,他们回归自然的生态与对乡土、童年的记忆,目的在于寻找心灵的寄托,以摆脱精神的无所归属。
于是,故乡在夏磊的叙述中渐渐分解为一个个充满温情与眷恋的生活场景:《那时芦叶香》回忆了多年之前一家人围拢在一起包粽子的情景,那时笑声在“那个安静的晚上传出去很远,很远”;《秋以为期》呈现一个躺在田野上看书的惫懒与闲适的少年,他读着来自土地的诗——《诗经》,“我听到了来自大地的自由的歌唱”;《露天电影》再现了童年时看露天电影的乐趣和时代变迁的感伤;《故乡的雪》写道“我们的记忆又能留住多少逝去的美丽呢”,以追忆儿时下雪的场景传达出对岁月的唏嘘;《乡忆如丝》叙写八卦洲的风土民情,通过对三国和大虎子两个人物的回忆将乡村的生态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当作者以成年人的视角重新审视这片乡土时,记忆和现实的错位却又总是造成心灵的不安和焦虑,对他来说,故乡只能成为回忆,成为夜晚如蚕丝般抽不完的往事,在记忆中提供灵魂的休憩。
带着时光一去不返的怅惘抒写故乡,是夏磊与整个新生代散文共同的写作倾向,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希望以回归母体的方式实现精神原乡的诉求。这种细腻的生命体验呈现出的是情感的真实与心灵的开放,对于作者而言,“真实”意味着自我的率真表露,是指向内心的真诚与无遮蔽。
在《独在旅途》中,作者展现了孤独的旅程里精神状态的丰满和愉悦,“行走”与“寻找”的质感充溢在跳跃的文字间,“我们已无法忍受孤寂。其实,是早已失去了孤寂的机会。
我们已不知道享受独自旅行时的孤单寂寞。我们的一切,包括心灵,都已经不再属于自己”,因此孤独给予了心灵自由舒展的空间,“独处是心灵的放松,寂寞是一种美丽的情绪”,“一个人在旅途,透过车窗,能看到很多只有自己才能懂得的风景”。
从风格上看,夏磊的散文以相对质朴而富于文化意蕴的文字,高扬了个人生命体验尤其是自我的独特感知,这样的文字趋向作者内心,强调的是用主体的体验介入对事件的书写,从历史文化与生活经验的细微处凸现心灵的真实。他对历史、文化的深入把握和独特视角创造了一个别有韵味的审美空间,特别是从历史的视野建构文本,使作品从碎片化、自娱自乐式的叙述中摆脱出来,显现出了历史的深度与广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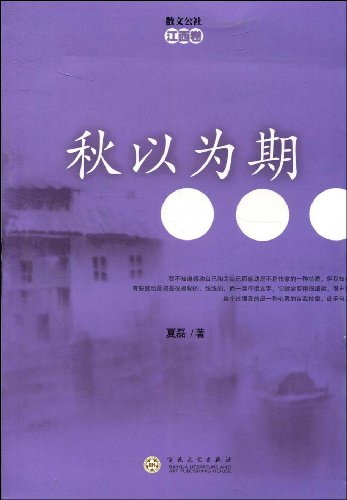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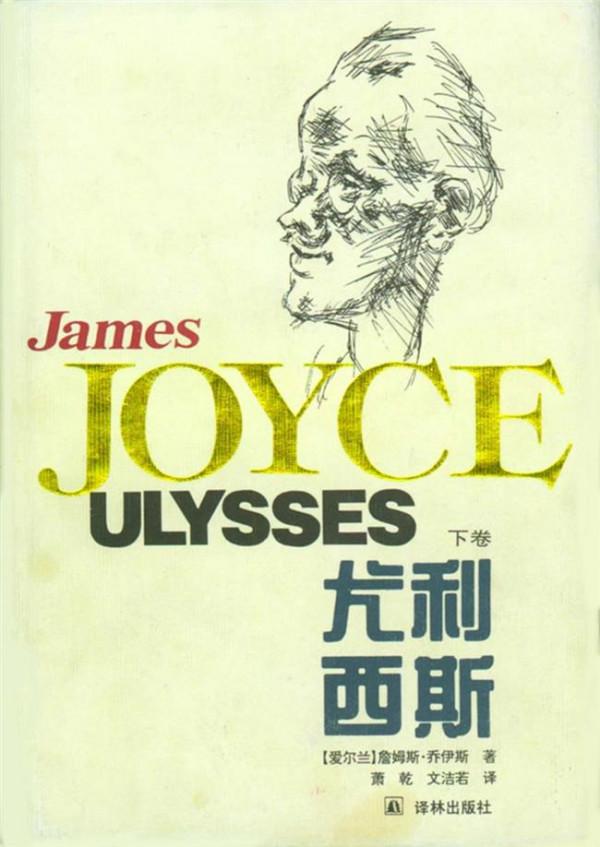

![>主持人方亭老公 夏磊[东方卫视主持人]](https://pic.bilezu.com/upload/1/9b/19b7dd9e51e66a03b351d2285ebbba89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