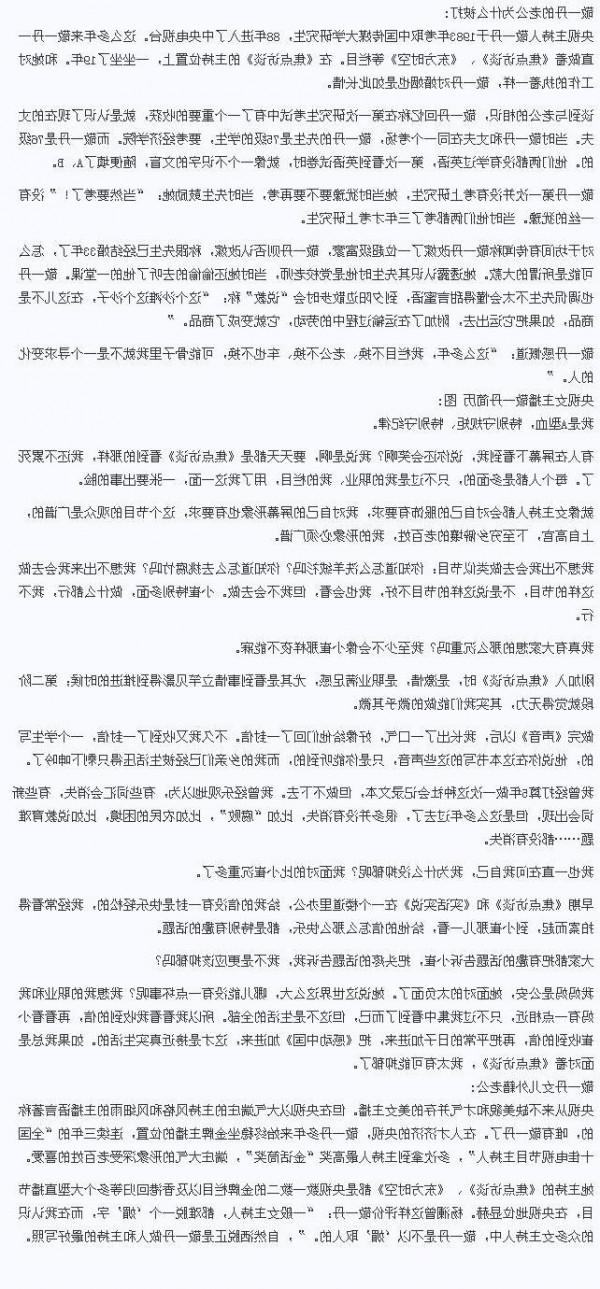“末代工农兵学员”敬一丹出新书:我的少女时代没任性过
“缺少选择是我们这一代的最大特点。”敬一丹说。
在上世纪70年代,有一群特殊的高校学生,他们的名字叫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始于1970年,共有94万年轻人入校学习。1977年恢复高考,持续七年的工农兵学员招生成为历史。1976年入学的那一届成为了“末代工农兵学员”。
《我,末代工农兵学员》一书中,敬一丹以那个上山下乡的匆匆岁月书写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从下地干活、公社生活、时代变迁等多方面介绍了那他那一代50后所经历的各种特殊的体验。敬一丹与同学们,一起回忆过去写下珍贵的记事录,也借此反思了当下如何重获最简单的快乐。书中60张手绘图,均为76播同学、敬一丹的宿舍室友李小梅所绘,形象地再现了60年代、70年代的生活场景。当年同学们走出校园后,这些年各自在专业领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和成就。不论在电台、电视台,还是在学校、报社,经过多年的努力、坚持,进取,他们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
“我们全班是29人,有两位已经去世了。”敬一丹无不遗憾地说。“我们的记忆,不仅是我们的。如果我们忘记了,如果我们不留下痕迹,以后的人们怎么知道那些事情曾发生过?就连我们的孩子都会模模糊糊将信将疑。趁我们还没有忘记,写下来吧,留给孩子。”
“我从来没有任性过,我的克制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敬一丹认为自己的大学时光全部都是在严格的自我约束中度过的:“我那时候总穿一身蓝衣服,永远是一本正经的”。敬一丹上大学的时候,“广院”是严格禁止学生们谈恋爱的,有些“叛逆”的同学仍旧不顾禁令偷偷恋爱,敬一丹不是叛逆恋爱的那个,而是作为班干部负责和恋爱的同学谈话的那个。当年恋爱的同学也来到了现场,他们当年的地下恋爱开花结果,如今已经有了孙子。
“缺少选择是我们这一代的最大特点。”敬一丹说,他们上大学没得选,分配工作也没有太大选择,这是也让他们青春时虽然吃过不少苦,却没感受过什么迷茫。“我们那一代是有饥饿记忆的,估计水亦诗这一代的年轻人就只有减肥记忆了。”敬一丹回忆,她们入学的时候还是票证时代,她馋了想去王府井吃完面还琢磨半天:我是花三毛二买一碗面呢,还是买二两“酸三色”的水果糖呢,水果糖能吃一个星期,但面一下就吃完了……
敬一丹于2015年曾写作《我遇到你》,讲述自己的职业生涯;而《我 末代工农兵学员》就如《我遇到你》的“前传”般,讲述了她职业生涯之前的大学生活记忆。在这两本书中,敬一丹通过自己的视角、同学群体的视角,折射出50多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1993年进入央视的,说起青年我们这一代人在大学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迷茫,但和敬一丹老师他们那一代已经很不一样了。”与敬一丹的“缺少选择”不同,康辉经历了高考填报志愿、选择大学和专业的过程,但也不算迷茫。“当时考大学选择播音是特别偶然的,我不是方向性很强,觉得这算是提前录取了,而且那时候广院的分不高,以我的高考成绩一定能上,选这个是最踏实了。至于后面的志愿都是瞎填的,什么辽宁大学的考古专业、天津商学院的酒店管理专业,真是闹着玩的。”康辉说。
康辉回忆自己上大学的时候每个月的生活费是100块钱,而水均益的女儿水亦诗是2012年进入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2016年毕业,她的生活费每个月“两三千”,上学的时候用零花钱花七、八百块在学校旁边的西装店买一身播音时穿的西装。水亦诗这一代人不但没见过“布票”,连成匹的布也没见过,但敬一丹讲到大学时将布票放过期而后悔万分的故事还历历在目。
而中坚力量的康辉也开始对年龄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了。他每次碰到敬一丹都说:好羡慕您退休了,可以有很多时间自己支配。“我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人,已经开始对年龄有一种很特别的认知。前一段时间我值配音班,有一个90年的记者拿来一个稿子,里面有一句‘这位年近半百的老人’,我说,怎么年近半百就是老人了?你一定要改掉,太刺激人了。”康辉说,算算自己的年龄也“年近半百”了,是不是自己已经算老人了?
敬一丹的年代,中央电视台还不是大家的“事业理想”,那时所有人都想进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练习播报发声的时候都以“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谁谁”开头,尽管大家心里清楚这样的机会凤毛麟角。敬一丹告诉晚报记者,当年他们选择工作不看成绩、不看业务能力,而是“从哪来回哪去”,北京的同学有可能留在最好的单位,基本上同学们都回原籍了,敬一丹就回到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
康辉进央视就顺利地多,康辉告诉晚报记者,她们当时刚刚开始使用一种叫“双向选择”的找工作机制。“说是双向,但其实我没有什么资格去选择中央台,只能等他们选择我。”康辉说,所谓的“双向选择”其实是当你很明确知道这三个台不会要你的时候可以选别的,比如其它省份的电视台,但必须要征得所在省份广播电视厅的同意,开退函才可以去。
“我们首先要经过选拔才有机会去央视实习,再经过台里的选拔认为你从工作态度、专业能力等各个方面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进。”康辉回忆,他们班当年在中央电视台实习的同学有12、13人,最终有7个同学同年分配进台,“这在广院播音系的历史上不知道是不是绝后,但肯定是空前的,因为1993年起电视开始有一个‘黄金时代’,需要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来,从这个角度想,我们是幸运的。”
康辉现在还会想起那时候的紧张和焦虑,他当时也“双向选择”过,自主地选了上海东方电视台,现在想想,那个时候自己特别幼稚,曾经跟东方电视台人事处处长讲过特别冒犯的话,我说中央台还没有给我信儿,要是中央台不要我的话,我就去你那儿。
敬一丹称为“我们台里最靠谱的青年”的康辉,敬一丹说笑称“我俩的交情就隔着一个《天气预报》,《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嘛。”康辉则称敬一丹为“业界标杆”,他记得敬一丹在台里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剪辑室,一帧一帧地调节目:“敬大姐现在退休了,也管不着我了,我完全没必要巴结她,她在我心目中就是很完美的,标杆一样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