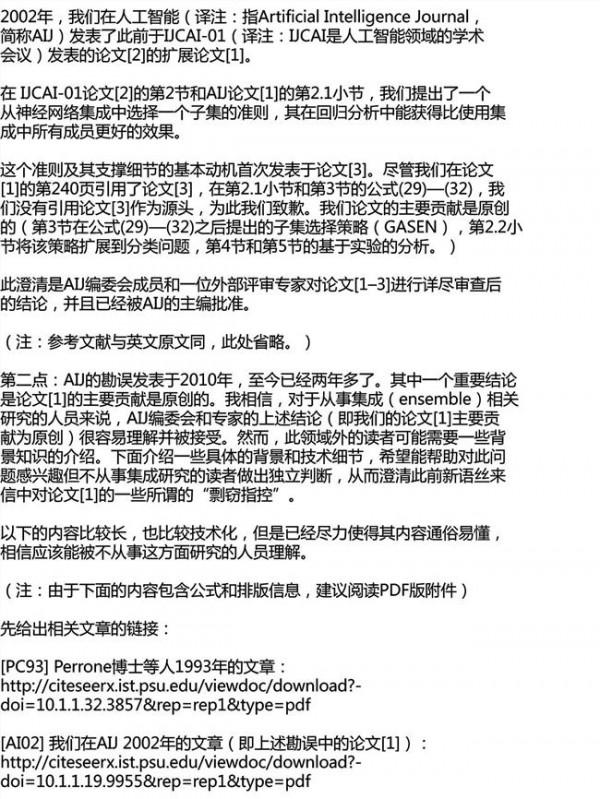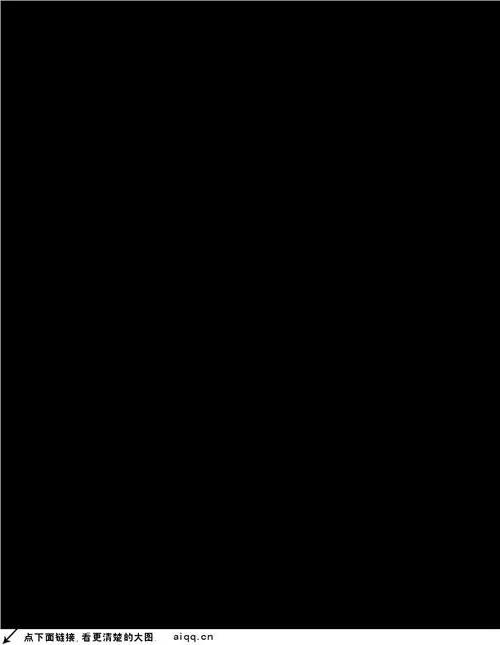潘知常事件 潘知常:以美学精神投身现实事业(上)
潘知常 个人简介 潘知常:1956年生。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9年被评为河南省与郑州市的“青年精英”,并被授予荣誉称号,1992年被批准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93年被特聘为教授。
历任南京大学企业形象研究中心主任、《美学与文艺学研究》副主编,中国民盟中央委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广播受众研究会理事,中国青年美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企业形象研究会副会长等。
研究范围主要为美学基本理论、中西比较文化与美学、媒介文化、媒介研究等。同时长期从事企业、地区与媒介等方面的各类策划、设计等应用学科的研究与实践。
先后出版了《众妙之门》、《中西比较美学论稿》、《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独上高楼——中西美学对话中的王国维》等学术著作14部,《传媒批判理论》等编著5部,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历年来主持、参加国家社科项目、省重点项目、省一般项目、省教委项目、南京大学重大项目等共11项。
同时曾主持横向项目《南京城市形象研究》、《南京河西新城区文化特色研究》、《南京市仙林大学城文化特色研究》等十余项政府与地区形象设计与策划项目。
2004年9月10日,教师节。一场江南的细雨,悄悄地淋湿了夏天郁积的燥热和潮闷,南京,这个繁花似锦、妩媚多姿的“博爱之都”在早来的秋凉中变得明媚和舒爽起来了。也是在这一天,南京的鲜花陡然紧俏,伴随着南京大学策划的“鲜花送老师”活动的渐入高潮,在南京大学梧桐遮盖的林荫大道上,掩映在鲜花和欢笑丛中的莘莘学子穿梭如织。
置身此情此景,令人不由想起2003年3月开始的南京市“万朵鲜花送雷锋”那个百万人瞩目的盛况空前的场面,令人不由想起那次活动的策划者、著名美学学者、传播学者、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知常先生。
始终坚持 “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 记者:潘老师,您好,今天是教师节,首先祝您节日快乐。
熟悉您的人都知道,您是中国当代自李泽厚以后最为重要的美学家之一,我个人也非常喜欢您在《生命美学》、《诗与思的对话》、《生命美学论稿》等一系列美学论著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飞云烈火、骄阳甘霖般的恣肆文风。
我知道,在国内学界您应该算是“年少成名”,1984年,年仅28岁的您就已经举起现在已经名动天下的“生命美学”的旗帜,在90年代开始的国内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两大学派的迄今已经长达十年的大论战中,三十几岁的您又成为后实践美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而且,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您也曾经是国内最年轻的副教授、教授之一,还在1990年被作为优秀学术带头人“特聘”到了南京大学。
那么,您能否谈一谈,您是如何看待学术创新、理论创新问题的? 潘知常:“创新”是学术研究、理论研究的生命。人们喜欢对年轻学子强调要勤奋、要厚积薄发、要严谨。这无疑都是对的,但是其结果往往是“厚积”而不“发”,所谓“严谨”也往往成为“平庸”的代名词。
最终所谓“勤奋”也就成为为“勤奋”而“勤奋”。每届博士、硕士入学的时候,我都会以足球运动员的日常训练为例跟他们强调:一定要“脚下有球、眼中有门”。
没有带球意识、射门意识的运动员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同样,没有带球意识、射门意识的学生也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看看中国与西方的情况,我们会发现,西方的学生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都不像中国学生这样死命读书(我们甚至从“胎教”就开始逼迫孩子学习了),但是西方的学生从大学到博士毕业,很快就会走向诺贝尔奖的学术圣殿,但是我们的学生却至今没有“登堂”,就更不要说“入室”了。
这种“高成本、低回报”的困境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当然,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缺乏创新意识却肯定是其中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想想我们的教育理念吧,“铁杵磨成针”、“愚公移山”都是我们熟悉的故事,我们的老师经常以此来勉励我们,但是我们为什么就没有想过用铁棍子去换针呢?那岂不是不但得到了许多的针,而且还得到了大量可以用来成就其他事业的时间?而“愚公”又为什么非要“移山”?为什么就不能搬家?再看看古今中外的大学者,他们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的年龄其实大多都很年轻,就以美学家为例,王国维是28岁,鲁迅是26岁,叔本华、尼采写下不朽之作时也只有二十几岁。
而且鲁迅学的是医学、尼采是语言学教授,他们在人文科学方面的积累究竟有多少?我想,肯定不会比当时同年龄的一直在学习人文科学的那些人要多吧,但是,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的为什么偏偏是鲁迅、尼采?个中原因无疑不能忽视。
记者:您能否结合您的美学研究再具体谈谈什么是带球意识、射门意识呢? 潘知常:带球意识、射门意识实际就是问题意识、科研意识。
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百上加斤易,千上加两难”。真正的学术研究不是在“百上加斤”,而是“千上加两”。就问题意识而言,我们的学术研究其实就是要找到前人所已经提供的既有研究成果,所谓的“千”,并且进而加上自己的那一“两”。
在我看来学术研究的全部艰难与简单就都在于此了。以我自己的美学研究为例,假如说我的美学研究还有一点点经验可谈的话,那么对于问题的发现应该说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了。
20世纪80年代初,我天天阅读的都是西方康德、黑格尔的知识论美学和中国朱光潜、李泽厚的实践论美学的著作,那个时候,我无疑是非常勤奋的,但是真正使我受益的,却是最终的对于问题的发现。
在我28岁的时候,我发现美学之为美学应该是对于人类的审美活动与人类个体生命之间的对应的阐释,而这正是西方康德、黑格尔的知识论美学和中国朱光潜、李泽厚的实践论美学所最为缺乏的。
于是,我很快离开了他们。实践美学在80年代的中国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人微言轻的年轻人,之所以敢于“离经叛道”,还不仅仅是出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学术勇气,而更主要的是出于对于问题的发现,美学之为美学,应该是对于人类的审美活动与人类个体生命之间的对应的阐释,这就是我所提出的生命美学所要面对的美学问题。
当然,此后生命美学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是我所始料未及的。卡尔·巴尔特在描写自己写作《罗马书注释》一书时的心路历程时说:“当我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沿着教堂钟楼黑暗的楼道往上爬的人。
他力图稳住身子,伸手摸索楼梯的扶手,可是抓住的却不是扶手而是钟绳。令他害怕的是,随后他便不得不听着那巨大的钟声在他的头上震响,而且不只在他一个人的头上震响。
”这也是我提出生命美学后所走过的心路历程。还有一次对于问题的发现是在2001年的春天,新世纪伊始,我是在美国、加拿大度过的。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因为生命美学而“邂逅”了不少卑鄙与龌龊以及国内某些人借助“反自由化”运动而在美学领域对于生命美学的严厉批判,但是我却始终“虽九死而不悔”,不但不悔,而且还在执着地思索着新的美学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了15年的苦苦探索,2001年的春天我在美国纽约的圣巴特里克大教堂终于又找到了进一步的美学问题。那一天,我在圣巴特里克大教堂深思了很长时间,终于第一次清晰地理清了15年来的纷纭思绪:个体的诞生必然以信仰与爱作为必要的对应,因此,必须为美学补上信仰的维度、爱的维度。
在我看来,这就是美学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可以不去面对宗教,但是必须面对宗教精神;我们可以不是信教者,但是却必须是信仰者,我们可以拒绝崇尚神,但是却不能拒绝崇尚神性。
而神性缺席所导致的心灵困厄,正是美学之为美学的不治之症。因此,个体的发现必然导致的只能是也必须是爱之维度、信仰之维度。这就是说,人类的审美活动与人类个体生命之间的对应也必然导致与人类的信仰维度、爱的维度的对应。
美学之为美学,不但应该是对于人类的审美活动与人类个体生命之间的对应的阐释,而且还应该是对于人类的审美活动与人类的信仰维度、爱的维度的对应的阐释。
你可以看到,我近20年的所有美学著述,无非就是对于这样两个由浅入深的美学问题的考察。换言之,在上个世纪是对于人类的审美活动与人类个体生命之间的对应的阐释,新世纪伊始,则开始转向对于人类的审美活动与人类的信仰维度、爱的维度的对应的阐释。
记者:您回国以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许多著名高校的演讲中都反复强调要关注《红楼梦》、王国维,尤其要关注“鲁迅的失败与失败的鲁迅”,这是否就与您在纽约圣巴特里克大教堂的对于进一步的美学问题的发现有关? 潘知常:是的,因为没有意识到个体的绝望必然导致的只能是也必须是爱之维度、信仰之维度,事实上鲁迅只吃到了知识树的果子,但是却没有吃到生命树的果子。
他经常追问:“娜拉走后怎样”?现在我们更应该追问的却是:“鲁迅走后怎样”以及“我们怎样比王国维、鲁迅走得更远?”在我看来,新世纪的美学必须从这里也就是从“鲁迅的失败与失败的鲁迅”开始。
记者:作为国内后实践美学的领军人物之一,您的美学贡献已经被写入了多部中国20世纪美学史研究的学术专著,例如,北大教授、博导阎国忠的《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武汉大学教授、博导陈望衡的《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我注意到,在中国20世纪的美学家中,您是名列20世纪美学史研究的学术殿堂之中的最为年轻的学者,那么,作为新世纪中国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您怎样看待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长达十年的论争? 潘知常:坦率而言,我对于实践美学的创始者李泽厚先生始终保持着敬意,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畸形年代,他能够提出实践美学,事实上已经极为难能可贵。
但是从学术本身而言,我必须说,实践美学的缺憾是致命的,在王国维、鲁迅之后,实践美学始终既未能“照着讲”,也未能“接着讲”,根本没有找到真正的美学问题,这使得它最终必将被历史所跨越。至于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之间的论争,我则始终坚持“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坚持从“对抗”到“对话”,坚持从“砌墙”到“架桥”,坚持从“不破不立”、“先立后破”到“立而不破”。
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向主流美学挑战无疑并非“请客吃饭”,而且肯定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或者愧对良心,或者愧对妻儿,除此之外,我也实在别无选择。
需要强调的是,经过上个世纪90年代的激烈论争,实践美学的根本缺憾已经为人所周知,因此它已经并不继续构成美学前进的主要障碍。
真正的美学前进的主要障碍,是当前的“美学研究的空心化”。无穷无尽的并非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失去了精神的重量的声音、灵魂的缺席的声音,开始充斥着美学讲坛,真正的美学研究已经有如空谷足音。
再加上对于体制内的位置与学术要津的竭力争夺,为思想而痛、为思想而病、为思想而死亡,以及为爱而忍痛、为希望而景仰、为悲悯而绝望,诸如此类美学的宝贵品质也早已被摈弃不顾。值此严峻时刻,迫切需要的已经不是什么美学论争,而是毅然地退出,退出一切美学的喧嚣,退出一切美学的浮躁,也退出一切美学的争夺,倾尽全力去做一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块石头的关心时代的中心问题但是却不绝对为时代所左右的美学的西西弗斯。
在我看来,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为美学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学新闻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记者:在美学的新千年开始的时候,您在中国美学界第一个喊出了“为爱作证”、“信仰启蒙”、“为美学补神性”,可谓是振聋发聩。
您准备如何进行这项未竟的事业? 潘知常:其实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这一呼唤,可以参看我的《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可惜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
在我看来,中国20世纪从王国维、鲁迅开始的生命美学思潮是一个真正的“大事姻缘”,只有由此入手,美学才有可能真正找到只属于自己的问题,也才有可能真正完成学科自身的美学定位。十分感谢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后旅居美国并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教授的刘再复先生、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导师林岗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导师阎国忠先生、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导师杨春时先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导师张弘先生,我的文章《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美学新千年的追问》在《学术月刊》2003年10期刊出后,他们及时撰文予以热情肯定(见《学术月刊》2004年8期),这无疑极大地坚定了我的信心与决心。
目前,继《生命美学》、《诗与思的对话》、《生命美学论稿》之后,我正在写作一部新的有关生命美学的专著——《生命的悲悯》,希望能够就我近年来所思考的重新理解美学与美学历史并叩问美学新千年的现代思路做一些深入的讨论。
其中的一些想法,可以从我的新著《独上高楼——中西美学对话中的王国维》(文津出版社2004年版)看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先看此书。此书是应乐黛云先生之命专门为乐黛云先生主编的丛书而撰写,蕴涵着我近年来所思考的重新理解美学与美学历史并叩问美学新千年的现代思路的一些基本想法。
记者:我通读了您的14部著作,感觉您的治学理路一直是坚持“理论、历史、现状”的统一,是否如此? 潘知常:是的。
在我看来,“历史”的研究、“现状”的研究就是“理论”的研究,“理论”的研究也就是“历史”的研究、“现状”的研究。对现状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反美学——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美学的边缘——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观念》、《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和《传媒批判理论》等对大众文化、媒介文化的研究上。
在国内,对大众文化、媒介文化的研究,我应该是先行者之一了。在我2001年从南京大学中文系转到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后,现状研究,也就是大众文化、媒介文化的研究也就更成为了我的学术研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
当然,不论是对于当代审美文化“现状”的研究,例如《反美学——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还是对于当代审美观念“现状”的研究,例如《美学的边缘——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观念》,我所关注的都是它们对于人们习以为常的美学边界的突破。
我所从事的,是将事实的财富提升为思想的财富、美学的财富的工作。
在我看来,这仍旧是“理论”的生命美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记者:听说您经常跟南大新闻学院的同学讲,学新闻的同学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非常有意思,那么,您是如何看待新闻传播业务与新闻传播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潘知常:这就要从中国社会的转型所导致的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型讲起了。
一般而言,知识分子有三种类型,即传统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和特殊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就是技术知识分子,他是独立的、自治的,超越于一切社会利益和集团之上,代表着社会一般的普遍要求,而有机知识分子则是与“阶级”一起创造出来,与一定的社会体制或利益集团存在着某种有机的思想联系,自觉地代表着某一个阶级,并作为阶级或阶层的代言人而出现,比如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广场型知识分子,强调的是革命和造反,显然,这种有机知识分子目前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特殊知识分子则不然,在所谓元话语——整体性知识的虚妄性已经昭然若揭,整体性知识所造就的两套宏大叙事——关于真理的叙事和革命的叙事被颠覆之后,普遍知识分子所赖以存在的知识论依据就完全被釜底抽薪,失去了立足之地。
知识分子从无所不能转而成为一无所能,特殊知识分子因此应运诞生。他的真正作用不是在于为政府代言或者为民众代言,而是从自己所处的特殊位置,通过专业分析的方式,从专业的角度内行地、深入地为公众分析问题症结之所在,提示社会所应该采取的价值立场,从而与身临其中的权力形式做斗争,揭示知识话语与权力统治之间的隐蔽关系,揭示所谓的真理与权力的不可分割,并在此基础上将对象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
这样,我们可以把现在的知识分子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知识分子即技术知识分子,这就是所谓体制内知识分子;一种是特殊知识分子,所谓体制外知识分子,体制内知识分子做的主要是对策研究,体制外知识分子做的主要是学术研究,对我来说,我觉得中国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时期,处在一个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角色很难截然分开,纯粹做一种角色,社会也没有给你留出足够的空间,因此应该尽可能一身而二任。
也经常有学生会提出问题,说潘老师您怎么自己和自己互相矛盾,一只手做业务,一只手做研究,而且绝对不把两者统一起来?比如,您为什么坚持不把自己的那些成功策划与对策研究作为学术成果发表呢?很多学者不都是这样做的吗?相对于那些学者的种种闭门造车的对策研究,您的成功策划与对策研究都是经过了实践检验的,那么您为什么不把它们作为论文与专著发表呢?我总是回答说,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就是出主意,想办法,这些“主意”和“办法”,严格地说不能作为学术成果;而做体制外知识分子,就是做研究,这就与对策无关了。
我在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的“亚洲传媒论坛”发言,讲完以后,有学生问了一个问题:潘老师,您讲了传媒中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那么,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我回答说,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学术研究不是“咨询”,也不是“对于实践的指导”。
人们往往会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其实却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我1995年在《反美学》的后记里就说过,“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说理论研究必须要去解决理论的应用问题。其实,理论研究是无法走出自己的学科边界的,也是存在着自己的学科边界的,因此“理论联系实际”只是指的理论研究要联系理论自身的实际。
也因此,我经常说,研究与业务,这是学新闻传播的学生所必须同时学会的“两手”。在学习期间不但要两手抓,而且要两手都要硬。必须强调的是,这两手不能混同,不能做着就把“业务”变成“研究”,也不能做着就把“研究”变成“业务”。
例如,如果和传媒发生关系,那么我就是一个做业务的策划人。如果研究传媒,那我就完全置身其外,不和它发生任何业务关系。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