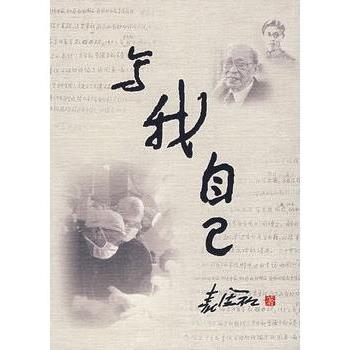写我自己裘法祖 《写我自己》 裘法祖【摘要 书评 试读】图书
裘法祖先生《写我自己》节选
三、同济大学的医学生
1934年夏天,我刚读完大学一年,我的母亲病了,当我赶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不 能说话了。母亲死了,在离我家不远的基督教教堂里给母亲举行了葬礼。我大哥在钢琴 上弹奏了德国音乐家H'andel作的Largo名曲。现在,每次我听到Largo音响,就会想起 我亲爱的母亲。
我们医学生的学制是八年,其中2年预科,5年医科,1年实习。2年预科主要是以 学习德语为主,每天上3个小时的德语课,每周要上18个小时。每个星期六要测试, 基本上都是将中文翻译成德文。同时还要学习物理、化学、生物以及中文。成绩优秀者, 才能从预科结业,升入医科就读。
我们有两个德语老师,第一年是凌翼支老师,第二年是廖馥君老师。凌老师上第一 课时就说,你们20个学生,记不住名字,他就以靠门、靠窗和第几排来称呼我们。他 每次都不叫我的名字,而叫我“门五中”,因为我坐在靠门的第五排中间,所以叫我“门 五中”。
凌老师上课时不讲文法,用一种比较“活”的教授法。在上第一课时就说:德语很 长,可以几个字连在一起,例如火灾保险公司就有30个字母(Feuerversichemngsgesellschaft),同学们都吓了。有一次,他要我们翻译Genchmacksache 这个字(个人的趣味),我们都译成“口味”,他说不对,应该译成“情人眼里出西施”。
凌老师喜欢讲不少他在德国的故事,例如他如何与德国人相骂,如何驾驶摩托车与火车 赛跑等等,因此当时中国留学生给他一个绰号“柏林土地”。据云他获得三个方面的资 助金,很富有。他读过医,也读过工,但都半途而废,没有读完,最后还是回国教德语 了。廖老师则不然,非常严肃,很正规,重视德语文法,我得益于廖老师的教育甚多。
星期六上午在课堂测试德语后有时还带着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学生去海边郊游,一面 走,一面用德语和我们聊天。廖老师的夫人也是德国人,非常贤惠;抗日战争期间也逃 到四川。据闻,解放后他去北京外语学院任教,并编写了一本很实用的德语教材。看来, 为人师表十分重要,学生会终生难忘每个老师的人品和学识。
那时同济大学里是没有食堂的,学生吃饭只能到学校外面农民开的小饭店里去订饭 吃。有钱的同学就订12块银元一个月的饭票标准,没钱的同学就订8块银元的标准; 我就是每个月订8块银元的穷学生。
我们学习非常紧张,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有时我们几个同学在周末相约骑单车去 吴淞宝山县吃汤圆,因为那卖汤圆的是一个长头发长得很漂亮的姑娘,我们都叫她汤团 (上海方言)西施。现在我已记不得她的样子了,也不知道她到底漂亮不漂亮。
升入医科后,我和谢毓晋成了知友,与另外3个同学一起住在一间宿舍里,他们是 江圣造、王辨明、过晋源。谢毓晋最大,属牛。我们四个人比他小一岁,属虎。大虎江 圣造,二虎王辨明,三虎过晋源,我最小,是小虎,这就是被人戏称的“1牛4虎”
我 们5个人之间感情很好,大家彼此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亲密如兄弟一样。我们吃在一 起,住在一起,玩在一起,一起学习。我们还组织了一支小球队,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 叫“Royal”,译成“老爷”小球队。因为谢毓晋年龄最大,我们都把他当大哥,他说什 么我们就做什么,一直到毕业都是这样子。
解剖学在医学中的学习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我们需要重复地学习两年的时间。第一年上解剖课的时候,高年级的学生坐在前面,而我们则坐在他们的后面。第二年上课的 时候,我们就坐在前面,低年级学生坐在我们的后面。
我们第一年的解剖学老师是Waldeyer教授,德国人,有些脾气:据说由于在上尸 体解剖课时辱骂了学生,他走了。第二年的解剖学老师是Hayek教授,奥地利人,为人 很温和。我在德国留学时间,听说他们二人在德国都是名教授。我学习比较刻苦用功, 每天都到图书馆去读书,所以我有个外号叫“图书馆长”。
由于重复地学习了两年的解 剖学,加之我的努力,在前期终考的时候,我考得非常好。考我的老师就是Hayek教授; 他说你考得太好了,对不起,我只能给你100分,因为没有101分。所以我的解剖学成 绩是同济人都知道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主要是我一开始就先攻读组织胚胎学,在 这个基础上再攻读系统解剖学,所以我的解剖学根底很扎实。
由于那个时候对解剖学很 有兴趣,我曾一度想做解剖学老师。到德国后,我的博士论文是有关病理学的,但我感 到病理学的尸检和镜检工作枯燥,于是就专修外科了。所以我是从解剖到病理,从病理 到外科这条路上走过来的。
需要着重提出的,攻读医学前期的两年期间,除了上午听解剖和生理、生化课之外, 下午都在进行尸体解剖,用一把刀子、一把镊子解剖人体的各个部分。记得在解剖厅内 有10多个尸体,每个尸体配给四个学生,左侧二人,右侧二人。然后,解剖学教授来 了,拿了一支色笔,在尸体上划出一个范围,一般先在上肢或下肢,要学生在一周内解 剖出来。
每周六教授又来了,拿一支小杆,指着一根肌肉或一条血管、一根神经,要学 生说出它的拉丁文名词和它的功能。如果学生回答得很对,教授会在学生卡上签字,并 接着划出另一个范围,学生就可继续解剖下去。所以,每周六我们都很紧张。二年期间, 我解剖了全身的肌肉、血管、神经以及内脏,包括脊髓和脑。
解剖尸体及格后才允许你 参加前期考试,这实在是一种非常扎实的学习方法。由于解剖名词都用拉丁文,所以在 进医科的第一年里,必须参加初级拉丁文的短期培训班,并拿到证书。这张证书后来很 重要,在我去德国继续攻读临床医学时,要先呈验这张证明,才允许你注册入学。
在这个期间,谢毓晋组织了一件在当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发起组织了一个展 示人体四肢和内脏的“解剖学展览会”。当时很多的人反对我们做这件事,我们的德国 解剖学Waldeyer教授,更不同意我们这样做。但是谢毓晋坚持要做,不仅是做成了, 而且还轰动了整个上海滩。展览会上展示的都是人体的骨骼、肌肉、血管、神经和内脏 等,大横幅上“解剖学展览会”这六个大字也是用人的骨头拼出来的。
我和我的同学们 都穿起白大褂,充当义务讲解员。由于这是一个由中国人自己举办的、免费的展览会, 很多人乘车或乘小火车从上海到吴淞同济大学医学院校区来参观这个展览会。这在1935 年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开创了一个先河,我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几张珍贵的照片;现 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这个事情做得真是不容易啊。
1936年,医科前期学习结束后,要进入后期临床学习了。谢毓晋提出来到德国留学 去。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便专程到杭州向父亲、兄姐提出来要去德国继续学习医学。我 的想法得到家里人的支持,我的二姐对我特别关心,在经济上给予了我极大的资助。
于 是,谢毓晋帮我办好了去德国的各种手续,我们踏上了前往德国求学的旅途。与我们一 同前往的还有过晋源和盛澄鉴。参加完大家为我们准备的盛大欢送会后,我们一行四人 便在1936年底登上了3万多吨的意大利轮船“Conte Rosso”号,从上海出发,前往欧 洲,开始了我们新的人生。
四、从上海到德国慕尼黑
二十世纪30年代要去欧洲,没有飞机,也不能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前去,只可走海 路,即乘船经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到欧洲。在轮船上我们住的是经济舱, 两张上下铺,一张小桌。海上的生活是无聊乏味的,虽然每到一个大港口,例如香港、 孟买,可以上岸去片刻观光,但这是有钱中国人的享受;我们没有钱,只好站在甲板上 遥望港口的车水马龙。
那几个有钱的中国人,白天打麻将,住得好、吃得好,我们一想 就来个白天睡觉,晚上向他们借来麻将牌打麻将。就这样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航行,轮船 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意大利威尼斯。
下船的那天,在早餐后看到餐厅的侍者站在餐厅 门口收小费,有钱的人给的是50或100美元;我们没有钱,谢毓晋说:只给10美元, 我们是学生,过去的时候不看他的面孔就是了。就这样我们挺过去了,那个侍者连一句 谢谢都没有吭出来。回忆起来,实在有趣。
威尼斯是一座美丽的水城,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名城。上岸后,我们买了一些桔 子来吃,当我们剥开后,发现里面都是像血一样的,以为坏了,就全部丢掉了,后来才 知道它是名贵的血桔。我们无暇浏览水城的全貌,只有稍作逗留,便离开了威尼斯。当 我们到达奥地利维也纳的时候,当地的学校已经开学2个星期了。那天正好是星期日, 所有的商店按常规都关了门,连面包都买不着。
我们都很饿了,只好多花钱去餐馆用餐。 第二天我们便乘火车前往慕尼黑。到达慕尼黑后,谢毓晋便提出,我们几个应该分开, 不应该再在一起,因为只要我们在一起便会讲中文,这对我们学习德语是很不利的。于 。是他去了弗莱堡(Freiburg)。盛澄鉴也认为在一起不利于学习语言,便离开我们去了柏 林。
我和过晋源比较保守,二人没有分开,留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继续后期(临床)学 习。当时同济大学与德国的大学之间有广泛的合作关系,只要再通过一门拉丁文初级考 试,就可以注册入学。幸亏我们在国内已取得那张拉丁文初级考试的证明,免考了,也 就顺利地注册进校学习了。
慕尼黑是英语munich的译语,德语叫München(明兴),是德国继柏林、汉堡的第三个大城市,是Bayern州的首府,当时人口约120万。德国人称慕尼黑是德国的“天 堂”,靠近阿尔卑斯山区,周围环景非常优美,又是德国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中心。
1919 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组成了国社党,是纳粹主义的发祥地,所以在希特勒执政时期,慕尼 黑也称为“政治运动首府”(Hauptstadt der Bewegung)。慕尼黑大学创建于1472年,至 今已有500余年历史,是世界著名大学之一。我能就读于此大学,并在此大学毕业,感 到自豪。
我一到慕尼黑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住处。德国有不少家庭,由于节约就空出房 间出租,在大门口挂出一张牌:“这里有住房出租”;出租的房间备有简单实用家具,包 括床上被褥。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医院、研究所都集中在一个区内,我就在这个医学区 内找住房。第一个住房在Walther街,每月30马克,连供早餐。
房东是一位老太太,非 常和蔼。我的住房在一楼,光线不足,读书的桌在窗口,而窗口正在院子里行人道边, 虽然有白色薄薄的窗帘,但不断地来往人影使得我无法集中思路。此外,一到晚上9时 房东老太太就来打门,说:先生可以睡了。我住了一个月,无法再住下去,尽管房东老 太太热情地挽留我,我还是迁到第二个住房,在H?berl街;每月28马克,少2马克, 也供早餐,房东是一对中年夫妇。
我也只住了一个月,由于房间在二楼,楼下正是一条 汽车通道,从早到晚不断地有卡车来往;另一个原因是房东夫妇经常吵架,男的打女的, 女的大哭。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第二次迁居,搬到Frauenlob街,房租每月30马克, 也供早餐。
房东也是一对中年夫妇,住房在四层楼,对面是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第三医院 (泌尿外科、皮肤科),环境非常安静。住房中还有一个房客,住在我的隔壁,是一位 兽医,叫Mayer先生,他在附近宰猪场工作,一个典型的德国南方靠近阿尔卑斯山的巴 伐利亚人。
他经常穿着巴伐利亚人的服装,头戴绿色呢帽,帽上插上一根羽毛,羊皮制的短裤,厚厚的毛袜子,重重的皮靴鞋。他下班总在夜晚11点钟左右,走上楼梯的脚 步震重,铿铿有声;开门时钥匙在门孔口乱插,然后砰的一声关了门。一到房间就将二 只皮靴先后撬出来,砰砰二声,接着就发出鼾声。我也习惯了,不在乎了。
问题是房屋 很冷,有壁炉但没有煤炭,我只好将所有的衣服穿上御寒。房东女主人Frau Schachtner 非常善良,有一个女儿,每晚总嘱我将皮鞋摆在门口,她会擦干净;每星期日早晨,她 总送上自己做的蛋糕。我很乐意住下去,一直住到我毕业到1940年。
我的经济状况很紧,特别是在1939年开始,由于日军侵略到上海、杭州,二姐已 无法再寄钱了;她已前后五次共资助了我4200美金。我每月只用70马克,其中30马 克付房租,剩下来的40马克用于吃饭和买书,幸而德国读书是免费的。
早餐是由房东 供给的;中餐就去专供学生用的饭店吃,每餐60芬尼,加上小费是65芬尼。晚上就吃 黑面包,抹上一点果酱果腹了。果酱可以在小店里自己拿空瓶子去另买。由于租屋里没 有洗澡设备,每周约好过晋源同到公共浴场去洗;衣服就送洗衣店秤重后付钱,一周后 去取。这样,三年大学生生活渡过来了。
在国内我自己认为德文是很不错了。但到了德国却变成了聋子和哑巴了。慕尼黑 人讲话很快,又带有地方口音,实在难懂。过了半年听和讲才好了一些。举一个例子, 德国人将“您”和“你”分得很清楚。“您”(Sie)是尊称,“你”(Du)是亲密称;对家人、对16岁以下的孩子都称“Du”。
一次到公园里散步,看到了一个很可爱的男孩, 我就问他,您几岁了;他忽然大笑着转身去告诉他的母亲说:他称我Sie呀!我才明白, “您”和“你”是有分别的。好朋友都相互称Du;对与长者或老师或不熟悉的人,都 称Sie。如果有朋友,感情较深,也要长者先提出Du称,然后相互就用Du称了。 在我读完医科第一个学期后,在1937年秋天,我忽然发现在直肠下端长有一个长 蒂的息肉,当时我就去外科医院手术。
德国大学生的医疗费是全免的,而医学生病了都 是由外科主任或副主任亲自手术的,这是传统,教授对学生是非常关心的。虽然我是中 国医学生,并且刚刚开始学业,仍然享受着这样的优待。住了一个星期医院,回到我自 己的住处,当时正是深秋,满地铺着褐黄色的树叶,冷风迎面吹来,我一个人慢慢地走 在街上,想起了祖国,想起了家乡,不禁哭了!此情此景到今日还深深地印在记忆中。
1939年,我获得了二个奖学金,都是我的博士导师Borst教授亲自签字推荐的。 一个是Wolf奖学金,三个半月,共420马克;另一个是洪堡奖学金(Humboldt-Stiftung), 每月150马克,共两年七个月。这样大大减轻了我的经济压力,不但完成了我三年的学 业,并开始了在慕尼黑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生涯。
在慕尼黑当时只有一家中国饭店,在Augusten街,老板姓徐,温州人。我和过晋 源有时也去吃一次中国饭,每餐1马克,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享受;同时也可以见到几 个中国留学生。当时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约有20人,其中有马节(经济学)、 徐维铸(经济学)、庄孝德(细胞生物学)、徐邦裕(制冷工程学)、许巍文(化学)、江 希明(生物学)和他的夫人徐瑞云(数学)以及当时在慕尼黑进修军事的蒋纬国。
记得 还有几位学医的女同学,一位叫李淑家,一位叫叶景恩(同济大学李国豪校长夫人), 她们都住在慕尼黑大学特设的女留学生宿舍;她们会做中国菜,有时也请我们去吃饭。 在慕尼黑的中国留学生相处得非常融洽,有时还一起去慕尼黑近郊Stamberg湖游乐。
这些情况都在二战开始前,1938年、1939年期间。等到二战开始后,气氛紧张,大家 都钻于学习和工作,彼此的交往几乎中断了。过晋源在毕业后也去维也纳大学医院工作 了,而我则忙于手术,且经常和我妻子在一起了。
五、坐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教室里
1937年2月我开始在德国攻读临床医学(医科后期),前后共三年,到1939年冬毕 业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需要大批医生,因此,医学学制由一年二个学期改 为一年三个学期(Trimester),这样,就等于缩短了一年学习时间,我遂于1939年冬比 在国内的同班同学提前一年毕业了。
德国临床医学的课程与国内的课程不很相同,三年内要学完14门必修课,方可参 加毕业考试。14门必修课是:病理学、药理学、微生物和卫生学、局部解剖学、病理生 理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神经精神病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皮 肤性病学和法医学。
由于上课的地点分散在不同的医院或研究所,我和过晋源各买了一 辆旧的自行车,在短短的课间休息时间,赶着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上课。例如早晨 第一课在内科学院听课,接着就去病理研究所听课。好在这14门必修课的听课和见习 时间完全可以由学生自己来安排,也就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分散安排在三年中的八个 学期中,完成上述所有课程的听课和见习。
临床学科的上课完全不同于国内情况,不是“填鸭式”的,而是“启发式”地要求 学生独立思考。例如上外科第一课,老师先介绍了几本教材,供学生阅读参考,接着就 以示范的方式授课。国内老师的授课是按教材系统地讲授,只见书本,不见病人;而德 国则是联系典型的病例进行示范授课。
今天是一位胃癌病人,明天是一位颅内肿瘤病人, 而后天是一位上肢骨折病人;老师简述了病史,提示了X线片,也可能就在课堂里施行 复位。总之,要学生自己去阅读书本,自己去思考,上课只是示范一些典型常见病例。 每次上课要叫四个学生下来问答,问答一些基本知识。
在一个或两个学期中上完了一门 课程,就可取得一张听课证明,等到14门课程读完取得了14张听课的证明,就可以到 大学去申请毕业考试。如果不勤奋,或不去上课,就无法报考,只得延长学习时间。我 遇到几个德国同学已经读了5~6年,还未读完,一年一年拖下去,人们都称他们为“老 学生”。
一次在上妇科课时,我可进手术室观看手术;当教授自腹腔中取出小儿头大的子宫 肌瘤时,我忽然晕厥过去,手术室护士(修女)立刻抬我到走廊里吸氧,我恢复了,但 我很伤心,看来我作不了“外科医生”。
德国的大学里流行着一句话,叫做“大学生自由”(Studentenfreiheit),也就是不但 学习时间的长短由大学生自己来掌握,而且可以转到其他的城市学习,例如柏林大学的 大学生可以转到慕尼黑大学来继续学习,也就是德国北方的大学生来到德国南方来读 书,或者相反。不少大学生喜欢这样转学,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可以了解当地的风俗人情、名胜古迹。
对我印象很深的是上临床医学课的场面。讲课的老师都是各学院或研究所的第一把 手,教授或主任。他们都很讲究仪表,熨得平直的白大衣、白长裤、白的领带、白的皮 鞋,后面跟随着一大批助教、讲师,一样是衣着整洁,也同时站着在教室的两边听课。 大学生不起立致敬,常是用手敲打桌子表示欢迎;如果有不同意的情况,学生就拖擦鞋 底来表示。
记得有一次,第一内科学院院长、血液病著名教授来上课,在他的白大衣口 袋中的电筒还亮着,学生就拖擦鞋底表示有意见,当时那位教授搞不明白,幸而一位助 教提醒了他立即关闭了电筒,学生立即敲打桌子,表示高兴。 著名的教授上课时,庞大的梯形教室坐无虚席,连站立的空间都满了。
记得1937 年世界著名的整形外科Lexer教授上课时,就是如歌剧院一样的场面。Lexer教授在上 课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外科学是一门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综合”,这句话到今天还深 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并影响了我一生的外科工作。
我和过晋源学习非常勤奋,上课时总抢着坐在第一排。寒假、暑假也不休息。三年 中我们没有去旅游,也没有看过一次电影,寒假、暑假时期,上午都去医院见习,下午 就准备博士论文课题,极力争取按时完成所有必修课程的听课和见习,按时报考、按时 毕业。
三年的刻苦攻读我坚强地挺过来了。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惊奇自己竟有如此持久的 动力。特别在最后一个月考试阶段,我经常失眠。由于我的住处离慕尼黑十月啤酒节广 场很近,每晚在睡前就去那里跑步一圈,这样才使我得以入睡几个小时。
作为外国留学生,在德国可以享受一种优待的学位考试,即所谓Rigorosum,也就 是写一篇论文,参加四门临床学科的考试,就可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当时,我与过晋 源商讨,决定放弃这种优待,要同德国学生一样,先参加德国的国家考试,再参加博士 学位考试。德国的国家考试非常严格,都是口试,分四人一组进行,必须在一个月中考 完上述的14门课。每门考试要半天甚至一整天的时间。
例如病理学的考试,上午口试, 先考问人体病理标本,继而要看五张病理镜片,作出诊断;下午还要自己做一个尸体解 剖。我在一个月(1939年9月)里完成了所有14门课考试,除了2门课是“II”(病理 学、儿科学)和1门课是“Ⅲ”(药理学)外,其他11门课都是“I”,因而获得总成 绩“I”(最高分),但精神却疲劳到极点,体重也减轻了5公斤。
随后,在同年11月 再参加了博士学位答辩。由于我的病理学博士论文在两个暑假(1938、1939)期间己完 成,因而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答辩。
外国留学生在德国读博士学位,不用参加国家考试,只参加一种优待的学位考试, “Rigorosum”,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的情况,这在国内是不清楚的,以为都是“医学博 士”,而实际上是有分别的。只有通过了国家考试,才有资格获得医师执照,在德国可 以做医生。因此,如果现在我回到德国去,仍然有资格做医生。另外,我在1945年12 月获得了德国“外科专科医师”的资格证书,这是一项不很容易获得的荣誉。
1938年我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病理研究所拿到了博士生的课题,导师是世界著名的 病理学家Borst教授,具体指导老师是讲师H?ra博士。研究的课题是“肥大性阑尾炎的 病理机制”。该研究所接收了一个成人拇指大的阑尾,不是肿瘤,也不是一般的炎症, 病理诊断不明,因而Borst教授认为是一种毒性较低的结核杆菌所致的病变,但没有证 据,必须要在标本里找到结核杆菌。
我查阅了不少文献,也有类似的报道,但仅仅是一 种推测,没有证实。我就在病理研究所自己动手,将标本作了许多的切片,用不同的染 色方法,终于用Ziehl-Neelsen染色法找到了一条结核杆菌。诊断明确了,导师很高兴, 就要我写成论文,作为博士论文发表。
实际上这是一个病例报道,可是工作量还是不少 的。当然,同现在的博士研究生论文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太简单了。但在70年前的时期,已经算是一篇博士论文了。
我的博士导师Max Borst教授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德国政府授予他为“国家顾问” (Geheimrat)称号。他身材不高,较稳健,经常结一条红色领带。他撰著的《病理组织学》是一部经典著作,有几个不同文字的译本。他热爱古典音乐,担任一个医生交响乐团 的指挥。Borst教授的性格开朗,富于幽默。医学生都知道国家考试中的病理学考试特 别严格,考试中要看五张病理镜片,并作出诊断。
这对一个医学生来说,确实是困难的。 因此,在病理研究所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在考试前去找一位老技师,他的身材有些 像Borst教授,给他5马克,就可以拿到五张镜片和诊断;在考试时也由这位老技师递 给Borst教授这五张镜片。1938年,从另一个城市转来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参 加国家考试前也去病理研究所寻找那位老技师。
恰巧在研究所的大厅里遇到了Borst教 授本人,这个学生认为他就是那位老技师,就给Borst教授5马克,Borst教授接受了, 也给了这个学生五张镜片。第二天,我们上课时,Borst教授一开始就说,在座哪位同 学,我要还他昨天付我的5马克。这件事引起了整个教室的学生长时间敲打桌子;表示 高兴和赞扬。今天回忆起当时的场面,不禁要失声大笑。
Borst教授不幸于1946年因车 祸去世。1979年我去德国访问时,见到了Borst教授的儿子,Hannover医学院的著名胸 心外科教授,通过他我到慕尼黑拜访了Borst教授夫人,我的师母,受到她的亲切接见。
过晋源的博士生课题是有关维生素C的作用,他的导师是维生素C的开拓者,叫 Stepp教授。过晋源每日喂养大鼠,非常辛苦。他的论文成绩获得“I”,而我的论文成 绩是“II”。相反的,国家考试我的成绩是“I”,而他的是“Ⅱ”。这样算来,我们两 人各有长短,实际是拉平了。
在这里需要声明的,我的大学毕业和博士学位证书上的名字是按德语拼音:Tjiu Fa-dsdu;回国后改为英语拼音:Chiu Fa-tsu;解放后一律按现代汉语拼音:Qiu Fa-zu。 我的生日也有了改动,当时我只知道我属虎,冬天出生。
按中国老的习惯,生日都不记 年月日,只记生肖;出生后到第一个春节就是一岁,也就是生日,因此我算一算是在1915 年生;为了容易记住,我自己写了生日是1915年11月15日。回国后我问了父亲,他 查了年历本,我的真正生日是1914年12月6日,在德国所有证书上写的都错了。
我们在三年的临床医学学习时期,最使我不高兴的是同学们认为我们是日本人。记 得有一次,大学生学生会组织一次去慕尼黑郊区一个温泉地区参观,晚上开会时我和过 晋源进入会场,大家喊着:欢迎日本人。
当然,我非常不高兴,我鼓起勇气走上台阶说: 我们不是日本佬,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也能够在慕尼黑大学留学!当时,会场一阵哑 然,接着是一阵掌声。今天,祖国强大了,富裕了,中国人站起来了。只有我们老一辈 的留学生才有这样的亲身体会!
六、开始我的外科生涯
1939年11月中旬,我和过晋源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毕业了,并且获得了医学博士 学位。我们十分高兴,就在专供学生用餐的饭店里,晚上在地下室打保龄球的地方,开 了一次小小的庆祝会,邀请了6位在慕尼黑大学读工的同学,喝啤酒、吃小猪排。当时, 二战刚刚开始,德国的食品供应还很充裕,还没有实行配给制,所以大家还可以大吃一 顿,谈笑欢乐一直到深夜才兴尽告别。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还去看了电影,在德国第一 次看电影,片名叫:Jud Süss(犹太人Süss),是辱骂污蔑犹太人的影片。我们又作了一 次旅行,到了柏林、Nürnberg(审判二战战犯的城市,我还拜访了名画家Dürer的坟墓)、 Leipzig和Dresden四个名城,回到慕尼黑已经12月中旬了。
我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思 考,毕业后专哪门医学专业。过晋源已决定做内科医生,我考虑再三决定做外科医生。 我的解剖学底子很扎实,我的博士论文又是病理学方面的,由解剖到病理,再由病理到 外科,这条路我是走定了。
我选择了当时最大的市立Schwabing医院,有2000多病床,设备齐全,又是慕尼 黑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在1939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鼓着勇气,带着毕业证书和 博士学位证书去见Schwabing医院的外科主任H.Bronner教授。Bronner教授很客气, 问了我一些问题,就同意我立即上班工作,但没有薪金,做所谓“志愿医生”
(Volont?rarzt)。Schwabing医院的外科有6个病区,男女各一半,总的病床是300张, 在当时算是很大的外科了,而病种又很多。不方便的是离我的住处太远,每日早晨6点 半起床,要乘7站电车才能到达医院。这样的情况大约维持了半年之久。
德国大医院的各科主任都有自己直接支配的病房,称谓“私人病房”(Privatstation), 都是单人间,设备较好。对这些病人的查房、诊治或手术的费用都归科主任所有。之所 以有这种的规定,为的是提高科主任的待遇,安心工作,不需要到院外去兼职或手术了。
医院还配给科主任一个助手,帮助处理对私人病人的诊疗工作;Bronner教授当时的助 手是Schmidt医生。外科手术的官方规定费用范围很宽,一个阑尾炎手术定价在500-5000 马克之间;科主任可以按病人的经济情况定出价格,可能是1000马克,也可能是5000 马克。这种制度到今天在德国还存在。
德国医院的所有医生都享有每年一个月的休假,休假的时间由每个医生自己决定, 预先通知主任,主任同意就行了。1940年夏在一次晨会上,Bronner教授忽然说:Schmidt 医生,您今天就可以休假了,这个月由裘医生来顶替您。当时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真 是受宠若惊,可能由于我平时工作十分勤奋,他看在眼里,就作出了这个决定。
一个月 很快过去了,Schmidt医生休假回来了,Bronner教授在晨会上又说:Schmidt医生您可 到男病房二区工作,裘医生就继续作我的私人助手罢。从此,我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查房, 用德语写好病历,妥善地处理他所吩咐的各项医嘱。
由于Bronner教授亲自接待新病人, 电话也很多,还有许多信件要口述由女秘书打字,所以不少时间我在等候中渡过的。女 秘书Frau Hofberger非常和蔼可亲,事事都在关注我。有趣的是,病房的姆姆(修女, 信天主教的护士)每天上午10时准备一份中间餐给Bronner教授,但每次总从中取出几 片香肠,一片面包加黄油,留着给我吃。此情此境还历历在目。
兼任了Bronner教授的私人助手后,我就受聘为慕尼黑市的正式职工了,月薪300 马克,加上Bronner教授私人给我100马克的补贴,我的经济情况很好了。我在医院里 有了一间住房,三餐饭是免费的,因此我就从旧居搬出来,房东女主人要哭了。同时我 就信告Humboldt基金会,谢退了每月150马克的奖学金。
这是1941年7月的事情。 Bronner教授是很有名望的,他是著名外科学家Frey教授的弟子,而Frey教授又是 著名外科学家Sauerbruch的高足。因此,我也就有幸成为Sauerbruch-Frey-Bronner的传 人了。Bronner教授工作非常勤奋,治学十分严谨,一丝不苟;每日工作10个小时以上,
我也跟着他一样勤奋,恪尽职守。记得有一次,我们快步从一个病区到另一个病区,忽 然他停了下来,说:走慢一些罢,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走入坟墓里;我们相对笑了。尽管 非常辛苦,但是我在他的指导下管理病人、做手术、值夜班,学到了不少技术和良好的医风。 Bronner教授对病人极端负责,关爱有加,是一个医德高尚的人。
他不仅对科内的 医生要求很高,而且严以律己。每天早晨7点半他准时到科室参加晨会,听取六个大病区 主治医师的汇报。每星期二上午他带领全体外科医生到该院的病理解剖研究所参加死亡 病例尸体解剖的讨论,对上一个星期死亡病例诊断的正确性、手术的适应症进行严格的 审查。
每星期四晚上全体医生必须参加新文献报告会,相互交流在过去一周内各自所 阅读的文献内容。他对下属医生非常严格,记得有一天一位年资较高的医生早晨上班前 喝了酒,呈微醉状态,他不但毫不留情地禁止该医生做手术,并立即辞退了他的职位。
他对我的要求也很严格。我在外科工作一年以后,才允许做第一个阑尾切除术。在我做 第三个阑尾切除手术时,病人是一位中年妇女,术后第五天这位病人忽然死去。尽管尸 体解剖没有发现手术方面的问题,但Bronner教授以严肃的眼光对我说,“她(死者)是 一位四个孩子的妈妈。”65年前的这句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始终教育着我, 鞭策着我,影响了我65年外科生涯中的作风和态度。
1943年德国开始溃败,慕尼黑不时遭到轰炸。记得有一天上午,Bronner教授做手 术(胃癌根治术),我任第一助手。恰在此时响起警报声,美国飞机就在我们上空呼啸, 爆炸声不绝于耳。当时,我直觉地感到会有危险,便力劝Bronner教授暂停手术,连推 带拉地将手术台和病人拖出手术室。
我们刚一离开,一颗炸弹正好落在那里,好险呀! 现在想起来还冷汗直冒。鉴于这种情况,医院建造了一套地下手术室,钢筋混凝土墙壁 厚达2米,设备十分齐全。我们在里面日夜手术,遇到轰炸时,能感受到手术室在地下 深处晃动,像一条船在水里摇摆一样。由于建筑十分坚固,没有受到丝毫损害。
我在医院里工作并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总的来说还比较顺利,主要是我绝对不谈政 治,只是埋头苦干,经常代他们值夜班,也从不休假。他们需要我工作,而我又需要尽 快尽多地学习到本领。我和大多数德国同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只有一个外科医生名叫 Hess,是SS(Schutzstaffel,党卫军)例外。
他竟向医院领导提出,不许我检查德国女病人,幸而我的恩师Bronner教授把他顶了回去,使我度过了这个难关。还有一次晚上, 我和我的德国妻子(当时她是慕尼黑大学医学院学生)到慕尼黑市政厅附近一个咖啡馆 喝咖啡;由于德国政府特别照顾中国人,每月配给大米数斤,我就请我妻子代购,给了 她粮票和钱,这个动作被秘密警察钉住了。
当时德国已呈战败迹象,夜间实行灯火管制。 当我们走出咖啡馆时,从黑暗中突然伸来一只大手抓住我的右肩,并向我出示他的证件: 秘密警察。我大吃一惊,即出示了我的证件: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第二天,又来人调 查,这一次又是我的恩师Bronner教授保护了我,我仍然平安无事。以后,我便非常小 心,不再和我的妻子公开在街上一起行走或乘车了。
希特勒的口号是只有雅利安种的德国人才是优秀的民族。他极力排斥犹太人,犹太 人是劣种人。我亲眼看到不少现象,听到不少消息:慕尼黑的所有商店,包括食品店, 玻璃大门上都贴有一张黄色纸条“犹太人禁止进入”(Jud eintritt verboten),我在Frauenlob 街的住房大门右侧,一爿小小面包店也贴有一张同样的纸条。
有一天,我的妻子走在公 园里,一位犹太老妇人低声问我的妻子:姑娘,可否请您给我在电话亭里打个电话,当 然我妻子同意了,这是连电话亭也禁止犹太人进去。在慕尼黑市政厅附近的一家犹太人 经营的很大百货公司,一个夜里就被SS抢劫一空。
我看到走在街上的犹太人,大都是 贫困的、没有预先逃离德国的,在衣襟上都有一个园形黄色标记“厂(犹太人)。二战 开始的一、二年,我经常看到列队行进的“义务劳动”(Arbeitsdienst)青年人,肩上托
着铲把,唱着“我们去,我们去,我们去打英国,??”(wir fahren,wir fahren,wir fahrengegen England??”。
二战结束的前二年我经常听到一首流行歌曲,叫做"Lili Marleen",唱 的是一个在军营大门口路灯下站岗的德国兵想起他情人的歌词,这首歌流行得很快,军 队里的士兵都唱起来了,大大降低了德国军队的士气,曾一度被禁唱。
这些点滴情况, 都是我亲自看到的、听到的。1942-1943年,德国军队在各条战线上开始呈崩溃现象,我耳闻在慕尼黑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一件是希特勒在Bürger啤酒厅作报告,听者人山人海,在他离开会场后的片刻突然发生定时爆炸,死伤了不少人。那次谋杀希特勒没有成功。另一件是慕尼黑大学的二个大学生,Scholl兄妹,与几位教授和同班同学建立了一个反纳粹的“白 玫瑰”组织。
Scholl兄妹在慕尼黑大学大楼屋顶上散发反希特勒传单,被SS抓住了, 很快Scholl兄妹和几位教授被绞死了。对这些事件我绝对不闻、不问、不说。我只是一 心一意作好我的外科工作,这样来保护我妻子和我自己。
1944年初,慕尼黑己日夜受到空袭,德国的地面高射炮已失去效力,没有还击的能 力,后来就连警报系统也失效不灵了,只能由青年队员骑着自行车,边吹哨子边叫喊, Alarm!
Alarm!要人们进入防空地道。每次轰炸后都有大批受伤百姓涌入医院。医院床位 己远远不够,受伤者都躺在地上。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决定一分为二搬迁到离慕尼黑较 近的两个小城,一处在Brannenburg,一处在Bad T?lz,每处有病床200张,以外科为 主;我被任命为Oberarzt(相当于副主任医师)派到Bad Toelz主持外科日常工作,而Bronner教授则每两个星期来几天,查病房并做手术。
每周有一批病人自慕尼黑转来Bad Toelz治疗,另有一批病人治愈后转回慕尼黑。就这样,我又工作了两年(1944—1945年)。 应该肯定,60年前德国外科手术是比较先进的,培养的外科医生技术也比较全面。
由于 当时外科尚未分成不同专科,所以德国大学教学医院外科医生都能掌握从头到脚的常见 手术。大学教学医院的病种多,手术机会多。我经常每日要做两台大手术,学到了不少 技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临床经验。从这方面来看,我是幸运的。
《写我自己》裘法祖教授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实事求是地写出来,书中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用朴素的文笔写自传而不是用华丽的文字搞文学创作,书中只求写实,绝不夸张,也不掩饰作者自己的真情。他说“我是一个外科医生,应该做到坦率和诚实。” 《写我自己》由作者裘法祖教授自己执笔,他要的是真实、朴素、平直的回忆,不是浓笔五彩的传奇。
94岁高龄,仍然是百忙之间抽空写作。他写了他的老家,回忆童年到少年,写了同济大学的医学生,写了从上海到德国慕尼黑的生活经历,写了坐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教室里感受,怎么样开始他的外科生涯,回忆了在Bad Tolz市工作和生活,讲述了在***中磨练,回顾了编著《黄家驷外科学》的全过程,经历了从小家变成了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