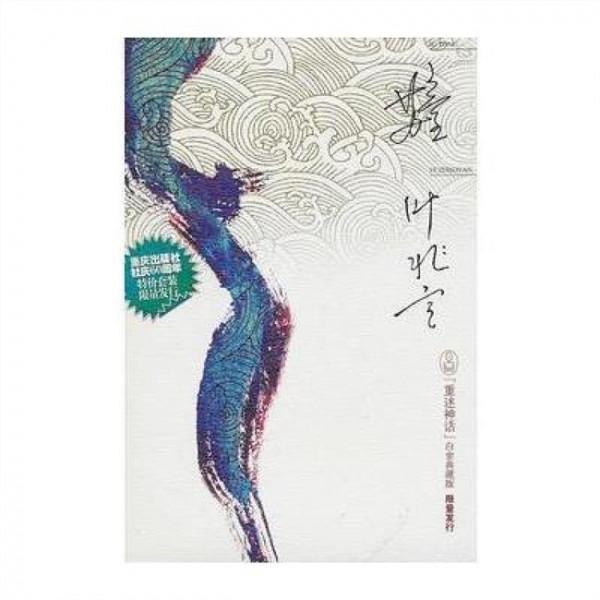引以为戒:叶兆言父亲的写作悲剧
叶兆言是南京作家。此前我只知其名,想不起看过他什么作品。最近读了他的《陈旧人物》,觉得不错。又借了《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叶兆言》。发现其中的散文《纪念》非常好,远远好过其中的几篇小说。我想,这很自然,《纪念》纪念的是他父亲,而且是养父,不可能写不好。
叶兆言的生父,他说不知道是谁。他一岁多就被他养父领养。所以,《纪念》开篇第一句就是,“我对父亲的最初印象,是他将我扛在肩上,往幼儿园送。”这个父亲叫叶至诚,当过《雨花》的主编。
叶至诚的父亲是叶圣陶。看完了《纪念》,我特地把《大学语文》找出来,翻到《潘先生在难中》,看了一遍。已经至少10年没再看过了。想起简杨曾说,我在《巴黎一日流水账》里,很像潘先生在难中,不禁莞尔。
亦叹白话文的演变速度惊人。叶圣陶这篇1925年的小说,语言上已经有许多地方,特别是虚词,读起来感到疙疙瘩瘩的,例如“可是也不能全乎没有肇端”。而读普鲁斯特一百年前写的法文,并没有感到这样的突兀和拗口。由此,想到一百年后,如果有人读到我写的东西,是不是也会觉得语言很不相同?
《纪念》一文最令我感叹,以至有些兔死狐悲,脊背发凉的,是叶兆言分析他父亲为什么写不出来作品。兹抄录如下,引以为戒。
我考上大学的第二年,父亲的冤案得到了平反。老朋友们出了一口恶气,又重新聚到了一起,高晓声陆文夫方之像文学新人一样在文坛上脱颖而出。父亲重新回到作家协会,立刻贼心不死,开始写那些“有自己”的文章,写自己曾经熟悉的散文和小说。
父亲没有像他的老朋友那样大红大紫。我想内心狂妄的父亲嘴上没说什么,心里一定不会太好过。“有自己”的小说并不是那么轻易地就能在文坛上站住脚跟,尽管父亲遍体鳞伤,可惜他写不来“伤痕小说”。父亲显然不是那种争名夺利之辈,但是也许是过去的岁月里太寂寞的关系,父亲对于自己新写出来的作品毫无反响感到不堪忍受。
写作的人,对于自己暂时不能被人理解通常有三种态度,一是义无反顾地向前走, 一是顺变改造自己的风格,一是干脆搁笔不写。父亲选择的往往是最后一种。事实上,粉粹“四人帮”这么多年来,父亲真正动笔在写的日子并不多。
父亲的作家梦永远有些脱离实际。父亲想的太多,做的却又太少。在一个不能写不该写的时代,父亲始终在硬写,而在一个能写应该写的时代,父亲写得太少。在写作上不像自己的老朋友们那样勤奋,不能忍受一点点干扰,是父亲未能达到理想高度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过去的特定的时代里,由于大家都不能写,因此写与不写没什么区别,然而进入了新时期,大家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写与不写,便有了严重不同的后果。
父亲病危期间,我一遍又一遍地想到父亲的写作生涯。让我感到吃惊的,是父亲自认为可以留下的作品,不到三十万字。这个数字真是太少了,因为其中还包括了父亲少年时代写得十多万字。一个作家真正能留下三十万字,并不算太少,可是面对父亲终身要当大作家的狂妄野心,面对父亲多少年来为了文学的含辛茹苦忍辱负重,三十万字又怎么能不说太少了。父亲毕竟一辈子都在写,除了写作之外,父亲毕竟什么也没干好过。
成为一个好作家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父亲常常教导我,也常常这样教导那些向父亲倾角的文学青年,他常常说思想的火花,如果不用文字固定下来,就永远是空的。想象中的好文章在没有落实成文字之前,也仍然等于零。父亲自然是意识到了不坐下来写的危险性。
父亲常常有意无意地躲避写作。不写作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正如福克纳所说的那样:“如果这个人是一流的作家,没有什么会损害到他写作。”父亲似乎永远处于一种准备大干一番的状态,不断对我宣布要写什么何打算怎么写。
我听过父亲说过许多好的甚至可以说非常好的设想。写作对于父亲来说太神圣了,正因为神圣,父亲对于写作环境的要求,便有些过分苛刻。作家太把自己当回事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事,并不是什么人都能理解写作神圣。作家永远或者说最多只能当个普通人。作家当不了高高在上为所欲为的荒地。没多少人会把作家不写作的赌气放在眼里,不写作的受害者无疑还是作家自己。
对于一个太想写太相当大作家的人来说,放弃写作是一种自我虐杀。不写作的借口永远找得到,不写作的借口永远安慰不了想写而没写的受着煎熬的心灵。在这最后的十几年里,宝贵的可以用来“写自己”的时间,像水一般在手指缝里淌走了。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1957年的“反右”,文化大革命,修改了那些几乎毫无价值的剧本,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也许只有我一个人能理解父亲想写却没写的痛苦。也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父亲所找的借口每一个站得住脚。过去的这些年里,作为《雨花》主编,无论行政或者稿件,事实上父亲都很少过问。主编只是一个优惠的虚衔,只是一种享受的待遇。
至于编祖父文集这一浩大工程,事实上也是伯父一个人在编,祖父的文集已出至十一卷,父亲充其量不过是浏览一遍三校样。祖父在八十多岁的时候,每天伏案仍然八九个小时。伯父更是工作狂,现在已经七十多岁,独自一个人能干几个人的工作。让人疑惑不解的是,为什么祖父的这种优良品质,在父亲身上便见不到了。祖父和伯父都在写作之外,干了大量别的工作。
我丝毫没有在这里指责父亲的意思。我的眼泪老是情不自禁地要流出来。父亲已把他热爱协作的激情传给了我。我是父亲想写而没写出来的痛苦的见证人。世上上,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总是婉言地劝父亲注意身体,写不写无所谓。事实上,是父亲一遍遍地和我说他要写什么,父亲永远像年轻人一样喜欢摆出大干一番的样子。事实上,他不止一次开始写,又不止一次被不能成其为理由的理由中断。
我感到悲伤的是,既然不写作给父亲带来了那么大的痛苦,父亲为什么不能咬紧牙关坚持写下去。既然父亲对写作那么痴心一往情深,要写作的愿望那么强烈,为什么不能振作起来,勇敢地面对那些微不足道的干扰。
即使在最后的日子,父亲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会魂归仙岛。父亲即使死到临头,仍然顽固地相信自己会成为好作家。父亲没有认输,在精神上,父亲仍然是胜利者。父亲带着强烈的作家梦想散手人寰。在另一个世界,父亲仍然会继续他的作家梦想。父亲的故事永远不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