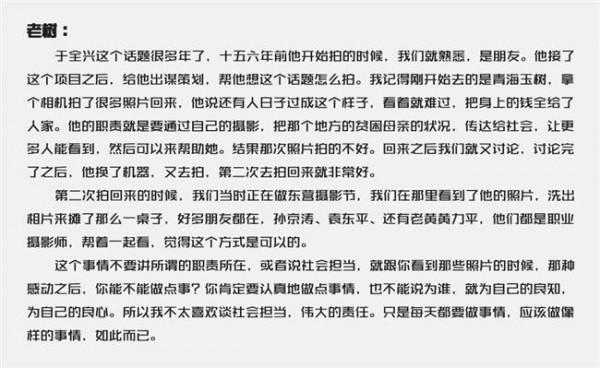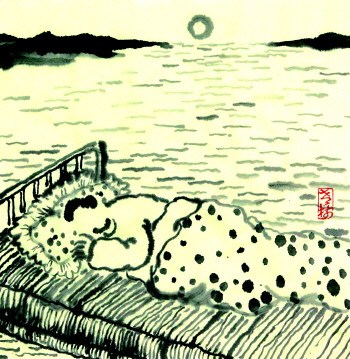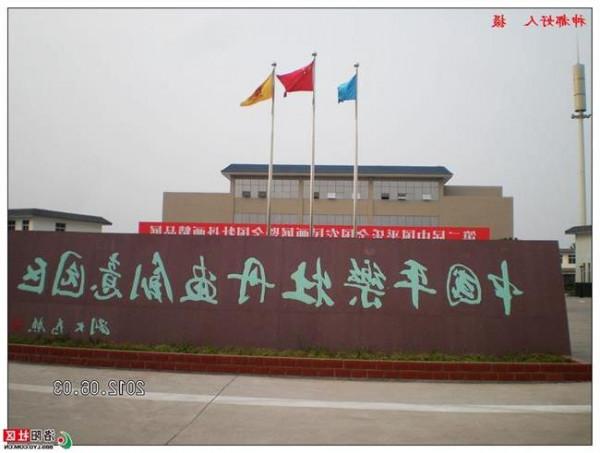刘树勇的画 刘树勇谈新书《在江湖》:画出向往之诗意
图为《在江湖》插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图为封面。
这次老树出了他的新书《在江湖》,画是从3000多幅中精选的200多幅,文是老树谈自己的画和诗,搭配着看,更能理解他的画中世界。我们不妨听一听他如何看待自己的画与诗。
——编 者
生活中的一切经验,身体的经验、人伦日常的经验、知识文化的经验,包括绘画经验,都是个人生命经验的一部分。生活与绘画两者是一体的,无以分别。
中国传统绘画总体来说还是农耕文明时代的产物,所以关注的题材基本上是乡村题材,山水、人物、花卉、走兽,跟现代城市文明没有太大关系。我从小生活在鲁中丘陵地带的乡村,北方的大部分植物、动物,包括山水的空间变化,都是我日常经验的一部分。
一个人循四季变化经常见识这些事物,这些事物成了他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这个记忆在他脱离这个环境之后就会非常的深刻和重要。比如我画一株野草。在城里人看来就是一株野草,形诸笔墨,如此而已。
对我来说,这株野草就很复杂。因为在我小时候,夏季每天放学之后最要紧的活儿是打猪草喂猪。哪些草叫什么名字,猪是爱吃的,哪些野草猪是不爱吃的,我都知道。所以我画草的感觉就跟所谓的写生是不一样的。这里面会有我的经验与记忆,画出来,包括写些词儿题识在画上,感受就会不一样。
我们今天会很喜欢古人画的山水花卉翎毛草虫,那些诗文题识也好,却很少想到,他画的东西其实就是自己彼时彼地切身的日常生活经验。我们有时会感慨今天的人没有古人那么丰富的想象力了,其实是古代的那种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已经没有了。
古时的诗人写诗并不都是靠想象,更多是直接描写眼前所见所感、设身处地的真切经历。1984年我在黄山游览,晚上住在西海一间很大的板房里。我裹了件军大衣一个人往北海散步,路过一片很大的松林,就在一块大石板上坐下来,听松涛的声音。
四周极安静,月光从松针的缝隙里漏下来,斑斑驳驳地照在松软的地上、山石上。坐了一会,忽然感觉屁股下面湿了,原来是山间流出的泉水,我一下子就想起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诗句来。我们写不出这样的诗句,不是缺少想象力,而是没有了这种经验。我们怀念那些年代、那些情怀,也是因为再也回不去了。
我写的题画诗多为六言,即古体诗的格制。古体诗的最大好处是朴素、自由,没有近体诗那么多的讲究和限制。今天人们一说到中国古诗,就是押韵、对仗、平仄那一套格律。其实这只是一半,也就是唐以后的近体诗。唐以前广泛流行的古体诗,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乃至杂言都有,押韵、平仄这一套就更不大讲究。汉代的乐府民歌,以及大量的古体诗,在格律上没有那么苛刻的要求,自由表达显然是第一位的。
我们上大学时,南开大学有很多老先生教课,邢公畹、李何林、李霁野、朱维之,他们古代诗文的底子很深。叶嘉莹当时回国讲学,最早就是给我们这个年级讲宋词。她秉承的是顾随的讲法,完全是体验性的。她在讲台上侧向着学生走来走去,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完全沉入到词境里面去了,走到宋人的庭院和山水里去了。
她还会唱诵式的吟咏之法,她吟咏古人诗词的样子,仿佛一位宋时女词人花前月下走来走去,不仅是心境的进入,而且是身体的进入。听她讲课,可以说是处处落花流水、天天晓风残月。
集诗书画印于一体,是中国传统绘画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苏东坡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他是诗词、文章、书画等各方面的大家,是对诗画之关系有深切的体验和理解的人。《宣和画谱》中也说,“文章翰墨形容所不逮,故一寄于毫楮”。
张彦远说得更明确:“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可见,古人很早就明白不同的语言方式各有长处和局限,只有借助不同的语言方式互为补充,才能完整地表达出一个丰富多样的对象世界,以及个人对这个世界生发出来的更为复杂微妙的内心觉受,使得一张画的整体信息更为丰富和具有深度。
我想,最重要的是画家心中有没有话要说,其次,是否清楚且充分地说出来了。至于用绘画的语言,还是补充使用其他语言,都不重要。我希望,文字在画面上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是文字意象的组合在读者头脑中构成具有空间感的情境,而这个情境又与画面的视觉空间融为一体。另一个作用,是希望文字书写能够成为画面整体视觉结构的一部分。有时觉得画的结构不均衡了,找对位置题上一些字,可能就又活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