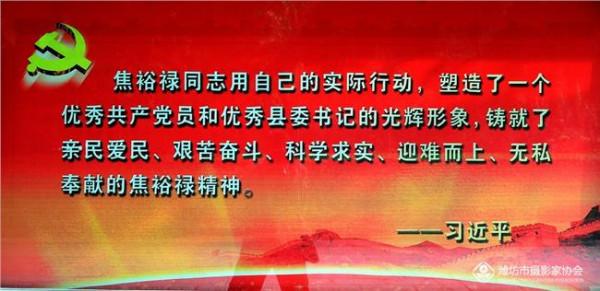焦菊隐心象 焦菊隐“心象”说辨析(转载三)
三 “心象”说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说的区别和联系
如上所述,“心象”在字面上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内心视象”非常相似,而在实际内容上,两者却有着明显的区别。
其一,和“心象”相比,“内心视象”的所指较为宽泛。斯坦尼的定义是:“只要我指出幻想的题目,你们便开始用所谓内心视线看到相应的视觉形象了。这种形象在我们演员的行话里叫做内心视象。
”[xvi]实际上,正如斯坦尼全集编者在书后的注释中所指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视觉形象”不仅包括人物、景物,还包括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其他各种“想象的感觉”。[xvii]而焦菊隐先生所说的“心象”的内涵则比较具体,它专指角色在演员心中呈现的视觉形象。
其二,获取“心象”和获取“内心视象”的途径不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演员从规定情境入手,先想象出角色所处的具体生活环境,假使自己置身其中,然后由此进入内心体验:“只要你用内心视线看到熟识的环境,你便感到这种环境的气氛,于是和动作地点有关的熟悉的思想立刻在你心里活跃起来了。
从思想产生了情感和体验,接踵而来的就是内心的动作欲求”。[xviii]斯坦尼还说:“首先,我们需要习作所依据的‘规定情境’的不断的线,其次,……我们需要跟这些规定情境有关的一系列不断的视象。
简单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普通的、而是插图式的规定情境的不断的线。……你们在舞台上的每一个瞬间,在剧本及其情节的外在或内在发展的每一个瞬间,演员或者是必须看见在他的身外,在舞台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外在的规定情境);或者是必须看见在心里,在演员自己的想象中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明角色生活的规定情境的那些视象。
这一切瞬间,一会儿在我们身外,一会儿在我们心里,形成了视象的内在和外在瞬间的不断的线,就象影片似的。
”[xix]这段话不但指出了“规定情境——插图式的不断的线——产生内心视象”这样一个过程,而且进而把内心视象分为外在的规定情境(演员的身外事)所引起的内心视象与在演员想象中发生的事所产生的内心视象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内心视象的产生,都是以进入从规定情境为前提的。
而焦菊隐所提倡的获取心象的途径,则是在阅读、分析剧本的基础上,通过体验现实生活来形成角色的心象。焦菊隐并不急于让演员进入规定情境,而是首先让演员在对现实生活的亲身体验中增强对角色的认识,通过对角色的生活环境的考察,了解角色性格的成长史,使演员对角色的认识从阅读剧本时的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
用这样的办法,使演员在心中培育起一个角色的雏形,甚至对角色的动作特征、相貌穿戴都有具体的印象。总而言之,在焦菊隐看来,体验生活是孕育心象的前提。
其三,演员创造角色的途径是从外到内,还是从内到外?在这个问题上,焦菊隐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所不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倾向于用“从内到外”的办法,在他活动的前期尤其如此。所谓“从内到外”,就是要求演员在规定情境中体验角色的内心活动,引发相应的情感反应,形成内在的心理动机,然后借助相应的形体动作将这种体验体现出来。也就是说,体验在先,体现在后。
而焦菊隐的“心象”说则允许演员“从外到内”,即允许演员先获取角色的某些外形特征(例如在观察生活时捕捉到与角色相似的人物的外部特征,将它用于角色的外形塑造),然后通过模仿这些特征,感受、体验角色这些形体动作的内心依据、内在动机,达到形神合一、内外合一,真正“生活于角色”;然后在排练过程中,进一丰富和发展外在的动作。
焦菊隐把角色的创造看作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既不赞成机械地模仿生活中的某个人物,也不赞成在排练中刻板地模仿一个既定的“心象”,而是提醒演员要不断地完善和丰富角色形象。
心象只是借以进入体验的桥梁,而不是表演的范本。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焦菊隐不同于历史上的表现派。
从上述三点可以看出,焦菊隐一方面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最努力、最积极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坚决地反对否定和曲解体系的企图和做法;另一方面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斯坦尼体系。焦菊隐之所以在上述三个问题上提出有别于斯坦尼体系的主张,主要是针对了以下两方面实际情况:
第一,焦菊隐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面对的演员不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面对的演员大多来自丹钦科领导的戏剧学校,受过良好的训练,对于如何进行体验已有一定的经验;而焦菊隐所面对的演员基本上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对如何进行体验感到困惑。
于是之就说过:“我如果不熟悉生活,决不是假使一下、积极动作,这个人就可以演活了。比如光靠假使,假使你是阿巴贡,这成吗?第一阿巴贡,第二莫里哀,第三法兰西等的情况我都不知道,就假设我,这样的假设没有资本啊!
”“当叫我演一个我并不深知其生活的角色时,我曾经这么‘假设就是我’过,但都收效甚微。弥补的办法,不是那‘魔术般的假设’,而是去生活。”这就生动地说明,对剧本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缺乏了解,单纯靠“假使”、靠心理技术,是无法真正地体验角色内心、塑造角色形象的。
正是为了解决于是之提出的这个问题,焦菊隐采取了“从外到内”的途径,成功地帮助演员创造了角色。于是之通过体验生活和培育心象,在《龙须沟》塑造程疯子的形象大获成功,便是典型的一例。
第二,焦菊隐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培养演员的程序不同。对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来说,要按照体系所规定的严格的训练教程,培养一个演员的周期至少要两年时间。但是,对于北京人艺这样一个刚刚成立、急需上演新剧目来为新中国服务的新剧院来说,照搬斯坦尼的办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焦菊隐不得不打破斯坦尼式的程序,采取有别于体系的办法。“从外到内”等三条就是这样的办法。关于这一点,焦菊隐说得很清楚:斯坦尼体系“之所以应当称为体系,因为它是一个有机的理论,是一个原则,是一个演剧的科学。
要实践这个科学的体系,在苏联就有适用于苏联演员条件的方法,在中国也就应当有适用于中国演员条件的方法。”[xx]
焦菊隐所提出的适用于中国演员条件的新方法,是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一个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有人认为,焦菊隐的方法是他吸收中国戏曲传统表演理论的产物,这一说法是不大合乎事实的。
实际上,当焦菊隐提出“心象”说的时候,他尚未有意识地借鉴戏曲的表演理论。尽管焦菊隐先生很早就对中国戏曲作过较为系统的研究,但是,自觉地借鉴戏曲的传统来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演剧方法,却是提出“心象”说之后的事情,大体上是从1956年导演《虎符》开始的。
实际上,我们从焦菊隐关于“心象”的论述中不但看不出他有意识地借鉴戏曲表演理论的证据,而且,反而可以找到某些与传统表演理论相悖的地方。例如:戏曲表演要求演员始终不忘自己的演员身分,既要能入戏,又要能出戏,所谓“不象不是戏,太象不是艺”即是这个意思。
所以,演员与角色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似与不似”的关系。与此相反的是,焦菊隐在提出“心象”说的时期反复强调演员必须在舞台上“消灭演戏的感觉”,尽可能地化身为角色。又如:戏曲表演是程式化的,而焦菊隐在提倡“心象”说的时期却是反对话剧表演中的程式化倾向的。这又是一个证明。
笔者认为,焦菊隐的“心象”说与其说是借鉴戏曲表演理论的产物,不如说是对斯坦尼体系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事实是,斯坦尼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演员在创造角色时可以运用类似“心象”说所提倡的方法,他确实是注意到了。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档案中有一页不完整的手稿,记录了斯氏的谈话:
大家知道,有些演员在想象中给自己创造出规定情境并使其达到尽致入微的程度。他们在内心里看到他们想象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一切。
但也有一种有创造性的演员,他们看到的不是他们身外的事物,不是环境和规定情境,而是处在相应的环境和规定情境中的他们所扮演的形象。他们在自己身外看到它,注视着它,同时在外表上抄袭这个想象出来的形象所做的动作。
还有一些演员,他们所创造的想象中的形象对他们说来已成他们的alter ego,他们的挛生弟兄,他们的第二个“我”。它不停不休地同他们在一起生活,他们也不(与它)分离。演员经常注视着它,但不是为了要在外表上抄袭,而是因为处在它的魔力、权力之下,他这样或那样地动作,也是由于他跟那个在自己身外创造的形象过着同一的生活。
有些演员对这种创作状态抱着神秘的态度,准备从似乎在自己身外创造出来的形象中,看到与自己的非尘世的或轻飘飘的身体相似的东西。[xxi]
在上面列举的三种演员中,第三种所用的方法最接近焦菊隐在“心象”说中所提倡的方法,二者可以说颇为相似。对于这种方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并没有加以否定,显然,他承认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然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没有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来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的编者只是在该书的注释中列举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这段文字,同时以肯定的口气指出,这页手稿“显然应该成为进一步修订本章(指“性格化”一章——引者)时的材料。”[xxii]
这样一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早就注意到、但并不很重视的创造角色的方法,在焦菊隐看来却是适用于50年代初北京人艺草创期的中国演员的,因此,他采取了这种方法。《龙须沟》的巨大成功已经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即焦菊隐在北平师范大学开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讲座和排演话剧《龙须沟》这一时期,“心象”说的提出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具有某种拨乱反正的意义。在当时中国的话剧舞台,笼罩着一片程式化的“做戏的感觉”,形式主义的“老套子”。
为了在舞台上确立现实主义的地位,焦菊隐提出了“心象”说,向《龙须沟》剧组的演员们提出了在舞台上再现“一片生活”和“消灭演戏感觉”的目标。
更为可贵的是,焦菊隐同时又对另一种不良倾向产生了警惕,这就是由于误解斯坦尼而产生的只讲“体验”、缺乏外部体现技术的平庸化表演。然而,“心象”说的提出,针对的首先是前一种倾向,即形式主义的、程式化的表演。
综上所述,“心象”说的诞生不是由于别的原因,它是焦菊隐先生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斯坦尼体系的结果。有人认为,焦菊隐创造“心象”说是“从中国民族戏剧美学出发”,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焦菊隐先生真正地“从中国民族戏剧美学出发”,自觉地、有意识地从事话剧艺术的民族化,是从1956年的《虎符》开始的,而不是在提出“心象”说的50年代初期。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外撰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