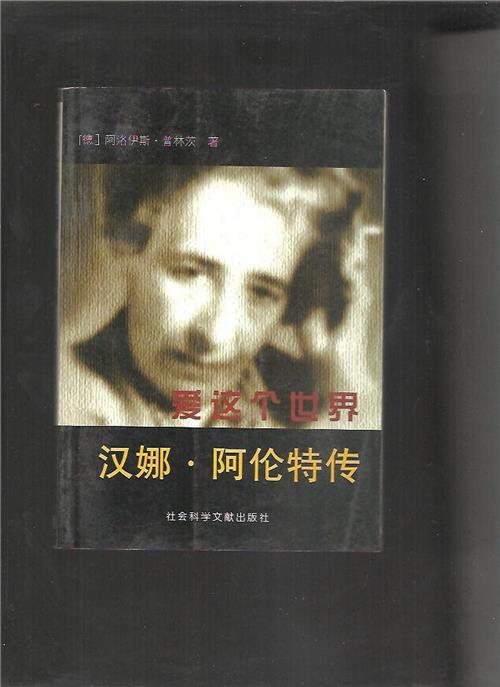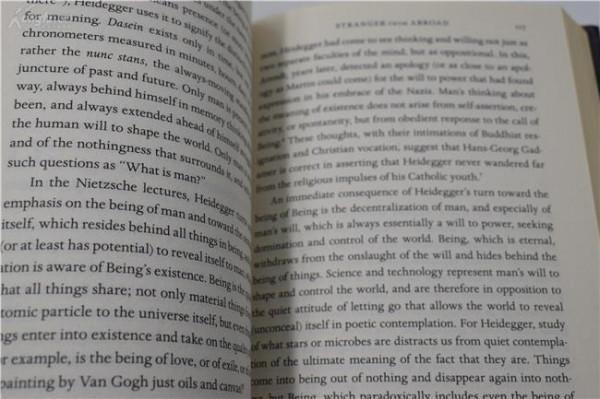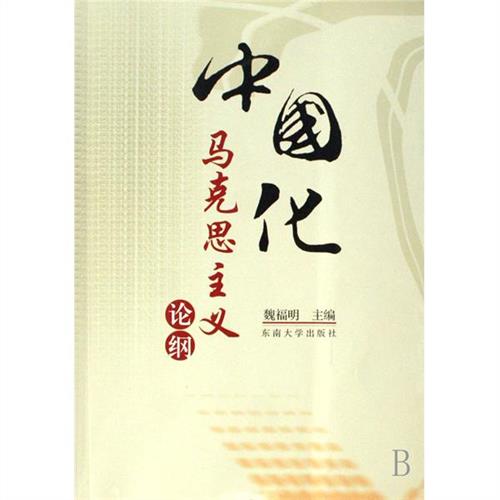阿伦特叙述 汉娜·阿伦特:生命作为爱的叙事
汉娜·阿伦特作为20世纪西方重要的政治理论家,其影响与日俱增,她的主要著作,如《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论革命》《精神生活》等已经译成中文并受到广泛关注。作为生活在德国的犹太裔女性,她亲历了希特勒上台后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大屠杀,她本人曾经被盖世太保讯问和关押,后来逃离并流亡到纽约。她的生平与思想之所以引起批评界的广泛重视,还因为她与20世纪两位德国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和卡尔·雅斯贝尔斯有着特殊的关系。阿伦特是一位睿智、深刻、热爱生命与生活的杰出女性,她的生命本身就是一首爱的叙事诗。
为爱而生
阿伦特自幼丧父,母亲改嫁,虽然母亲把她视为掌上明珠,继父也十分钟爱她,千方百计讨她欢心,她仍然感到孤独、不快乐。她异常聪慧早熟,还在少女时代就显示出特立独行、不受约束的叛逆性格。她对事件的看法和反应也不同寻常,例如祖父和父亲在同一年相继去世,7岁的她似乎无动于衷,还规劝母亲说,“一个人应该尽可能少地思考悲伤的事情,因此而情绪低落毫无意义”。
1924年阿伦特来到马堡大学读书,与年轻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一见钟情。海德格尔讲课极具魅力,阿伦特听后惊叹:“思想又复活了,过去时代的、相信早已死亡的思想财富又进入了言说,如此这般言说出来的东西与人们在怀疑中猜测的东西大不相同。”
阿伦特被海德格尔迷住了。1924年11月她在海德格尔的约谈日名单上填写了自己的名字,而此前他们已经多次交换过会心的眼神,读出了彼此内心的倾慕。他们的爱情在秘密之中迅速发展,双方都是情不自禁。海德格尔此时35岁,有妻子和两个儿子,而18岁的阿伦特则没有任何恋爱经验。他们的关系也不平等,阿伦特完全按照海德格尔的游戏规则与他交往,在他需要的时候召之即来,在他忙碌的时候耐心等待。
阿伦特在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并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她在论文《论奥古斯丁爱的观念》中坚信爱情,认为爱与生命的外延是相同的,生命本身的特性就在于爱。
1933年对于阿伦特、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都是决定性的。希特勒以国会纵火案为借口,实行恐怖的独裁统治,大批犹太人被逮捕、关押、审讯、处死。阿伦特的爱情被冻结,她的学术生涯也因其犹太人身份戛然而止,就连她的生命都岌岌可危。雅斯贝尔斯也因为其妻子的犹太人身份受到歧视和迫害。而海德格尔则被选为弗莱堡大学校长,并且加入纳粹,在就职演说中热情洋溢地发表支持纳粹的言论。
阿伦特对雅斯贝尔斯尊敬有加,爱他就像爱父亲一样。尤其是二战时期的共同遭遇、战后对犹太人命运的共同关注,使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而她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却是更深层次的感情与思想纠葛。战后安顿下来之后,阿伦特首先想到看望自己敬爱的老师。她先去拜访了雅斯贝尔斯,向老师和盘托出了当年与海德格尔的恋情,雅斯贝尔斯惊讶不已。
1950年2月,阿伦特来到弗莱堡与海德格尔会面。他们各自的处境与1933年时相比,已经大相径庭,形成鲜明对照,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阿伦特此时已经成为研究政治哲学的名人,在美国的名牌大学搞讲座,做演讲,还经常出现在镁光灯前接受记者采访,就时局发表见解,她的言论在知识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海德格尔因为二战期间的亲纳粹表现受到审查,被停止了教课,终日郁郁寡欢。
两年后阿伦特再次到弗莱堡看望海德格尔。他们恢复了恋爱时期那样频繁的通信,而且从1967年直到1975年她去世,阿伦特每年都前往德国拜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遗存信件表明他很感动。1966年10月,阿伦特60岁生日收到海德格尔的贺信,喜不自禁。“你的秋日来信给我带来极大的喜悦,最大的喜悦。这封信陪伴着我——还有那首诗和那张可以看见你黑森林书房外的景致,特别是那漂亮的充满活力的山泉的照片——并将长久地陪伴我。在春天里破碎的心,在秋日里得到了愈合。”
1969年9月,阿伦特专门为海德格尔80寿辰在广播电台发表演讲,盛赞他对哲学的贡献。关于海德格尔二战期间为纳粹效力,阿伦特辩解道,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家身上都存在暴君倾向,都患有职业畸形病。当他们认为可以把自己的哲学转化为一种教育纲领时,就是这种畸形病的发作。阿伦特最后说:“如同柏拉图的著作在千年之后仍向我们劲吹不息一样,海德格尔的思想掀起的风暴来自远古,臻于完成,此一完成如同所有的完成一样,又归于远古。”
从思想的深刻性与影响力来看,尽管雅斯贝尔斯不失为20世纪一位大哲学家,与海德格尔相比却相差很远。阿伦特虽然在雅斯贝尔斯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但是她的思想受海德格尔影响远远大于雅斯贝尔斯。阿伦特奔走于二人之间,希望他们能像20年代反抗传统哲学那样和好如初,并肩战斗,但是她的努力终告无效。
《拉赫尔·瓦伦哈根》
阿伦特在与海德格尔的恋爱陷入僵局时,偶然读到拉赫尔·瓦伦哈根的资料,深陷其中,后来写出传记小说《拉赫尔·瓦伦哈根——一位犹太女人的生活》。阿伦特说,她写书的目的不是要表现拉赫尔这个人的个性、影响,或者她与浪漫主义、与歌德的关系等等,而是“要讲述拉赫尔的生平故事,就像拉赫尔本人可能讲述的那样”。阿伦特认为拉赫尔的全部努力就是“畅快淋漓地坦露生命,就像不打雨伞站在暴雨中那样”。
拉赫尔自视为艺术家,认为通过努力,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经验转化为一件艺术品。而通过讲述拉赫尔的故事,阿伦特从深重的精神危机中拯救了自己。阿伦特认为,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讲述生命的故事。“我一向认为,不管理论多么抽象,也不管论证多么严密,它们后面都有事件和故事,这些事件和故事包含了我们能够表述的全部意义。思想本身就来自于事件,来自于活生生的生命体验。”
拉赫尔·瓦伦哈根是犹太中产阶级珠宝商的女儿。她聪慧过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不羁的行为方式,但是犹太血统使她受到种种歧视。她历经初恋失意、婚姻破裂、经济拮据等磨难,最后变得成熟坚强。在拉赫尔的书信和日记里,阿伦特体会到一种强烈的认同。拉赫尔与冯·福克斯坦伯爵那一段惊心动魄、最终却无结果的爱情,在阿伦特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从拉赫尔身上,阿伦特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虽然相隔一个世纪,二人的经历却如出一辙。
讲述生命的故事是赋予生命意义的行为。拉赫尔与众多名人保持着密切的信件往来和频繁的个人接触,在日记中详细记录自己与这些人的交往言谈和生活的点滴感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在历史上留下自己曾经活过的踪迹。阿伦特讲述拉赫尔的生命,从拉赫尔的生命中汲取了经验和力量,懂得了该如何应对生活的磨难,以介入历史的方式拯救了自己“微不足道的生命”。
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在讲述拉赫尔故事的时候,往往不加引号,自由引用拉赫尔私人信件和日记中记录的细节,将其混入女人的情感生活,混入身为犹太人、特别是犹太女人所感受的难处,包括精神使命、社会与政治的限制与选择的哲学思考等等。阿伦特在拉赫尔身上发现的最可贵的品质,是后者对生命、对尘世、对人类的爱。
《积极生活》
《积极生活》是阿伦特继《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也是她试图回答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未能充分展开论述的一些问题。阿伦特通过探究亚里士多德一些关键概念的多重含义以及后人对这些概念的误解,试图从源头上厘清一些基本概念,提出自己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思考。
所谓积极生活,是对应于沉思生活而言。阿伦特指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个词被翻译成了“政治生活”,在奥古斯丁那里被翻译成“交谈或实践的生活”。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生活”相对应的“理论生活”被翻译成了“沉思生活”。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自由人选择的三种生活方式: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认为三种生活方式的价值与意义依次递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的“有死性”使他感到恐惧,进而促使他追求不朽。
阿伦特多次说到她之所以那么需要爱,就是因为爱可以驱走对死亡的恐惧。她期望在爱中忘却恐惧,希望通过一种积极的、行动的生活排除恐惧。
阿伦特指出艺术品是所有有形事物中最具世界性的东西,因为它们的持存不受自然过程的侵蚀,可以跨越时代而至永恒。但是艺术品直接来源于人思想的能力,而思想只有在对象化和物化之后才能变成有形之物,对象化和物化的代价就是生命本身。阿伦特写道:“活的精神必须存在于死的文字中,只有在死的文字再一次跟一个愿意复活它的生命发生联系时,活的精神才能从死亡(所有活的生命都逃避不了的结局)中被拯救出来,虽然这个活的生命会再次死亡。”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阿道夫·艾希曼曾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计划的主要组织者和执行者,有三百多万犹太人根据他的命令被处死。1960年艾希曼被捕并被引渡到以色列,对他的诉讼在耶路撒冷被提起。阿伦特向《纽约客》建议对此事进行报道,意在“面对面地清偿过去的债”。1963年由《纽约客》刊登的5篇文章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书名问世,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她被批评为诋毁犹太人的纳粹分子,对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缺乏同情心,等等,严厉的批评和苛责持续了三年之久。
在阿伦特不得不面对的诸多责难与攻击中,艾希曼被具体化为“平庸恶”的化身可能是最有争议的。康德提出了根本恶的概念,认为它根源于一种邪恶的动机、作恶的意图、人的邪恶心肠。阿伦特在早期著作中采用了康德的这一概念来指纳粹集中营的犯罪。在旁听了耶路撒冷的审判,尤其是见到艾希曼本人说着他怪异的德国官方话语之后,阿伦特断定他是一个肤浅的人,缺乏独立的思考和责任感,他的全部动力仅仅源于渴望在纳粹层级中得到晋升。
阿伦特指出:“我们听到的越多,我们就越明确地了解,表达上的无能是与思考——尤其是对别人观点的思考——的无能紧密联系的。与他交流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他说谎,而是因为他将自己置身于机械论的极端有效防护之中从而攻击他人的言语、他人的存在,甚至是反对现实。”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有一种可悲的天赋,就是用一些口头禅自我安慰,直到临死前,仍然满足于发表一些僵化的言论。比如他自称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引用康德“服从是一种美德”为自己辩护。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曾经分析这样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人类思想的消除,人类自身对思想的放弃,以及对上级权威的绝对服从。艾希曼的审判给了她证明的良机:实现了纳粹主义的绝大多数人,在没有成为暴虐的怪物和嫉恶如仇的拷问人的情况下,共同分享了这种平庸,即将个人判断权利的放弃视为无足轻重的事被广泛接受。阿伦特以“平庸恶”来概括这样一种罪恶,它出自像艾希曼这样的人所固有的停止思考的能力,惟上是从,这种人的无思又因周围所有人都毫无异议地支持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命令及其千年帝国的辉煌前景而得到加强。
阿伦特批评那些不懂政治、不关心时局的人。这些人认为仅仅献身于私人友谊或者独自的追求,就能够逃脱黑暗时代的浩劫。他们不懂得,如果忽略了人类社会中他人的存在,对自身利益和人身自由的追求会成为镜花水月。阿伦特不相信有某一类型的人能够抵御平庸恶的黑暗侵蚀,但是她相信,“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仍有理由期待某种启明。这启明或许较少地源于理论、概念,更多地来自难以确知、稍纵即逝又时常微弱的光芒,一些男人女人在他们生活和工作中的种种情形下将其点燃,这光芒会穿越时空,照亮人世”。
阿伦特没有把希望寄托在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当权者、科学家身上,而是寄托在“被爱训练过的”普通人身上。阿伦特认为只有爱才能拯救人类,只有受到爱的教育和熏陶的人,那些真正爱这个世界、爱人类的人,才会自觉地试图维护公共世界或公共领域的和谐与安全。他们具有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能力,不随波逐流,不受“平庸恶”的侵蚀,是反抗极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阿伦特以自己的生命叙述的,正是一条抵御黑暗、照亮人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