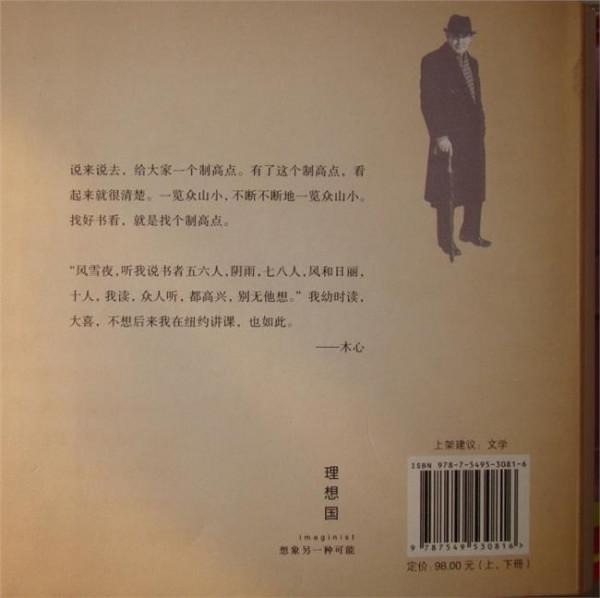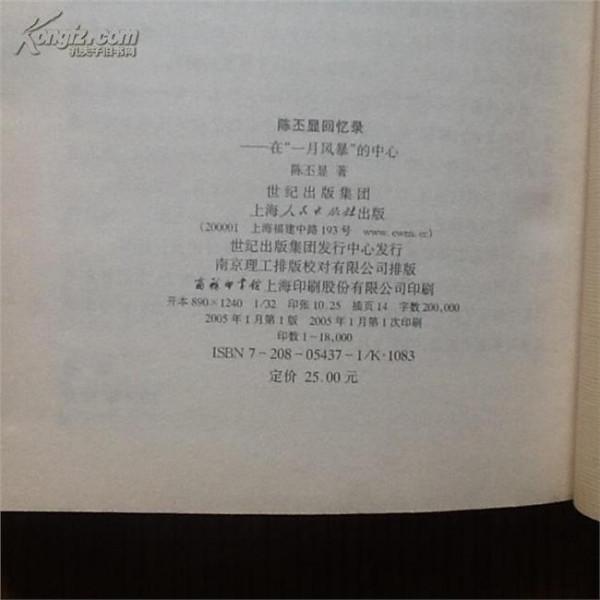叶飞回忆录(坚持闽东三年游击战)第6、7、8章
刘英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的,一九四二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英勇牺牲。他对敌斗争非常坚决,但在党内斗争中却很“左”。此时虽然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和挺进师已经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是没有总结经验教训,主要是刘英同志仍然坚持他那一套“左”的做法。
刘英同志批评闽东独立师不到白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根据地,是右倾保守主义;提出要闽东独立师(此时已改称闽浙独立第二师)离开闽东到浙西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我和闽东特委的同志都不同意刘英同志的意见,认为如果闽东独立师离开了闽东老区,闽东根据地就无法坚持,有垮台的危险;而闽东独立师如果没有闽东根据地作为依托,也就无法到白区开展游击战争。粟裕同志也不同意刘英的意见,赞成我们的意见。
有一次,粟裕同志和我个别谈话,详细谈了浙西南斗争的情况。由于他们在浙西南活动期间,没有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和新区的条件,相应改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在龙泉、丽水、龙游一带活动时仍是采取中央苏区时代的工作方式,遭到强大敌人的进攻,无法站稳脚跟,根据地和部队都受到损失,所以部队活动总是被国民党军跟踪追击,摆脱不掉。
粟裕同志问我:“我们‘尾巴’总是甩不掉,你们是怎样甩掉(尾巴)的?”所谓“尾巴”,是指跟踪的敌人。
我一下回答不出来,只能这样告诉他“像你们那样在白区横冲直撞,我们没有这个把握。我们开辟新区,在未巩固以前,党组织是不公开的,也不公开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部队到白区活动时,一般是先派人去同当地党和群众组织取得联系,了解情况,然后部队才开出去活动。
我们把这叫作‘群众工作在前,部队在后’。”我还告诉他:“我们共有四块根据地,还有大大小小的游击区。每次行动,部队从这块根据地到达活动地区公开活动,任务完成了,敌人调集兵力要来进攻了,部队就回到另一块根据地隐蔽休息,都是夜间活动,一夜走七八十里。
这样,敌人不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出来,又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有群众,敌人没有群众,所以敌人就找不到我们的行踪。
”粟裕同志深有感慨地说:“这办法好,这叫作‘狡兔三窟’,‘窟’就是根据地,没有‘窟’,兔就狡不起来。我们如果有‘窟’,就不会这样被动了!”粟裕同志又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闽东部队不能离开闽东根据地,我们挺进师就是吃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
但是,刘英同志违背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违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还是坚持他自己的错误意见。这样,闽浙临时省委内部就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
可是闽浙临时省委自己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粟裕同志就提出只有和闽北地区联得联系,请黄道同志来主持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才有办法解决和纠正刘英同志的错误。粟裕同志还要我负责设法去问闽北独立师和黄道同志取得联系。
黄道同志是闽浙赣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是闽北游击根据地党的负责人。在成立闽浙临时省委的时候,刘英同志也曾主张设法同闽北地区取得联系,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来领导闽北、闽东、浙西南三个地区的斗争。
我首先和闽北独立师取得联系,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在福建政和县洞宫山与黄道同志会晤。当时在座的除黄道同志和我以外,还有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和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政治委员曾镜冰等同志。
我向黄道同志汇报了闽东和浙西南的斗争情况,并且详述了刘英同志和我们在斗争方针上的原则分歧,建议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请黄道同志担任书记,统一领导闽北、闽东、浙南的斗争。黄道同志认为:当前远离中央领导,几个地方统一领导是有利于革命斗争的。
他这次出来就是为了与闽东党会合,拟议建立闽赣临时省委的。但是,鉴于闽浙临时省委当前的情况,要建立统一领导,首先必须闽浙临时省委自己对前一阶段的工作作出总结,指出刘英同志的错误并责成他去恢复浙西南的工作,然后才能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
我当即提出:“我们正是由于临时省委内部对于方针问题争论无法解决,所以请你出来担任领导的。”黄道同志坚持说:“如果你们本身不能解决问题,闽浙赣临时省委也就无法成立。
”我就进一步说:“我可以向闽东特委和粟裕同志传达这个意见。但是,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则非但浙西南斗争濒临危机,闽东又如何办?”黄道同志以高度革命责任心,忧心忡忡地说:“是呀,是呀,闽东斗争的成败,你们要对党负责的!
”我提出:“如果不行,我们就受闽赣临时省委领导。”黄道同志说:“你们必须先退出闽浙临时省委,才能接受闽赣临时省委领导。”我觉得问题严重,考虑再三后提出:“这样做不是分裂行为么!
”黄道同志也怔住了,他经过慎重考虑后说:“如果正常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只能采用非常方法,这是斗争的需要,何况临时省委是你们两家协商成立的,未经中央批准,可合可散嘛。”我说:“今后如和中央接上联系,打起官司来怎么办?”黄道同志毫不犹豫地说:“我一定替你们证明。
” 我回到闽东后,刘英同志来了,召开了闽浙临时省委会议,有阮英平、范式人同志参加,粟裕同志未到。平时刘英同志总是和粟裕同志一起行动,这次他却是单独前来。
在闽浙临时省委会议上,我向刘英同志报告了和黄道同志会合,并向他坦率汇报了黄道同志的意见。刘英同志一反常态,满口承认浙西南工作的错误,但是他不同意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并由黄道同志任书记,虽然他自己过去曾多次提议此事。
他反复声称,错误我们自己纠正,并居然提出要我担任闽浙临时省委书记。他说,我们已建立了闽浙临时省委,何必再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呢,还是我们这个摊子吧。我当然坚决拒绝。会议毫无结果,闽东特委不得不宣布退出临时省委。
我完全没有料到以后竟在我们自己的队伍内部演出了一场“鸿门宴”。事情发生在浙江省庆元县的南阳村,所以就被称为“南阳事件”。 “南阳事件” 一九三六年初秋,粟裕同志约我到庆元南阳会面。
自我们同刘英同志的会议以后,我还没有见到粟裕同志,我也很想同他谈话。我和陈挺同志率一个连,于中午时分到达南阳,与粟裕同志会合。见到粟裕同志,我很高兴,要向他汇报会见黄道同志的情况和临时省委会议的结果。
他说:“好呀,晚上吃过饭再说吧。” 当天晚饭的时候,我、陈挺和闽东的干部都入席了。如同旧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场景,酒过三巡,掷杯为号,预先布置好坐在我两边的人把我抓了起来,把陈挺同志也抓了。
我的警卫员拔出驳壳枪,打出门去,报告连队冲出去。我的手脚被捆绑起来,背上还被撑了一根竹竿,不能动弹,就像对待土豪、叛徒一样。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几次提出要同粟裕同志见面说话,都未予理睬。后来在路上遇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部队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乱中向我打了一枪,打伤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
国民党士兵逼了上来,我就从十几丈高的悬崖上跳下去,恰巧挂在树上,没有摔死。陈挺同志也随我跳下悬崖。
天黑后,我俩不顾伤痛,赶往闽东根据地,昼伏夜行,整整走了五夜,才到达目的地。 后来,粟裕同志告诉我,当时是刘英命令他扣押我的,也不说明是什么原因。“南阳事件”后,刘英单独召开了闽浙边临时省委紧急会议,宣布开除我和阮英平同志的党籍。
同时说粟裕也参加了叶飞、黄道反对刘英的活动,也将粟裕同志隔离起来审查。 “南阳事件”导致了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彻底分裂。此后,闽东特委接受闽赣临时省委的领导。 “南阳事件”给闽浙边的革命斗争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
我被抓的消息传到闽东根据地,部队、群众非常气愤,认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小叶(当时闽东军民称我为“小叶”)是红军,抓小叶的人一定是坏人。有的人情绪激动,甚至提出要带部队去找他们算账。
幸而我赶回闽东,及时向大家做工作,制止了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 这就是导致闽东和浙南彻底分裂的“南阳事件”,这是在当时“左”的影响下党内斗争不正常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其表现形式又带着中国的传统色彩。
记得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火并”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是常见的现象,看来在革命队伍中也很难避免(大意)。我自己就亲身经历了一次。然而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我深感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毕竟不是农民武装,因为在革命队伍内部,能够为着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后,闽东和浙南的部队都编人了新四军,以后一直并肩作战,直到革命胜利。我和粟裕同志也长期战斗在一起,从新四军一师,华东野战军,一直到解放后,我都在粟裕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多次当他的副手,相互间配合得很好,没有因为个人意气而影响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八年有一次在上海开会时,李富春同志问我:听说在闽浙边临时省委时发生过南阳事件,有没有这回事?我就扼要地把这段党内斗争的经过告诉他。
富春同志听了之后,很吃惊,并问我有没有向毛主席报告过,我说没有。富春同志对我说,有机会时应当报告毛主席。但是,以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此事。
现在我认为有责任对闽浙临时省委当时那段极不正常的党内斗争作出如实的反映。 第八章 顾全大局团结抗战 闽东山民——畲族群众 一九三六年秋天,斗争形势又紧张起来。国民党以刘建绪为绥靖主任,对闽浙、闽赣边区红色游击队进行“清剿”,先后增派八十师、九师、保安独立旅等到闽东来,配合地主反动武装分驻在根据地周围,进一步用“五光”、“十条”、“移民并村”等残酷手段,再度“围剿”我闽东根据地。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其“剿共”方针,更加疯狂地对我南方根据地进行“清剿”,妄图消灭我南方红军游击队。 闽东党和闽东人民已有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清剿”斗争。
地方武装在原地坚持斗争,独立师仍以纵队为单位在根据地周围开展游击斗争。 这里应该特别提一下闽东地区的少数民族——畲族。这个民族人数不多,约二十多万人,有一半以上散居在闽东太姥山脉、鹫峰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自称“山民”。
他们在旧社会历来受到歧视和凌辱,身受几重压迫,在大山上含辛茹苦,饥寒交迫。历史上,他们也曾白发地掀起过几次斗争。闽东党很早就重视民族政策,注意在畲族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但在初期,畲族人民对汉族是不信任的,有戒心,工作很难开展。后来,发展了一个畲族党员,在畲族中的工作才开展起来。以后畲族群众有许多人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并成为骨干。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畲族人民的作用是很大的。
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在最困难的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对革命斗争支援最大。我们在山上依靠畲族掩护才能坚持。白云山支脉的竹洲山和屏峰山,闽东独立师的后方医院和修枪厂就设在这里。
一九三六年十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军伙同当地民团曾三次焚劫了这里六个畲村。敌人抓住雷银俤等八位老人和妇女,逼问红军医院和修枪厂的所在,结果只得到“不知道”三个字。
敌人烧了他们的四幢房屋,用马刀砍头威胁,捞到的仍是“不知道”三个字。敌人以更大兵力合围竹洲山,枪杀了村苏维埃主席雷良俊同志,烧毁全部茅屋,把避在山林的畲胞赶下山,实行并村,编保甲,订连坐。
可是共产党员雷成波等同志仍然活跃在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的群山之中,掩护着红军后方医院和修枪厂。在这困难的日子里,闽东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们,特别是少数民族,对我们没有一丝隔膜,把我们当自己人,成了我们的依靠。
闽东党就是这样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到一九三七年,大部分根据地已逐渐巩固。连江、罗源的部队则由海路南下莆田仙游地区,与莆田中心县委领导的游击武装会合,坚持闽东地区的斗争。
我们的部队活动范围直到离福州只有三十里的下店,我党在白区城镇的工作也开展起来了。军事、政治形势对我们更有利了 历史的转折关头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整个南方地区都与中央隔断了联系,所以政策的转变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在南方各个根据地是个大问题。
闽东地区政策的转变是在一九三六年冬开始的,其经过如下: 闽东党长期脱离上级党的领导,只有千方百计搜集党的公开文件和报纸刊物,从中分析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
每隔一两个月总要攻打敌占据点,固然也有补充枪支弹药,筹款、扩大政治影响等目的,更主要的是为了夺取报纸,了解国内外的政治形势。闽东地区毕竟靠近福州,搜集香港、上海出版的报章杂志比较方便。
福州的地下党组织虽然遭受了破坏,但它还有一定数量的党员,还有党的外围组织,还有党的影响。当时我们在福州有一个交通,曾是地方军阀卢兴邦洪山桥兵工厂的工人,名字已记不起来,都叫他的外号“莫斯科”。这个人很灵活,经常给我们买一些书报、武器、弹药、西药,甚至连国民党军军械库里的迫击炮都买来了。
一九三六年冬,我们看到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以后又得到《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其他宣传品。
这是从香港党的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传到福州,又从福州传给我们的。我们虽然和“南委”没有发生关系,但知道这是党中央的文件,是新的精神。从报刊上,我们又了解到全国各个城市里蓬勃的学生抗日运动,看到了新的革命高潮,所以我们政策的转变比较顺利。
我们学习闽西,成立了闽东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代替闽东苏维埃政府,颁发了布告,大量翻印《八一宣方》,到处张贴,开始了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虽然没有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实际上不打苏维埃旗帜了。
那时提出的统一战线,还是反蒋抗日,号召同一切愿意抗日的友党、友军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然从土地革命到民族战争这是一大转变,但弯子转得还不那么大。“一.
二八”上海抗战后,十九路军调到福建,我们在进步青年中进行团结救亡的工作,也做十九路军中的士兵工作。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我们也感到光搞土地革命,不提抗日救国的口号是不行的。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了。
我们在政策上作了更大的改变,不提反蒋抗日的口号,只提抗日救国的口号,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团结起来抗日,只要愿意抗日,我们都可以团结。我们的政策进一步改变以后,开始收到效果,农村和城镇的一些商人、联保主任、乡绅、教师,都敢于和我们接触了,我们的团结面广泛了。
这时,原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一个排长带了一班人,投奔我军。他说,他觉悟到只有共产党人和红军是真正抗日的,所以他投奔来了。
我们从这里看到,这是一个信号:抗日救亡是当时的历史潮流。我们政策的转变,由反蒋抗日变为联蒋抗日,主要是两件事震动了我们。一是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二是国共合作,红军已改编成国民革命军。 当时我们对抗战一直是积极提倡的。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蒋介石来领导抗战,红军要改编为国军革命军。为了进一步弄清全国形势的变化,八月底,我们决定攻取宁德八都重镇。 八都是宁德县沿海市镇,靠近海口,是交通要冲,三都澳航船只能开到八都。
八都只有民团百多人。我亲自带一个纵队去,很顺利地打了下来。这仗,完全是为了政治目的,是为了搜集报纸。我们搜集到不少上海、南京、福州的报纸,整版整版的刊登着抗战战况:上海打响了;南口在苦战;张家口告急……我们在《申报》发现两篇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和《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就职通电》,赫然触目!
我们才知道国共合作已经实现,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准备开赴前线抗日。
我们在八都住了三天,特委做出决定,改变策略,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向福建省政府、闽东各县政府发出了油印信。这已不是一般泛泛地进行宣传,而是采取行动了。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仍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说什么“北方合作,南方不合作”,继续进攻,企图把我们各个消灭。那时,我们已经听到闽南我军受骗缴械的消息(即何鸣事件),引起了我们的警惕。因此一面积极争取停战谈判,一面坚持进行自卫。
在南阳附近消灭了进攻我们的浙江省保安团一个连,又在宁德的亲母岭打了一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加强连。敌人进攻不成,又吃了苦头,这才老实一些,表示愿意与我们谈判。但国民党福建当局还摆着架子,省方不愿出面,要宁德地方当局出面谈判。
上海战事紧张,国民党军事当局慌忙将七十八、八十七、八十等三个师从福建调赴上海,福建的国民党军事力量更小了。福州直接受到我军威胁,福建当局才不得不通过“福安抗日后援会”的郭文焕同志(系我党福安城区地下支部负责人)向我方表示,愿意以省政府作为一方与我谈判。
停战谈判 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我亲自去谈判。对此,特委认真进行了研究。鉴于何鸣事件的教训,作出决定:不宜由我立即出面谈判,如果国民党当局把我扣留了,不好办。
但也不能派一般人去,人家会以为我们没有诚意。因此决定派范式人同志作为全权代表去谈判。 第一次谈判地点在宁德县城,国民党方面由省保安处处长黄苏为代表。
谈判时,我方提出五个条件:第一,闽东人民抗日红军愿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队,干部由共产党委派,保持共产党的领导;第二,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释放一切政治犯;第三,宁德、屏南、福安三县划为我们的驻区,如果日军进攻福建,我们主动配合;第四,根据地已分的土地维持现状,不能强迫农民退还已分得的土地;第五,国民革命军抗日游击支队应按国民党军队供给标准发给给养。
但是国民党对于和平谈判并无诚意,妄图在谈判桌上获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坚持要把红军收编为“保安师”。
我们要改编,他们要收编,一字之差,相争不下。而这一字之差正是合作的原则问题。 那时,我们把部队集中在宁德的桃花溪地区。国民党代表黄苏提出,要派人见我,以便当面向我陈述意见。
派来的人叫王调勋,是个叛徒,引起了我们警惕。我们研究后认为肯定有阴谋,但也不能不让他来,看看他来究竟有什么名堂。我们决定在离宁德县城只有一天路程的半山边上的一个村子同王调勋见面。
因为这个地方位于边界,消息比较灵通。我只带一个排在村子里,把主力隐蔽在村子附近五六里路的地方,以防不测。果然,这个叛徒并不是真来谈判,而是来侦察。我们估计此人回去后敌人会来袭击,就做了战斗准备。
第二天拂晓,省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亲自带一个加强连来,那是很精干的部队,妄想袭击我们的首脑机关。敌人走出宁德城五六里,我们就知道了。部队就在敌人必经之路埋伏,等敌人走人我埋伏圈内,立即出击,截断了敌人后路。
两边一夹,不到一小时,就把敌人全部消灭,带队的参谋被我们打死了,他骑的枣红色的川马,很善于爬山,也被我们俘获了。我们彻底消灭来犯之敌以后,第二天立即派范式人同志下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
他们哑口无言,说是“误会”。 大概就在这时候,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派张云逸同志到福州来找我们部队。但是国民党当局还没有放弃诱降、分化、瓦解我们的阴谋,不让他进来。他们推托说,游击队没有固定地点,一下子找不到。
又说,已经跟我们谈判了,你不必去了。张云逸同志在福州通过和我们有关系的一些进步青年看到了我们的布告、传单等,知道我们不会上当。反正国民党当局“收编”不了时,总要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的,就离开了福州。
第二轮谈判,还是范式人同志去。黄苏却又推托说我党提出的条件他们不能解决,要我们到福州同省主席陈仪面谈,又把谈判拖延下来。 第三轮谈判也没有成功。 九月中旬,上海战场形势更趋紧张,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重开谈判。
由范式人同志去福州,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在以下几个条件上,与国民党福建当局达成协议: 一、闽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第二游击支队; 二、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支队由共产党领导; 三、划屏南县为闽东红军驻区,一百里内国民党不得驻兵; 四、以中共闽东特委的名义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宣言”,并公诸报纸。
改编用的番号是我们提出的,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达成协议成立新四军。听说闽西用了“抗日游击支队”名义,所以我们也用这个番号。
当时我们有个想法:什么番号都是暂时的,中央会有统一部署。但是我们坚持组织上是独立的,国民党不能干涉我们内政和委派干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当时的《福建民报》上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
闽东党和福建国民党当局的谈判经过了复杂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范式人同志带回了闽南、闽中部队在县城集中被国民党反动派缴械的消息,我们更加警惕。斗争转而集中在集结地点上:我们坚持“独立自主靠山驻扎”的方针,部队不开到县城集中,而集中在我宁德根据地中心的桃花溪地区。
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处理好,即五条件地采纳了停止打土豪的条款,发生了经济困难。我们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给养费问题,他们以为有机可乘,要挟说:“改称保安师,就可负责发给给养。
”我们提出借,他们还是不肯。我们就说:“那好,我们自由行动,自己解决给养问题。”他们当然懂得这个话的含意:我们又要打土豪了。
于是他们慌张起来,才借给我们七百套棉衣和五千块钱。也由于经费问题,我们没有能抓住抗日高潮的有利时机,扩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停战后就停止扩军,这是个失策。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新四军已在南昌设立办事处,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派来的顾玉良参谋进根据地和我们取得联络。
那时,项英、陈毅同志已到南昌筹建新四军军部,要我随同这位参谋前去领受任务。这样,我才下山经福州去南昌。 在福州,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在办公室见了我,惊讶地问:“你就是叶飞?”我说:“是呀。
”他情不自禁地说:“你是个书生嘛!”晚上,陈仪宴请我,保安司令等人作陪。 我在南昌接受了新四军军部命令,部队开到屏南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任命我为团长,阮英平同志为副团长,全团约一千三百多人,开到屏南县城集中。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我们奉命离开了战斗多年的闽东,踏上抗日征途,留下范式人同志在闽东坚持斗争。 闽东苏区和闽东红军的特点 五十年过去了,现在回想在闽东五年的战斗历程,感到: 闽东苏区和闽东红军既有其他苏区和红军的共同点,也有它自身的特点。
第一,它是全国最后建立的苏区,利用“闽变”的有利时机建立的工农革命政权。由于它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岁月里诞生的,失去中央的联系,所以中央只是从敌人报纸上知道这里有党的活动,有红军,有苏区。
第二,它的创建不同于主力红军开辟的苏区,主要是依靠本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是土生土长的。
第三,一九三四年春,福建党遭到大破坏,闽东党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解决本地区的问题,独立自主的坚持斗争。第四,闽东地区的斗争过程是从农民运动的小型武装斗争到建立苏区,到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始终以游击战作为基本斗争形式。
第五个特点是它有很长的海岸线,所以敌人难以封锁。 这些特点既是闽东苏区和红军的长处,也是它的短处。它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自始至终都是依靠群众的;受王明路线的影响比较少,受外来的错误做法的影响也比较少。但是,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又得不到上级的指导和兄弟苏区的经验交流,在斗争中当然要不断发生错误和遭受挫折,只能自己从错误和失败的实践中吸取教训,纠正错误,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