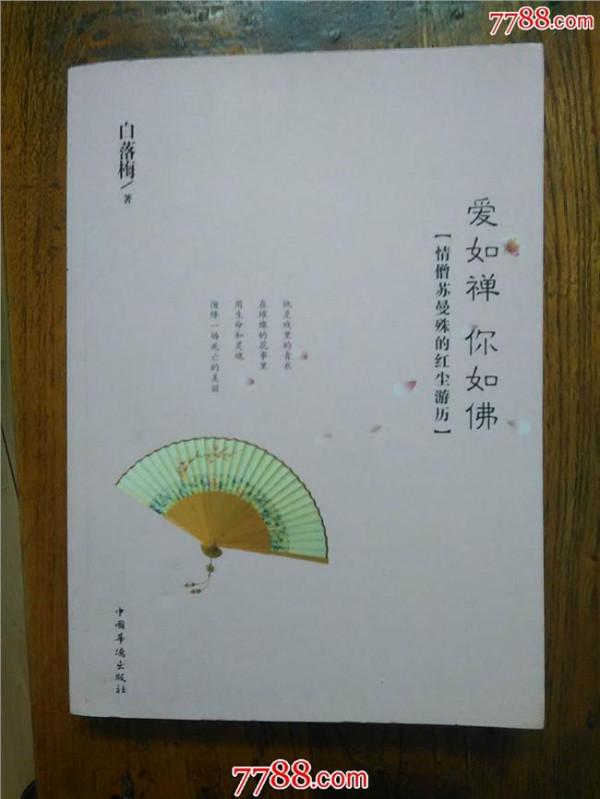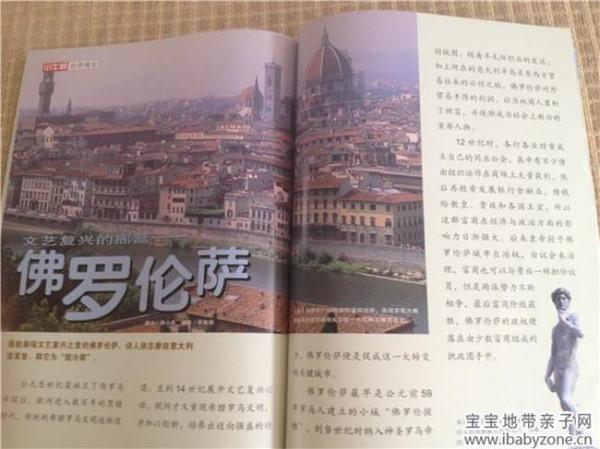苏曼殊说禅 苏曼殊和李叔同的爱情 苏曼殊爱情小说人物悲剧的审美特征1
苏曼殊是清末民初的一个颇具神秘色彩、亦僧亦俗、不僧不俗的文学家和革命家。他的艳丽、富有情趣的诗,清新婉丽、悲凉感伤的小说,他在中外文学关系史上作为较早把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介绍到中国来的作家之一的独特地位,都使他成为清末民初的一个极富浪漫色彩的人物,成为承载着过渡时代的感伤情绪的典型代表。
苏曼殊的生活轨迹和创作活动的轨迹几乎平行,有一定自叙传的性质,这主要体现在他的6部作品上,《断鸿零雁记》、《焚剑记》、《碎簪记》、《断鸿零雁记》、《绛纱记》和《非梦记》。这些作品最大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其作品中的典型的悲剧人物形象上。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在苏曼殊的笔下,男子皆有过人处:如三郎身世飘零却风流倜傥,守佛法,却多情多意;或如独孤粲俊迈不群,为友复仇,来去飘忽,腰佩一剑,可用火焚之,“如焚纸焉”:或如庄浞同为二美所挚爱,陷于情网中而不能自拔。
在他的笔下,女子皆美:雪梅容华绝代,古德幽光;静子清超拔俗,庄艳娟媚,袅娜无伦:秋云容仪绰约,出于世表;五姑姿度美秀,蝉嫣柔曼;阿兰端丽修能,亭亭似月;灵芳仪态万方,风致如仙;莲佩容光靡艳,丰韵娟逸;薇香眼色媚人,清超拔俗:风娴靡颜腻理,婉惠可爱。
苏曼殊小说浓厚的悲剧色彩因为有了这些纯洁美丽的少女以生命来渲染,就更为惨烈和惊心。
苏曼殊小说人物的悲剧命运与悲剧性格染上时代、社会的特有色
彩,社会危机乃造成悲剧的要根源。黑暗的时代、封建礼教的扼杀、男女主公的性格弱点——种种因素交织作用,苏曼殊小说于是一直潜伏着悲剧的暗流。这种持续的感伤气氛与作者传奇飘零的身世、震荡的时代相适,体现出一种必然。
苏曼殊笔下的女性如静子、灵芳、莲佩、五姑、阿兰、薇香大多才貌双全,颇有见识。像静子,她美若天仙,谈吐不凡,不仅对古典诗歌和绘画艺术有独到的见解,还通佛理、关心国事。连己为僧人的三郎也掩饰不住对她的欣赏与倾慕。
但这些可爱的女性大多在尚未享受到爱情的甜蜜时就过早地失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不禁令读者扼腕感慨红颜的短暂。究其原因,与她们对爱情的绝对忠贞有关,这种“至情”的可贵态度为什么会导致她们的“早天”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首先,封建家长的冷酷和将女子视为货物的贪婪品性。
作为女性,婚姻可以说是她们的全部,但在那个年代,拥有操控她们命运大权的家长却唯利是图,将她们作为赚钱的货物,想方设法把她们嫁入豪门,至于小说里清贫的男性,根本不在“精打会算”的家长们的考虑范围内。
《焚剑记》里阿兰的姨妈就嘲笑独孤粲,“公子佳则佳,然其人穷至无裤,安足偶吾娇女?”,一副势利面孔跃然纸上。《断鸿零雁记》里的雪梅更是因父母几番以金钱作为是否嫁女儿的标准,在对三郎的爱情无望下绝食而死。
其次,封建礼教对女性品行和思想的束缚。封建思想不仅仅从外部破坏女子的幸福,更侵蚀了她们的思想,使她们成为自觉的“殉葬品”。《焚剑记》里阿兰的妹妹阿蕙出嫁前几天未婚夫就得病死去,但她还是坚持嫁给一个“灵牌”,用行动验证了她先前说过的一段“女子贞节论”:“女
子之行,唯贞与节。”这种残酷的封建贞节观真是毒害少女身心的元凶。就连曾经留学英伦的玉鸾也作出“尝割臂疗父病”的毫无科学根据的封建“愚孝”举动。第三,脆弱的身心不堪命运的捉弄。封建时代的年青女性在身心上本来就是脆弱不堪的,有时候一点点的伤害对于无力的她们来说也相当于洪水猛兽。
五姑在与昙鸾因海难失散后,几经流离而死;阿兰也熬不住接连的逃难奔波之苦,暴病而卒:灵芳、薇香则是在三角恋中误会情人移情别恋或者因为脆弱善良的个性主动退让以至自尽。
第四,由于男主人公暖味的感情态度。《碎簪记》中的莲佩亦是好女子,也是悲剧人物。她溺于情而无法自拔,小说叙写她与庄湜交谈、周游沪上、观剧、偎依其怀等,而庄湜不为所动。以倾国之姿、聪慧之心而无法动摇庄湜对灵芳坚贞的爱情,叔曾劝告灵芳割舍庄湜,灵芳心死,要击碎玉簪,今生无缘,“愿订姻缘于再生。
”莲佩自知爱情无望,割喉自杀,灵芳自缢而亡,悲剧形成。“其实,这几个原因往往是互相作用,共同完成扼杀少女生命的‘任务’。花还未开,就已经谢了,这些少女的悲剧命运往往是小说里最令人痛心的一幕,她们才是最可怜可悲的受害者。”
“悲剧之产生主要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审美作为人类从精神上把握现实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与一定的历史时代同步发展的,是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改造而不断深化的,是为审美主体的哲学文化意识、心理结构、生命形式、生存状态、思维方式所制约的。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统治、封建压迫和封建思想的毒害,是造成民众思想落后的罪魁祸首;闭塞、贫困、保守及民族遗
传的某些心理原型,也部分地造就着民众思想的落后。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经济上的贫困以及相关的愚昧落后的遗风旧俗,封建意识以及相关的不健康的心理等,都是人性的否定力量,对于以个性主义和全面发展的人为理想和目标的现代人来说,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无形的悲剧因素。
在苏曼殊的时代,男女青年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只能有两种结局:一是向封建势力屈服,二是以悲剧告终。苏曼殊把第二种结局赋予自己的小说。在苏曼殊爱情小说中,与其把悲剧的实质看作一种冲突,不如宽泛地看作是一种“否定”,对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否定。
苏曼殊小说中的青年男女,对否定性力量根本没有主动性的挑战或应战,而是被动地或是出乎意料地受伤害。由于他们的弱小、被动,弱化了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且改变了悲剧的性质,否定性的悲剧力量(假丑恶)成为强势的压倒性力量;也正是这种反常、扭曲与颠倒,更显示了加害者、否定性力量的专制、暴戾、反动,更显示出悲剧者的弱小和无奈,使悲剧具有一种令人恐惧的压抑和沉重。
它与英雄悲剧相比,有其特殊的审美趣味。
英雄悲剧是一种强烈的悲剧美感形态,常常是社会剧烈变动的产物,是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思想矛盾和情感矛盾严重冲突的结果,是矛盾的双方在不可调和的状态下相互撞击而迸现的灼目的火花,是产生于特殊生活状态具有强烈美感悲剧类型:从悲剧者的地位与性质而言,悲剧者越是主动、强悍,冲突就会更加激烈,悲剧美感效果就更加鲜明、强烈,而且在道德和文化等形态上越发突出肯定性力量的地位,从而奠定其歌颂性的基调。
苏曼殊小说中的青年男女的这种弱小、被动、无辜,决定了其结局具有有冤无处诉、有悲无处发、有愤无处泄,“所产生的美感效应与其说是‘激励与鼓舞’,还不如说是压抑和深重,其文化取向主要是批判性的。”但从价值形态上说,却不会把人们导向悲观主义,它引起的主要是深层的、理性的、道德的、人性的省察以及政治和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其独特的审美特征主要从两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否定性力量强大而无形,由于普通人物的弱小、无辜,无法对冲突或说是否定性力量迸行挑战或应战,常常是被动地或是出乎意料地受伤害,有时甚至具有几分荒诞无稽的色彩。通常理解这样会弱化冲突的激烈程度,但实际上,经过这异化的力量对立,弱的一方更弱,强的一方更强,更显示出普通人物的弱小和无辜,使悲剧具有一种令人恐惧的压抑和深重,一种欲辩无言、欲哭无泪的悲哀气氛。
对苏曼殊小说中的人物来说,我们找不到或者说一时说不清楚谁是他们具体的敌人、仇人,但是他们的命运又是那样地无可躲避,实质是对一个荒诞的时代的控诉与否定。
正如鲁迅在《我之节烈观》所说:“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
其次,悲剧冲突由外部转向内心,由行为转向灵魂,心灵的受审成为这些悲剧人物的一般特征。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都有一颗孤独而病态的灵魂,他们正直善良,却卑弱伤感、优柔寡断、情怀抑郡、苦闷排徊、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大胆的叛逆反抗精神。《断鸿零雁记》
中温柔多情的三郎面对雪梅父亲悔婚,只能以出家的形式来压抑自我,逃避现实:面对母亲之命和静子柔情又顾虑重重,既斩不断情丝,又顾忌佛法戒律,最后的悄然离走,不是对静子的解脱,而是把静子推向悲剧的境地,把爱情推向毁灭。
《非梦记》中燕海琴既深爱薇香,又顾忌其婶,虽有“天下女子,非薇香不要也”的誓言,却面对婶母阻挠不敢大胆力争,《碎簪记》庄湜更是优柔寡欢,只知以泪洗面,既对灵芳“寸心注定,万劫不移”,又不敢逆叔婶意旨,陷入两难之境,难以自拔,终至三人殉情。
可见,苏曼殊小说主人公都经历了悲剧性的思想折磨,都在心灵深处为孤独、痛苦所折磨,而懦弱悲剧的性格使美好的爱情成为泡影,小说正是通过对人物悲剧性格的刻画,使人物具有了内在的悲剧性,增强了小说的悲剧色彩,也充分显示出悲剧的真实性和深刻性。
苏曼殊小说的悲剧基调,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特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处在新与旧的交替之中,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开始在封建废墟上寻找自己的位置,古老的中国出现了新的追求,新的思想;但另一方面,是强大的封建势力、封建意识的猖狂反扑,军阀割据,复辟猖狂,旧的意识在泛滥,沉渣在泛起。
联系时代的特点来看苏曼殊小说的悲剧性,作者要表达的是时代的迷惘、时代的彷徨,也是时代的企求;同时,苏曼殊小说人物的悲剧性,又是他这位时冷时热、亦僧亦俗的革命和尚、爱情和尚对时代的迷惘、彷徨在自己小说人物中的折射。从这个意义上看苏曼殊小说的悲剧性,揭示了悲剧的时代内蕴和社会性,揭示了封建道德观
念给人沉重的枷锁,造成社会非人性的劣根,而这也是其小说悲剧性的时代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