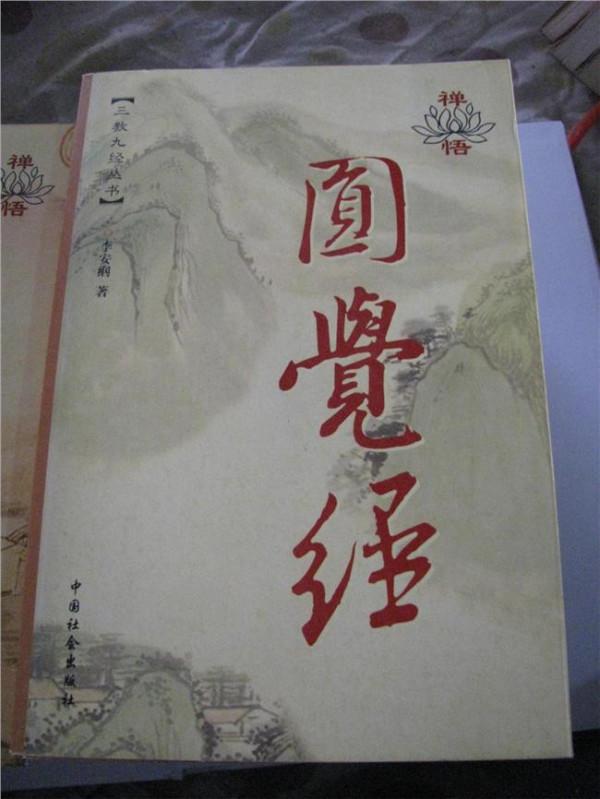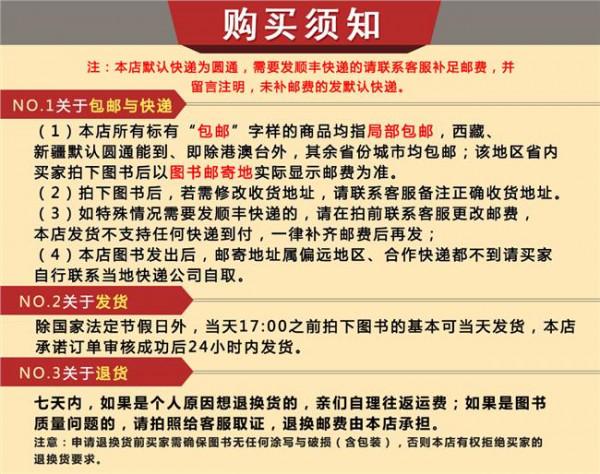叶曼讲道德经 【叶曼】《道德经》讲记——第四章
这一章是专门赞叹道的体、道的用非常微妙。道有体也有用,本体假设不启用的话,本体不存在;但如果只知道他的用,而不知道他的本体,你就是迷途的羔羊。就像电是看不见的,但它却能够使电灯发光、扩音机发声。假如把道的本体比作电,这些亮光、声音就是道的启用。我们因为道的启用而知道它的存在。
“冲”是虚的意思。道因为虚静才能有所启用,才能生万物。后面老子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我们有了这个东西很便利,但你要用它的什么呀?就是用它的无。譬如这个房子有了,要是里头实实在在的,我们能在里头坐吗?必须里头是空的才可以。
杯子是空的才能装水,车轮的轮毂是空的才能使车轴运转。房子有了窗户,光亮才可以透出来;有了门,人才可以进出。这就是“无之以为用”。以无用为大用,可以拿来治理社会,教化人民。如果统治者太追求功利,颁布太多律令,到法令如毛的时候,就会变成人民的负担了,反之只有虚静才能让人民生活安稳。
道体完全空虚,这样才能生就万物,才能充满天地之间。人的处世也是一样的。《三字经》说“满招损,谦受益”,孔子让弟子往器皿中倒水,水倒了一半,平平稳稳的;孔子让他再加水,结果水一满就器皿就歪了,水都流了出来。
这就是“满则倾”。孔子懂得这个道理,所以非常虚心,“入太庙,每事问”,绝不强不知以为知。诸位想一想,当我们自满的时候,还接受其它知识和别人的意见吗?不接受了。道冲虚才用处无穷,用处无穷才无所不在。
假如它有了,它是这个,那么就不是那个,这样就不广大了;正是由于它无,所以它不是一切但又是一切。同时,它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无穷无尽,所以它永远不满,永远都能用,“用之或不盈”。
“渊”是深的意思。这说道变动不居,高深莫测。道为什么“深”呢?因为我们见不到它、听不到它、抓不到它,不知它有多大、多高、多深。所以老子感叹说:“渊兮!”这个高深莫测的道却能够养育万物,是万物的根本,万物都是从它而生的。
它生了万物,万物有生有灭,可道在哪里呢?道永远都在这里。佛家说:“青青翠竹无非波罗,郁郁黄花皆是菩提”,翠竹和黄花都是要灭亡的,而波罗和菩提永远都在。
所以说渊深幽静的道是万物之宗。禅宗六祖慧能在读《金刚经》“因物所住而生其心”句时,跟他的师父五祖说:“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本无生灭,何其自信本无来去,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就是说本体不动摇、不生灭、没有来去,但是最要紧的是最后一句,假设没有生万法,你上哪去找它去。
道的本体从来不动,也不被万物所役使。怎么叫所役使呢?就是说它生了万物,但是它既不做万物的主人,也不做万物的奴仆。我们可以去顺从它,却不可以扭曲它、违背它。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王弼注解说:“冲而用之,用乃不穷;满以造实,实来则溢;故冲而用之,又复不盈。其为无穷,亦已极矣。形虽大不能累其体,事虽殷不能充其量;万物舍此而求生,主其安在乎﹖不亦渊兮似万物之宗乎?”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它怎么做呢?道体的用它不是尖锐。我们知道道之用是要柔要弱。所以老子说当它生也柔弱,你看花朵柔弱的,枝干柔弱的,其死也刚强。所以老子非常反对人家刚强,生的是活的,软的弱的,死了邦邦硬,静悄悄的。所以你必须不可以尖锐,太尖锐的话不高。所以道体的用要柔要弱,绝不能用尖锐或者敏锐,或者刚锐。
“挫其锐”,就是把锋芒挫去。诸位看我们削的铅笔,铅笔削的太尖了就断了。我们把什么东西削尖了以后,伤人也伤自己,所以一定会断的。我们思想太尖锐了,说话太刻薄了,做事太独断了,这就不符合道的那种品质。中国有句话叫“枪打出头鸟”,就是说一个人什么都爱出风头,志气太高了,就要遭到别人的妒忌,最终会遭到挫折。因此“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这才是高深的处世之道。
不但“挫其锐”,还要“解其纷”。世间本来没有是非,是非之怎么来的?是从争竞中来的。人们为了一些蝇头小利争个不停,事情没办成多少,反而惹了更多纠纷,我们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就是这个意思。
可真正有大智慧、大品德的人是不爱自我宣扬的,也是不会对事物起分别心的。道本体从来没有说话,“天何言哉”,可是春夏秋冬不停地在变,万物靠着它生长。所以《周易》中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说太多话,没有事情也会生出事情来。反而,不管世间的人事怎么样复杂,只要“冲而用之”,以柔弱为用,就能够把纠纷都解决了。
然后是“和其光,同其尘”。怎么“和其光”呢?我们常常称赞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可大家都想照亮别人,都努力把自己变成光源,这样会招来很多注意;可万一自己都烧了,别人并没有照亮,就会招来很多不满。
所以真正高明的人是把光芒收敛起来的。他们反求诸己,光芒内照,而不追求标新立异。“同其尘”又是什么呢?尘是尘俗的意思。我们称赞一个人很独特,与众不同,就说他“脱俗”。
现在很多人都要标榜自己有个性,有别人比不上的地方。可是老子说这样不好,因为无论个性多么独特,才华多么出众的人,都是要在社会中生存的。我们吃的饭、喝的水,是多少人辛苦劳动的结果。“举天下而奉一人”,天下人为你做了多少事情,你怎么能够特立独行呢?和光同尘,就像拿水投到水里,拿火投到火里,没有你也没有我,这就是“冲而用之”。
“湛兮似若存”,湛就是湛然明白的意思。本体虽然没有尖锐、没有光芒、没有纷争,本性清澈见底,跟万物“和其光,同其尘”,可是它依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存在。他不是一个乡愿先生,不是墙头草,随风倒。
它入乡随俗,没有跟事物有什么不同,但是它又是单独地存在,也不动也不坏。万物是有变化的,花有开有谢,人有老有死,这是个自然的过程。你可以知道了大道运行的规律,可以做到“物我两忘”;虽然物我两忘,但你还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有个故事讲禅师的弟子外出游方,临走之前请师父赐他一点指示。师父说了三个字:“莫为善。”弟子吓一跳,说:“你怎么叫我莫为善,难道要我去作恶吗?”诸位学过前面几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善和恶都是后来的区分,世间事本来就没有善和恶,只有顺应自然和违背自然。我们做事顺应自然,这就可以了,倘若有心为善,那反而不是最上乘的。物我两忘、和光同尘,这才叫湛然。
“吾不知谁之子,像帝之先”,这个道就是这么神奇,我不知道是谁把它生出来的,只知道它在天地成形之先就有了。这也是描写道的神秘。我们一直追问,从事物的外表到事物的本质,从事物的本质到普遍存在的规则,再到普遍存在的规则的来源,最后发现这个道无所从来,找不到踪迹。
佛教中也说:“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生,不逐四时凋”。这个先天地之物就是“道”。无形无生,自由自在。没有一个东西不是它生出来的,原子、电脑,一切一切,所有的东西都从它那生出来的;它又不会像春夏秋冬一样,有季节性变化,有兴衰成败。
以下看王弼的注释:“锐挫而无损,纷解而不劳,和光而不污,其体同尘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过其载,天慊其象,德不能过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我们看底下王弼的注“夫执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他说你只要制一家之量,你就不能全家,你不能把所有的家全都知道。“执一国之量者,不能成国”,我就是这个国家,我就是这个本土,我就是要这个,你不能成国。
“穷力举重,不能为用”,我们看举重的那些人,把所有的肌肉都集中在一起,一拿起来用了很多很多的力量举起来,立刻把它放下来。举重就是得了金牌,你能用吗?你能够说把这一百斤、二百斤那来用一用吗?所以说“穷力举重,不能为用”,我们使不上力,因为你力气都用完了。
“故人虽知,万物治也,治而不以二仪之道,则不能赡也。”所以我们人虽然知道万物都料理得很好,治理得很好,你看春天发芽了,随着气侯刚刚温暖发芽了。
夏天那么多的太阳那么多的雨量让它成长,成长到某一些时候花谢了,果子结起来了。整个万物萧条,于是大家都休息,连动物带植物都休息了。这些东西都理得很好,但是你知道万物都由此而治,“治而不以二仪之道”,但是你治又不拿二仪之到,“二仪”是阴阳的两道。
不用阴阳的两道,阴的有阴的,阳的有阳的,有正面有反面。那么你有阳的是进取,阴的守堂。你不用这个东西,你只是意气一直往前冲,或者你一直的保守不成,你必须阴阳两者兼用。那么则不能瞻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仰,你必须知道阴阳两道,于是有收有放,有阴有阳,有正有负,把这些都知道了,于是你才能够满足,才能够瞻。
那么“地虽形魄,不法于天则不能全其宁”,地有形,现在是外国还是中国说了,说是原来地也在那吐气,其实我们住在北方的人都知道,尤其是在山西时候,叫做大地噫气。大地会叹气的,所以当大地叹气的时候,当地的居民都躲开,那个不得了,碰到就会死。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的话,地虽然有形有魄,可是假设不法于天你要不按照天来做的话,则不能全其宁,地就不能够全其宁,于是地震、山崩都出来了,如果你不按照天来做的话。
“天虽精象,不法于道则不能保其精。”天是非常精,它的象是精的,但是你要不按照道来做的话,你说我违背道做,则不能保其精。“冲而用之,用乃不能穷”,你能够虚无的用它,于是用就无穷了。
我们再怎么发明,谁发明的,我们脑子发明的,我们脑子哪里来的,来自道。所以这些东西冲而用之,用才不能穷。“满亦造实,实来则已”,你要满你把它实实在在了,只要实实在在就蔓出来了。我们吃东西所以说吃七分饱,为什么?吃太饱了打嗝了等等都来了,你就出毛病了,所以绝对不能满,“满则溢,故冲而用之”,所以必须要“冲而用之”。
“又复不盈”,不能够太满,还要冲而用之,虚的用可是还要不满。“其为无穷亦已极矣”,所以能够这样的话,这可是真是无穷到了极点,永远用不完。
“形虽大,不能累其体”,这个形大大到不得了,他不会说我太大了,我走不动了,不会的。“事虽殷,不能充其量”,它做的事情多少。我们这人从那么一点点变成这么多人,这些东西你不能够充其量,说我的量已经充满了,不会的。
那么“万物舍此而求主,主其安在乎”,万物把道舍掉了,来求造物的主。主在哪里?所以“不亦渊兮似万物之宗乎”,所以就是这么个东西,你看不见,听不到抓不到,这个就深到不可以知道,这不就是万物之宗嘛。
你挫了他锐而无损,你把锐去掉了,还没有伤害到它。“纷解而不劳”,我们要替人家解纷,很累。这个解其纷不累,永远在解纷。“和光而不污其体”,它跟大家光一样,没有说一个人特别是是光说我是光你跟着我来,而它本体并不受污染。
“同尘而不渝其真”,同尘跟大家完全一样,可是并不来减少它的真。所以“不亦湛兮似或存乎”,一个东西能够这样,这不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真存在嘛。
“地守其形,德不能过其载”,地能够守其形,它的所得《道德经》的“得”就是得到的得。所以拿这个来解《道德经》我只要走这条路,按照道走我就有所得。“德不能过其载”,假如地守其形,你的德不会说我太重了,人太多了,我受不了了,没有的。
“天谦其象,德不能过其覆”,天只要能够把这个东西按照道来走,于是你的德不会说过其覆,超过它的负担。“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他说连天地都不能够超过它,所以这样的话不是就是四帝之先吗?比天地还在以前呢。“帝,天帝也”,帝是什么就是天地,天帝是什么就是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