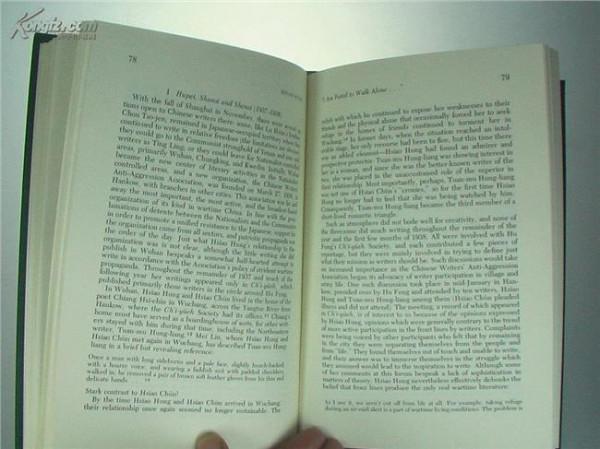马金莲和萧红 马金莲专栏:一个女人和一眼清泉
我们能记事起,她已经是个很老的老奶奶了。
老奶奶是个寡言的人,家在扇子湾最西边的沟畔上,她家的院里院外都是树。杏树,梨树,樱桃树,总之都是能结出果子的稀罕树。每年的五月天气,樱桃红了,映红了庄子西边的那个土院子,也映红了娃娃们的眼睛,就有油皮的半大小子伺机去偷。
看樱桃的是老奶奶,她喜欢坐在樱桃树下默默想心事,有孩子前去做贼,她不声张,静静地看着你一点一点靠近。等你一抬头,正撞上一双安静的眼睛,她在看着你蹑手蹑脚做贼的情景。偷嘴的人就会羞愧难当,恨不能找个地缝儿钻了进去,她却平静地开口,说想吃樱桃,自家揪去。再追加一句,不要把树股子踏折啊。
做贼的人顿时更加羞愧,草草揪一把,转身就走,樱桃吃进嘴里尝不出啥滋味。自古贼娃子都是被人追打喊骂的,这老奶奶却神色平静地以礼相待,自然,就连不懂事的娃娃也难为情起来,怎好意思再去偷盗呢。老奶奶终日守着满树熟透的红樱桃,大概也觉得寂寞,就招呼门槛下过路的人,叫大家缓缓,吃个樱桃。吃完,叫女人们再揪上些,揣在衣襟里拿回去给娃娃们尝鲜。
樱桃落尽,再看见老奶奶的身影,是在水沟里。扇子湾的水沟道路屈曲蜿蜒,大伙都在上游的大泉里担水。河水到了老奶奶家附近,已经是下游了。老奶奶的儿子打了水井,水旺旺的。老奶奶不用井里的水,坚持到沟里担。
她担水的情景我们放羊时见过,从她家门前开始,一条羊肠小道,弯弯地通到沟底,沟底一眼泉,不大,水也不旺,是个渗泉,水就在那红泥土的泉底子里一点一点渗出来。这样的水,一天一夜才能渗满一泉的吧。
暖暖的阳光下,老奶奶摸索着来担水。这时节她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瞎,想必隐隐约约能看清路。她一手抓着水担的铁钩,一手摸索走下沟来。她脚下的路实在陡得可怕,看着她颤巍巍的姿势,叫人心里直打颤,这情形,真的很凶险。万一,万一她一步走不稳,那就会一个跟头栽下陡峭的悬壁。
老奶奶走惯了这路,摸下沟底,到水泉边,跪在地上,弯腰舀水。一个木头挖成的马勺,一点一点舀起清水,舀满一个小铁桶和一个洗大净用的瓦罐。舀满水,她不急于起身回家,坐在泉边歇缓。姿势悠悠的,显得从容不迫。我们放羊娃的笑语传进她耳朵里了,她抬头望我们,看一阵,起身无声地上路。
回去的路陡峭,难行。她还是一手抓铁钩,一手扶住土崖,颤巍巍走,两步一个台阶,两步一个台阶。光溜溜的黄土台阶,不知道最初是谁踩踏出来的,老奶奶慢悠悠行走着,每天一回,担回一点清水去。
老奶奶的小孙女和我们一起放羊,看见奶奶担水就鼻子哼哼,说奶奶古怪,不用家里的井水,偏偏冒险到沟里担水,不晓得的人还会以为儿子媳妇糟践她哩。
老奶奶担水是为了自己洗大小净,一天五番乃麻子,她一番也不撇的。
当年,老奶奶并不是回民出身,大饥荒时从南边逃荒上来的,当时是一个小媳妇儿,蓬头垢面的,饿晕在村口,村里一个女人给了些吃的,她就活下来了,而且不愿意再走了。过几天又来一个男人,也是从陕西逃荒上来的汉民,也留在了扇子湾。在庄里人的帮助下,这一男一女结了夫妻,进了教,从此就成了老回回。
经过了很多年日子,老奶奶的身上已经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汉民迹象,只有口音中还残留了一些那个地方的方言。
九十年代,每到夏天,附近的壮劳力结伙下陕西去赶麦场,老奶奶的儿子也在其中。后来就有人说这儿子一到汉中地界就甩开大伙儿,一个人行动了,在到处打听一家人的音讯,可能正是老奶奶当年逃荒时留下的丈夫和孩子,据说一共三个娃呢,算来都已经成年了。
到底寻访到了没有,我们便不得而知,老奶奶和她的儿子是不愿意村庄里的人打听这些事情的。
扇子湾的人都敬重老人的作为,早就忘了她原来的出身,说她是真正的老回回。她那个媳妇的脏、懒是出了名的,老奶奶正是嫌弃媳妇从井里吊上的水不够干净,所以宁愿亲自去沟里担泉水。
老奶奶坚持担了十来年的水,后来眼睛彻底瞎了,下沟的泉边就再也见不到她担水的身影了。后来老人无常了,下沟的水泉被坍塌的泥土埋没,再也难以找到那些羊肠子般小路的踪迹。时光漫漶,竟连那条弯弯的小路也塌光了,现在的放羊娃看见的,是一面光秃秃的土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