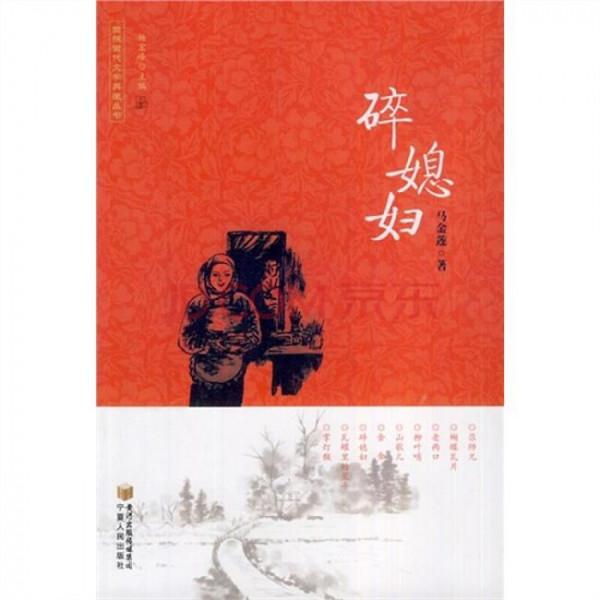马金莲的歌 乡土的余温——评马金莲的小说创作
在当下文学格局中,马金莲是一个特殊的存在。面对马金莲的创作,“80后”、女性文学等驾轻就熟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这位来自于宁夏西海固的青年作家,用回族女性隐忍的目光审视着属于她的那片土地,讲述着乡村中国剩余的故事。
她不依赖炫目的现代小说技巧和“望乡”式的写作姿态,而是用平实的文字将个体经验和乡间故事转换为充满温情的文学表达,再现了乡村社会中的超稳定文化结构和现代化浸染下的乡土嬗变。在乡土文学从百年中国文学中的主流地位旁落的当下,马金莲的文字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乡土中国的情感温度,而这也注定了只能是乡村文明光焰将逝的余温。
回族乡村的超稳定文化结构
西海固是马金莲的文学地标,它之于作家,意义不啻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和贾平凹的三秦大地。面对这一文学地理版图,马金莲回溯到历史的纵深处,通过村民应对饥荒和权力关系的行为、心理方式,揭示出流淌在乡村中国最底层的超稳定文化结构。
所谓“超稳定文化结构”是指“在中国乡村社会一直延续的乡村的风俗风情、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由于马金莲所处的社会群落是深受伊斯兰教教义影响的民族共同体,与主流的传统乡村社会所因循的儒家伦理截然不同,宗教是回族想象自我的基石。这就在另一种价值体系的观照下,为中国乡土社会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再发现提供了新的可能和表达对象。
从这一价值立场来看,《老人与窑》可以视为乡村超稳定文化结构对于权力关系的胜利。在五六十年代的农村运动中,“大养其猪”曾为中央所倡导,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而猪却是回民的禁忌,当从外地调来的唐队长不顾回民的生活禁忌,为了响应运动的号召而强迫各家各户养猪时,回乡中的超稳定文化结构就与权力关系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
唐队长是素为村民畏惧的威权人物,在村民眼中,他是国家权力意志的化身。而此时的宗教处于被压抑的地位。
这场力量悬殊的角逐最终的结果,却是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凭借民间的力量以潜在的对抗方式取胜。面对外部压力,形成于回民传统的文化结构依旧占据了民间的话语空间。它是如此稳定和富有力量,以至于在饥饿到每日只能以一个洋芋果腹时,“我”还是会本能地拒绝汉族羊倌烤食的鸟肉。
作为阿訇的老疯子才会对自己与唐队长的妥协愧疚不已,只有在“我”不断的诵经中才能减缓心灵的痛苦。规训和惩罚机制使得传统乡村社会中的精神价值只能以潜流的方式存在,但这一潜流却具有持久、强大的超越力量。
马金莲对于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再现还通过饥荒年代时乡村温情展开。西海固位于宁夏南部的黄土丘陵地区,有着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断定为“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的地区。如非有切肤的饥饿体验,作家很难用如此平实却又真切的文字书写出人类对于饥饿的感受。
在以残酷的饥荒书写再现凋敝的乡村图景时,马金莲并没有美化苦难,为受难者正名的政治诉求。她秉持去政治化的态度,将宏大的历史主旨置于小说叙事之外,着力于发掘饥荒之际的人性温暖。
马金莲笔下并不乏残酷的饥荒书写。在莫言的《丰乳肥臀》中,为阻止饥饿的人们偷食,母亲同其他妇女被戴上了笼头像牲畜一样劳作。《父亲的雪》中也有这样一处情节:生产队队长为了制止播种时偷吃种子的行为,甚至采取了将尿掺在其中的办法。
这些非人的举措显示了饥荒岁月时个体遭受的屈辱。然而这并不是作家书写的重点。作家藉此经由饥饿体验打通了西海固的历史和现实。在将饥荒日常化、主体化的同时,马金莲关注的是人的应对方式及在其中的情感体验,展现饥荒之际的人情与人性。
在极端困难的日子里,巴巴、二娘、母亲都以各自的方式给予“我”生存的可能。尤其是与“我”没有血亲的新大,大爱至隐,在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地给予温暖。人的自尊、责任以及人际间的温情读来感人至深,让我们看到了回族民间的情感温度。
换个角度来看,面对强权和饥荒中的非人道因素,叙述中作家并没有表现出其他此类作品中常有的义愤与激烈,反而在女性温婉的叙述中发掘植根于民族传统的乡土温情。在诸如《坚硬的月光》等文本中,回族女性隐忍的品格被演绎到了极致。
或许在回族乡间,这种品格即是作家延续传统对于乡土女性应有的美德的认定。无疑,作家对此是认同的。依此来看,在当下文化语境中,作家自身认同的,以女权观点来看略显陈旧的女性观念也可视为乡村超稳定文化结构的体现,与作家的叙述本身共同构成了认知乡土社会的路向。
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嬗变
能够颠覆乡村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力量并非来自于外部的政治压力,而是在现代性的询唤下,乡村文明内部的精神裂变。现代性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乡村文明的崩溃和城市文明的崛起已成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也促成了中国乡土文学在百年叙事传统中的又一次新变。
对当代文坛保持关注的读者不难发现,书写乡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嬗变业已成为当下乡土叙述中的主流。这其中既有关仁山的《日头》这种反映乡村文明崩溃的作品,也有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这类表现全球化语境下乡村文明现代境遇的文学表达,还有诸如梁鸿《中国在梁庄》的非虚构文本。
至于贾平凹、周大新、刘庆邦等一批活跃在文坛前线的优秀作家更是持久地关注着变革时期的乡土社会。这为我们审视马金莲的乡土叙述提供了有效的参照系,也对作家的创作构成了挑战。
以历时性的文学传统和共时性的文学场来看,马金莲的文学创作不失其独到之处。大多数作家的乡土叙述普遍是在离开乡村之后,对乡村历史和现实的回忆或观察。他们在城市享受着现代化的成果,并将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作为观照乡土中国的价值立场。
据此,他们的乡土叙述能够在与城市的对话中展开,却也因为与乡村生活的距离,无法细腻地感受现代性对乡村的侵蚀。马金莲却得益于以乡村文明崩溃亲历者的视角,补足了这一乡土叙述中的晦暗地带。
迄今为止,她的生活经历都扎根于乡土之中,甚至有几年的时间纯粹是以普通乡村妇女的身份生活。因此,马金莲的乡土叙述有效地祛除了“代言人”身份的虚妄性,将乡村从被言说的对象变成了言说自我的主体。切近于乡土社会的立场一方面使她的乡土叙述缺乏城市文明作为背景,另一方面却也使她能够敏锐地体察乡村的精神价值正在发生的变化,并经由日常生活这一叙事空间,在细微处展现乡村文明和现代性的碰撞。
《项链》是一篇十分巧妙的短篇佳品,讲述的是麦香出嫁时因彩礼引起的风波。突然回乡的麦花使本已谈定的婚事顿起波澜。麦花是麦香的姐姐,早年出嫁新疆——这个在东部地区看来需要对口援建的边疆之地,却是西海固想象城市文明的载体——现在已经出落为“富态臃肿高贵优雅”的妇人。
城市化了的麦花告别了乡村传统,也在乡村事务中占据了话语权的优越地位。在她力主之下,麦香最终获得了金项链,却也在婚后生活中成为麦香与婆家难以弥合的裂痕。
作为城市文明思维逻辑的产物,项链在麦香生活中的境遇暗示了现代性在乡村现实中的水土不服。《舍舍》则通过一次意外的车祸展现了金钱对民间超稳定文化结构的震荡。舍舍是马金莲理想的女性形象。她利索、俊美,既能在田间地头劳作,也是庭院里的能手。
更重要的是她能够在“年轻人都效仿城里人,厌弃山里保留的回民头饰”时,遵循教门上的传统,始终坚持佩戴头巾。她的身上摇曳着传统回民乡村社会认可的女性高贵品格的光辉。
然而,丈夫黑娃的意外事故却考验着乡间的伦理秩序。面对不菲的赔偿款,在公婆那里,老年丧子的人生剧痛转瞬就化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对爱情坚贞的舍舍却被娘家人视为“瓜女子”。文本最后,在村民讲述中,舍舍终于“摘了帽子,取下盖头,把头发烫成卷儿,波浪一样披着,据说,那样子,远远比戴着盖头洋气”。然而,村民及其背后的作家却无奈叹惋“还是原来那个戴着绿盖头的舍舍好看些,才是大家心里真正的舍舍”。
可以说,在马金莲笔下,现代性与乡村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冲突是清真寺唤礼拜用木梆子还是电喇叭的冲突,也是在家长里短和针头线脑中的冲突。一条项链、一方头巾,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却奏响了乡村文明崩溃的序曲,冷却了传统价值伦理的脉脉温情。
作家的两难
对乡土的现实变革有切实感受的作家,在书写当代乡村境遇时,几乎都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是作家充满眷恋的乡村文明,另一方面是具有历史合目的性、不可阻挡的现代性,马金莲也面临着同样的两难处境。
无疑,马金莲的情感天平是倾向于乡村的。对饥荒年代的追述寄托了马金莲对传统乡村的认同。这是有情感温度的乡村。不论是民族、宗教还是历史传统的规约,这些对村民做出行为规范的准则最终都归源于爱。而在现实境遇下,现代化在丰富乡村物质生活的同时,其弊端也暴露无遗。
乡村解决了饥荒的困扰,道德秩序却悄然崩塌,人与人之间的爱的伦理准则被金钱的实用准则取代。于是,作家一方面欣喜于现代乡村的物质富足,另一方面却又缅怀逝去的孕育于传统乡村的精神价值。
所以,在文本中我们看到,面对那些在历史上经受了苦难和人情考验的人物时,马金莲总是将现实简单化、理想化为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延续,以此对他们的苦难予以补偿。如《长河》中的穆萨爷爷,他在“社教”运动和饥荒时的义举是作家赋予他在现实中备受崇敬和物质富足的资本。
而在另外的大多数文本中,随着生活富足而来的恰恰是对穆萨爷爷所代表的那一套价值体系的解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视为作家在前现代文明立场上对现代性的拒斥。
马金莲就在这种两难处境中犹疑和矛盾。有时她可以深入到乡村文化肌理的深处,挖掘出其中的超稳定文化结构。通过《长河》《赛麦的院子》《坚硬的月光》等一系列文本,其他读者经验之外的,回族乡间的生死观、生育观以及妇女的生活伦理得到了文学化的呈现。
这种对回族传统乡村价值的再发现,在当下文学创作中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另一些时候,她却不免将传统乡村社会道德化,以二元对立的模式叙述乡村的历史和现实。《口唤》或可算作此种思维模式下的失败文本。
在大伯讲述爷爷遗愿的过程中,新一代的市侩、世俗处处与老一代的善良、感恩对立,将后者始终衬托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作家又通过大伯之口发出了“不像现在那么心眼儿多,老古时人都直得很”的感叹。
这就不免带有道学说教的痕迹,文本的艺术性由此大打折扣。同时,这也将现代乡村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简化为了道德问题,仿佛只有经由回归传统一途才能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精神危机。如何在这种两难困境中突围,处理好情感认同与乡土现实之间的矛盾是马金莲在日后创作中不得不正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