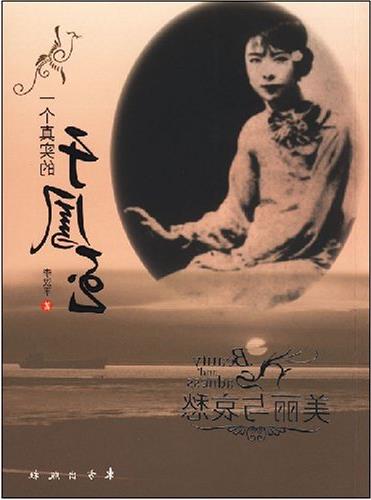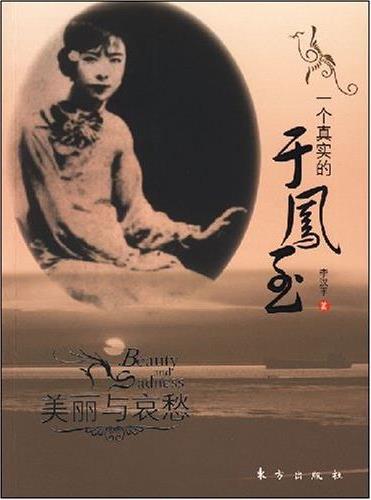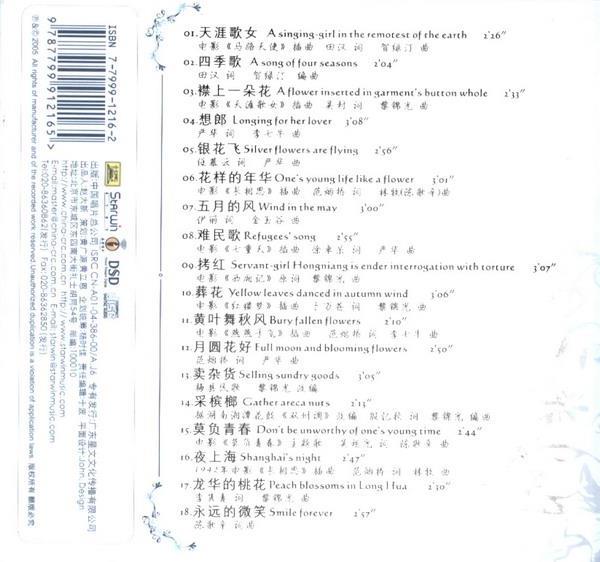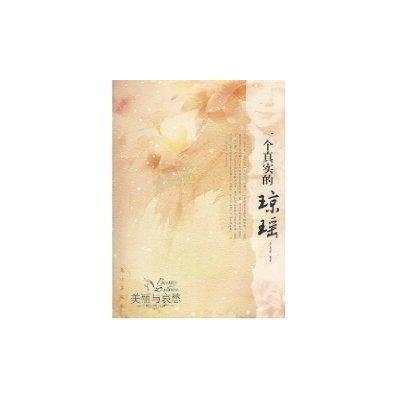一个真实的陈寅恪
中山大学永芳堂,陈寅恪的铜像就屹立在大堂中央。
这尊铜像,是以历史系78级全体同学的名义捐建的,作为陈寅恪的再传弟子,他们请来了最好的雕塑家。满头白发的蔡鸿生教授说:“要将盲者的眼睛雕塑出来,是最难的。”
而铜像上,一代大师失明的眼中分明泛着光芒。
1 绕不开的高峰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生于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是现代中国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这位享有崇高地位的学者,辞世几十年后,仍然是学界绕不开的高峰;他的学术造诣,他非凡的记忆力和语言能力,他终身坚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甚至成为普通公众津津乐道的话题,虽然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根本无法读懂他的任何一本著作。而对于他最后几年的生活,更是曾惹来争议:一代大师,是在悲惨中逝去的吗?所在的中山大学曾“有计划地迫害”他吗?
在陈寅恪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走访了中山大学历史系胡守为、蔡鸿生、姜伯勤三位教授,以作求证,陪同我们采访的,还有蔡鸿生的学生章文钦教授。
胡守为,81岁,身体硬朗,言语简洁清晰。原中山大学副校长,历史系教授,曾任陈寅恪先生助手,虽然在采访中,他多次强调:“不要说我是陈先生助手。”
蔡鸿生,77岁,满头白发,清瘦而精神,说话从容不迫。曾任历史系教授兼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姜伯勤,72岁,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他一年前摔断了腿,尽管坐在轮椅上,却精神充沛,声音洪亮,说话的时候,表情很丰富。
2 不要做大师的“追星族”
对于持续的陈寅恪热,三位教授都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忧虑,将大师戏剧化、明星化、神化,都是对陈先生学术精神的背离。
姜伯勤有些言辞激动:“不要神化陈寅恪。”
他说:“现在有关陈寅恪的书,很多是不可信的,材料转了很多手,以讹传讹。比如,说陈先生‘精通十几国语言’,真相是他在德国受过比较语言学的训练。陈寅恪的教师履历只写了德语,胡守为老师见过的。”
又比如那个著名的“三不讲”,说陈寅恪说过这样的话,‘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三不讲’,是错的。这些不澄清,有损陈寅恪的形象!”
讲到这里,年过八十仍很精神的胡守为补充道:“我保存了不止一种《两晋南北朝史》讲义,陈先生去年讲的一些东西,今年讲了,明年还会讲。懂得教学的人都知道,同一门课,每年都讲新的内容,怎么可能?”
对陈寅恪先生最好的纪念,应该是不虚饰,不溢美,以历史的态度,还原一个真实的大师。无怪蔡鸿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九泉并非热土,让大师回归自然吧!”
3 活得有尊严,死得也有尊严
坊间报刊有人说陈寅恪生活上受虐待,甚至说中山大学有计划地迫害陈寅恪,胡守为、蔡鸿生和姜伯勤均表示异议。
他们回忆,当时陈寅恪喜欢用旧时的宽稿纸,中大党委书记冯乃超就用最好的纸张请印刷厂给他印了稿纸。从冯乃超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都很照顾他的生活。在饮食上,陈先生是全盘西化的,这些都得到保障,当时的校工彬叔(梁彬),每天骑着单车到华南农学院去拿牛奶回来给他。那个时候全中国多少人都在吃红薯呢。
学校有口鱼塘,每次打鱼分鱼,不是每个人都能分到的,但陈先生每次都有的。所以吴宓来拜访,他说留下来吃个便饭,家里没什么别的,有鱼。那个时候,有鱼吃很不容易了。
为了照顾他,学校派了三个护士,还有助手、校工。陈寅恪当时的工资是381元,当时在中大叫381高地,另外还有一些车马费,比如全国政协委员、文史馆副馆长的补贴。那个时候,学生的伙食费一个月才12.5元,已经吃得很好了。
陈寅恪爱听京戏,广州京剧团的新谷莺等到他家里唱给他听的;平时他也听收音机,听读旧小说。心情好的时候,他也会接受别人的拜年。
蔡鸿生表示,陈先生生活上得到照顾,学术上被批判,在精神上不会没有痛苦。但就如我六年前在《仰望陈寅恪》一书里说的,不应该把他的悲剧结局扩大化。事实上,晚年的陈寅恪并不是度过漫漫寒夜,其间也有阳光和欢乐。和同时代人相比,可以说他活得尊严,也死得尊严。
4 陈寅恪没有被斗过
陈先生在校园里住过三处,西南区五十二号、东南区一号、西南区五十号。他受冲击最严重的是1969年春节后搬到西南区五十号那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只有夫人唐筼陪着他,身体不好,存款被冻结,每月只有25元的生活费。一代史学家,最后的生命是一部断肠史。
那么,在文革期间,陈寅恪究竟有没有挨过批斗?胡守为肯定地回答:“陈先生没有被斗过。”
有些书中写道,当时的历史系主任刘节曾经表示:“能代老师挨批斗是我的荣幸!”既然没有被斗,为什么刘节会说这样的话?胡守为说:“刘节是那样表示过,但最终是否代替陈先生挨斗了,并没有依据。”
姜伯勤认为,当时中大的领导冯乃超、杜国庠都是真正的教育家,他们很懂陈先生的价值。中大的周连宽老师、黄萱老师等都通过各种关系为陈先生寻找学术研究资料。至于后来的磨难,姜伯勤说:文革是佛学所说的劫。这是人类的灾难,谁能幸免?
5 最伤心的事
陈寅恪是学者,也是老师。从1926年进入清华,直到1958年6月,他整整教了32年的书。
岭南大学时代,有一次学生送他一面“万世师表”的锦旗,他非常高兴,与学生一起照了相。胡守为回忆,“那天是6月6日,我当时在场。有的地方把说明弄错了,那不是毕业生送的,是教师节的纪念。” 6月6日,是1931年确立的教师节,到1951年才取消。
胡守为说,陈先生教书是很负责任的,从不缺课。他曾经因为自己心脏病请过一周假,另外,就是因夫人病重请过一次假。他一生都很想将他的学问传给别人的。所以,他当初不愿意去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后来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也推辞掉,就是想教书。
陈寅恪并不是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人。比如,他非常拥护抗美援朝,有诗为证。他是中国民族本位的学人,对历史和现实都比较清醒的,所以他曾对浦江清先生说,“胡适是非走不可的,我可走可不走……我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我只是反对俄国式共产主义。”
尽管如此,陈寅恪还是在1958年之后就离开了讲台。
那一年,有学生贴出大字报,说他“误人子弟”。从此他“拒绝”上课。“误人子弟嘛!我不教书了!”这件事很伤他的心。
6 陈寅恪情结
陈寅恪的著作,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曾说“多数人恐亦不懂他说些什么”。胡守为、蔡鸿生和姜伯勤都说,有些我们也读不懂,陈先生的学术思想要慢慢理解的。当年历史系七八级学生章文钦这样讲述自己的读书经历:大学的时候,读《柳如是别传》读不懂,没读完,直到后来读博的时候,才读了一遍。
而傅斯年的评价是:“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天生大才,后来却醉心于为一位歌妓立传,招来后人的一些疑惑和猜测。姜伯勤对此别有解读:《柳如是别传》是陈先生的压卷之作,是他一辈子的力作。钱柳著作在清代是禁书,柳如是在20世纪初是学术前沿。1913年王国维《东山杂记》就研究柳如是,到1920年又研究柳如是尺牍;罗振玉也研究柳如是。可见,“别传”不是即兴之作,不是影射史学,而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在图书馆学专家周连宽、潘景郑等人支持下完成的世纪性课题。
1957年,中大曾经向陈寅恪表达给他多配一名助手的意思,一方面帮助陈先生完成学术著作,一方面去了解陈先生的学术渊源和成就。北京有些人却以为是派去监视他。
胡守为说,陈寅恪是文化托命之人,要理解陈寅恪,就要像姜伯勤老师说的那样,继承他的学术精神;不要写我是陈先生的助手,季羡林和蒋天枢才是陈先生的学生……
三位教授都谈到,近些年来,高校学术传统和学术精神被淡化、边缘化。但中大历史系,不愧为陈先生播种过的地方,他的学术传统,在历史系培养的学人中,仍可看出深远的影响。比如湛如、林悟殊、章文钦、林英、吴义雄和茅海建,都很好地体现了陈先生留下的学术传统。
章文钦教授向我解释,胡守为先生不让提“助手”,其实中大举办了三次纪念陈寅恪的研讨会,都是他组织的。胡守为老师、蔡鸿生老师和姜伯勤老师,都是陈寅恪先生学术精神的传承者,都有陈寅恪情结。
采访结束,走出历史系会客室的时候,我再一次注意到陈寅恪的铜像。
这尊出自著名雕塑家唐大禧之手的半身铜像,比常人要高,所有经过铜像的人,都须仰视。
而铜像后的屏风上刻着陈寅恪写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的句子:“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也许,这就是一代大师留给后人最大的精神遗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