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周口沈丘癌症村死亡倒计时【组图】
据《新京报》之前报道:过去十多年中,淮河流域内的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多发“癌症村”。更早之前,在粗放追求GDP的年代,淮河及其支流被大小工厂污染。村民们的水井越打越深。不过死亡还在增加。河南沈丘县1年因癌亡2000人。
一
中午强烈的阳光照射在死气沉沉的村庄上,刘玉芝家的房子灰暗老旧,在黄孟营村并不难找到。我们透过低矮的院墙看见鸡鸭在烂泥地里奔走觅食。刘玉芝从小屋里颤颤巍巍走出来,右手拄着一根树枝做成的拐杖,仿佛每走一步都很吃力,都很痛苦。
刘玉芝罹患骨癌多年,面色惨白,身形枯槁。她住在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屋子里,房顶是木质材料,光线从房顶的窟窿照射到泥土地面上,斑驳陆离,一如她将死的身躯上那一双依旧明亮的双眼,在告诉世人这饱尝疾病折磨的变形的躯壳里,还有一个渴望生活的灵魂依然在发出微弱的光芒。
刘玉芝无法长时间行走,活动范围仅限于自家小院。这些天丈夫出苦力给村民盖房,女儿在棉花地里给棉花授粉。父女俩顶着烈日干一天活,也就挣五十来块钱。
这个贫穷艰难的家庭无法担负刘玉芝的治疗费用,刘唯一的治疗方式就是吃止疼片。刘玉芝说着话,两手不断搓来搓去,她说疼,手疼,背上也疼,每天都很疼。刘睡在一张单人床上,床头柜上放着止疼药、水杯、电扇和《圣经》。我实在没有勇气谈及她的病情,简单问过几句她的情况后,我们聊起了登山宝训。
"你热不热?"刘玉芝忽然问我。屋子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通风透气,当地中午的气温恐怕已经接近40度。刘说着站起来,要开床头柜上的电扇。我急忙说:"我不热,我体寒,不怕热。"刘不听,坚持要开电扇,揿过按钮后,电扇发出吱吱响声,扇叶并不见转动。刘羞赧的说:"过一会儿,就转了。"我和她继续聊家常,聊《新约》。刘的眼角垂着泪,眼睛放着光。我看着心如刀绞,无言以对。刘心里还在惦记着我热不热,看电扇老不转,怕我热,拿起身边的一块塑料板,要给我扇凉。我急忙起身拿过来塑料板,再三解释说自己真的不热。
"我也不热,我早就不知道什么是冷什么是热了。"她说。
丈夫孙逢环和女儿孙美慈中午回到家,准备吃饭。孙逢环五十出头,驼背,脸上布满皱褶,头发灰白相间,干完活一脸疲惫。他见到我们很热情,微笑着和我们说话。
女儿孙美慈今年在县直中学读高二,家里无力负担每年五六千的学费住宿费,她随时有辍学的危险。正在放暑假,她在村里找了"对花"的活儿,每天早出晚归,赚二十块钱,她说还能再做四天,过后要再找别的活儿。
为贴补家用,美慈有意蓄长发,过三四年,头发长了,剪掉,卖钱,一次能卖四百多块。她说,她的理想是考上大学,毕业后找份好工作,赚钱,养活爸妈。
二
在黄孟营有很多刘玉芝这样的癌症患者,在沈丘县有很多黄孟营这样的癌症村。距离黄孟营二十里的东孙楼的村民,多年来亦饱尝癌症之苦。
东孙楼村有一条街名为"癌症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条街的每户人家里都至少有一位癌症病人。如今病人纷纷去世,有的房屋无人居住,日渐破败,杂草丛生,以至坍塌。王子清大爷的弟弟当年就在这条街住。二零零三年,在一个月内,王大爷的哥哥和弟弟因癌症相继去世。
王大爷出生于1942年,那一年河南爆发了"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王大爷这一生与忧患相伴。一出生赶上大饥荒、中日战争,紧接着国共内战,熬过40年代,到五十年代,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肃反、四清、三反、五反……1959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河南周口也是重灾区。文革期间,1975年8月板桥水库溃坝,河南30余万人罹难,周口亦无法幸免水患。
沙颍河乃淮河最大支流,周口就在沙颍河畔。为消除旱涝,引水灌溉,从1975年起,王大爷和相亲们开始挖沟渠,引沙颍河水入沈丘。一条条沟渠自此遍布沈丘大地,如同一道道血管渗入沈丘的肌理。东孙楼边的一条沟叫"颂华沟",取义"歌颂华国锋"。王大爷的俩兄弟去世后,坟墓就在"颂华沟"旁的玉米地里。
王大爷说,沟渠挖成后,灌溉吃水都方便了,过了几年好日子。然而好景不长,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各种制革厂、造纸厂、玻璃厂、化肥厂纷纷出现在沙颍河两岸。上游的郑州、开封、漯河、许昌、周口、项城等地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全都被排放到沙颍河支流,在周口汇入沙颍河。污水再顺着沟渠流入沈丘各个村庄。沈丘乃至整个周口都属于低洼地带,污水一旦流入,便无法排出,唯有慢慢渗入地下。当初造福村民的沟渠,变成吃人的毒蛇,将一个个村庄死死缠绕。
没人敢喝沟里的水,没人敢下到沟里洗澡。癌症病人骤增,每年几十、几百、甚至几千的村民患癌症去世。这里变成了笼罩在死亡阴影下的"癌症村"。
新京报记者王瑞峰撰文指出:国家疾控中心对沈丘研究区的5万人跟踪3年调查发现,2005年与1973年对比,排除人口老化因素后,男性和女性肺癌死亡率分别上升了14倍和20倍,肝癌死亡率上升了5.23倍和4.80倍。在其他地区胃癌和食道癌死亡率普遍下降的背景下,沈丘的这两类肿瘤的上升却非常突出。
三
王大爷患有胃穿孔,大腿有伤,走路不便,推着自行车走路更省力。他带我们穿过玉米地,路过墓地,去看"颂华沟"。沟已经干涸,沟床长满杂草。王大爷说,村民在沟上建土坝,拦截沙颍河的污水,但有时为灌溉,不得不放水进来。
回来的路上,我们请王大爷骑上自行车先回去,我们在后边走,王大爷说:"你们从四五百里远的郑州过来,都不怕累,我走两里地,怕啥累。"王大爷告诉我们他的座右铭是:大家幸福。沈丘环保志愿者"淮河卫士"和王大爷在他家门口建起了一座生物净水装置。王大爷负责净水装置日常维修,担负电费,村民们可以免费来提水。
沈丘癌症暴发因水污染而起,缓解癌症蔓延之道在于让村民喝上干净卫生的水。
从九十年代起,村民打井越来越深,从几十米一直到上百米。现在村民必须打四五百米的深井,才可能抽上干净的水。但打这样一口深井的费用造价一两百万,绝非癌症村的村民可以负担。
当地政府给癌症村财政补贴,用于打深井,但打出来的水水质依然成问题。当地村民抱怨说,这是因为施工人员偷工减料,下的管子只有一百多米深。
四
央视网评针对癌症村现象说道:"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为振兴当地经济,实现GDP快速增长,饥不择食,大量引进、接收重污染的工业,将地方经济发展凌驾于民众的健康和生命之上。"过去三十余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建立在环境破坏和低人权的基础之上。民众付出汗水和辛劳,承受着环境污染之害,但没有享受多少经济发展的成果。
当民众没有最起码的公民权,其所谓的生存权或健康权也无从保障。在发展国家经济的宏大叙事下,个体的生命和健康,往往被无情践踏。那些因环境污染而身患癌症的村民,没有呐喊,没有抗议,只能忍受残酷的命运,一个挨一个默默死去。
我们在当地想询问村医,医生脸上即刻露出为难和警惕的神色,不愿多言。医生的确没有多言,然而乡党委书记还是给他打来电话,威胁医生把卫生所从村里搬走。沈丘癌症村的恐怖不仅来自于癌症,还来自于部分官员施加于民众头上的淫威。
五
黄昏时分,村民提着水桶陆续来王大爷家的生物净水装置旁取水。这座生物净水装置是"淮河卫士"为东孙楼村建造的,王大爷家门前的这座已投入使用,另一座正在建造中。
"淮河卫士"霍雅伦大学美术系毕业后又进修了微生物学。随即跟着父亲霍岱珊一起从事保护淮河的工作。"淮河卫士"的环保活动得罪不少当地企业主和官员,一直受到人身威胁。霍雅伦坚持体育锻炼,除了做公益事业,也充当父亲的保镖。他正在东孙楼给生物净水装置铺设管道。
一座生物净水装置的成本大概4万块钱,一旦建成,可以供给八十户人家喝上清洁的水。截至目前,"淮河卫士"已经给百余村庄建造了二十多个净水装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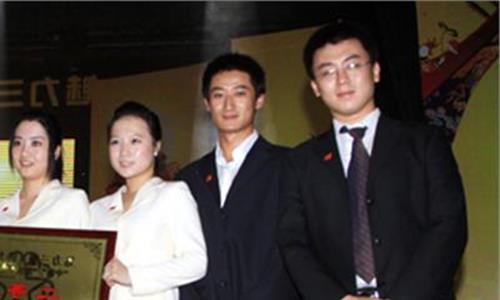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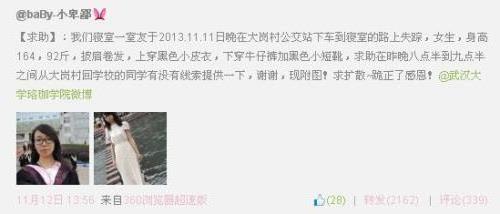

![>2013幅书法作品《中国梦》喜迎祖国华诞 创吉尼斯纪录[组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d/e6/de631f503abdc0053e6577d327859d90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