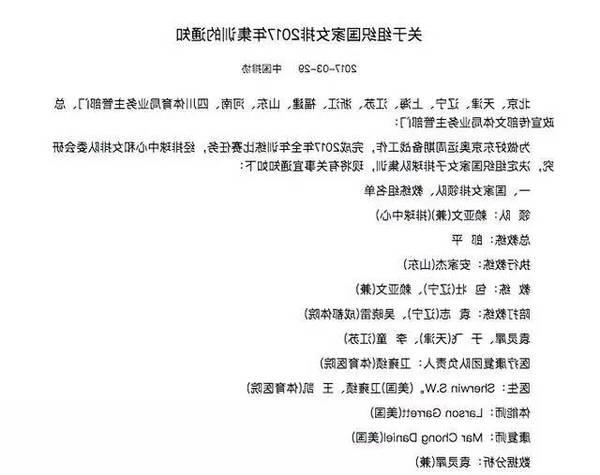郎平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 承受着13亿人的目光
十年后的1995年2月,一条消息在国内激起千层浪——郎平即将回国,执教女排国家队。那时的中国女排,成绩已经下滑至世界第八的历史最低。
2月15日,杨玛俐和《中国体育报》的同事来到首都机场迎接郎平。他们为此办了特殊通行证,可以进入机舱口接机。可当到达机场时,吓了一大跳——持有特殊通行证的记者就有100多个。
除了郎平的父母站在机舱口两边准备献花外,扛着机器的摄影记者用胳膊肘相互挤来挤去,只为抢到好的拍摄角度。等舱门一开,记者们都傻眼了——《焦点访谈》的记者钻到了飞机底下,郎平一下飞机,他们就倒退着拍她走出来的全过程,阻挡了门边所有的记者的视线。“大家开始拼命地往前涌,郎平妈妈只跟她碰了一下手,就被挤开了。”杨玛俐说。
在这样的阵势下,郎平连行李都没办法取。时任排球协会排球处处长的周晓兰和陈招娣开了辆车去机场,郎平上车以后在机场转了一圈,待记者们散去以后,才又回去取行李、过安检。
之后几天,媒体轰炸式地报道有关郎平的消息。中国女排世界第八名的成绩让民众的不满达到了顶峰,似乎觉得她一回来,“女排精神”也就回来了。
1995年的郎平,正经历着自己人生的重大转折——离婚。而2004年底开始,国内排球界及国家体委的一批人为了请郎平回国,不断地给她发传真、打电话,最后,袁伟民亲自出马。
“中国女排历来有一个传统,即牺牲自己,成全队伍。”新华社记者曲北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郎平当时的想法是,中国女排培养了我,当有需要的时候,我只有无条件地去做。
一上任,她快马加鞭地挑选了一批教练组成员并前往柳州训练基地选拔运动员,很快就组好一支队伍开始集训。然而,当时青黄不接的状况让她觉得自己简直是在带领一个“青年队”。这批女排姑娘连基础动作都还不过关。就这样,全新的中国女排在郎平的带领下,像小学生学拼音一样从头开始。
“郎平的工作时间基本上是全天24小时。”杨玛俐说。有一次,张蓉芳跟她一起去参加比赛,两人聊比赛的事聊到夜里12点才躺下睡觉,到了1点,张蓉芳发现郎平忽然坐起来,一边嘟囔着“我要看录像”,一边打开比赛录像又开始研究。
短短一年半时间,郎平将中国女排带上了1996年奥运会亚军的领奖台上。
而此时的郎平已是心力交瘁。“回来执教,全国人民的重托都压在身上,队伍的情况又不理想,工作特别费心,”郎平回忆道……我脑子里全是球啊,一天到晚就是这些解决不完的问题,就是躺着也很少睡着,睡眠质量差,每天都处在朦朦胧胧的状态中。”
备战奥运会时,由于过度疲劳,她在漳州晕倒过一次;奥运会中与日本比赛的前一天,郎平正在食堂里吃着饭,又感觉到一股凉飕飕的气体从脖子根往上冒。她从桌上滑到地上,嘴角冒白沫,舌头也吐了出来。
亚特兰大奥运会后,郎平与排协的合约也已到期,她也正与美国男朋友交往,国内媒体开始纷纷揣度,郎平似乎要激流勇退。当时中国女排刚刚好转,形势不稳定,排球协会的领导出面挽留。郎平考虑再三,选择留下。她的美国籍男友对此非常不理解,郎平的选择直接导致了他们最终的分手。
郎平又撑了两年。这两年却是她体育生涯中身心最为疲惫的两年。所有的熟人朋友见了她,第一句话往往都是:最近不错,又赢啦!“报刊似乎有个统一的语调:郎平,你何时再创辉煌?”郎平回忆说,可她内心的苦恼和压力,却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我一个人扛着、忍着、憋着,不能说呀,跟谁说?”
“每次大赛回来,她都要大病一场。”杨玛俐回忆说。
1998年对于郎平而言,“实在不平凡”,她在自传中这么记着:11月的世界锦标赛紧接着12月的亚运会———两场大赛,像两个重重的铁砣,沉沉地压着岁末,而1998年的每一天,我们的每个队员都得挤出足够的分量才能扛住这个“砣”,才能平衡这一年。
1998年世界锦标赛,开局小组赛便意外负于韩国队,情势急转直下,极可能被挤出前四,郎平形容自己“心里像着了火”。一个东北的老人见中国2:3输了韩国,一急之下,心脏病发作而死。老先生的朋友给郎平写了信,他大概是想告诉她,女排输赢对于国人意味着什么。
“软软地倚着栏杆,我突然感到一阵很无助的孤独,好像从山顶滚落到深深的峡谷,耸立四周的是悬崖、是峭壁,没有人知道我,没有人来拉我,我只能靠自己一步步地往上爬。我觉得浑身软弱无力,心跳、心慌……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在哪里?”在1998年曲折地夺得世锦赛亚军和亚运会冠军后,郎平第二次离开了中国女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