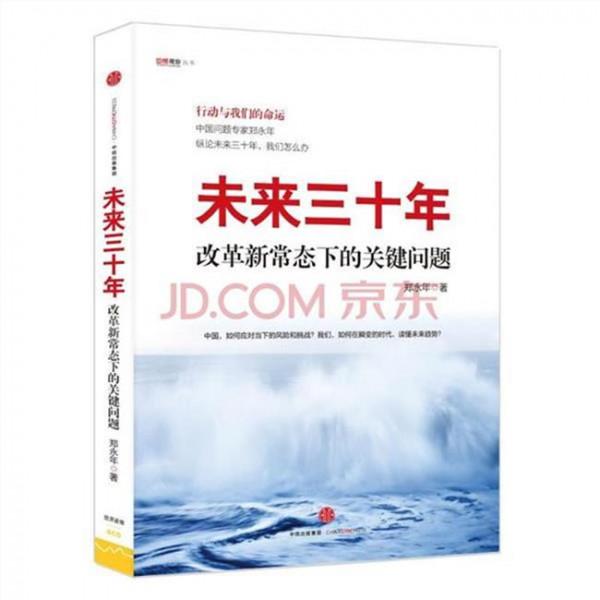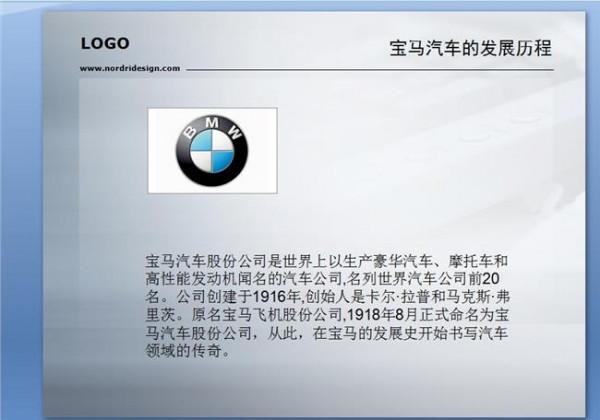北大教授汤一介谈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
在中国已经发生广泛影响的“国学热”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这两股思潮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有机结合,如果能在中国生根并得到发展,也许中国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第一次启蒙”,实现现代化,而且会较快地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帜的后现代社会。
一、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和16世纪明末中国的“启蒙思潮”
康德(1724-1804)提出“要敢于运用理性”作为“启蒙运动”的口号。因此,我们可以说“理性”开启了欧洲的“启蒙运动”,他们的思想家用“理性”扫除对天主教的迷信和世俗的愚昧,引发了在欧洲的一场资产阶级的思想革命运动。
这场运动不仅使西方的自然科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而且为西方的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奠定了基础。他们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理论促使1789年在法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于1793年发表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并颁布了宪法。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势力,有力地推动了在欧洲各国相继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说明,欧洲“启蒙运动”的结果最终落实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的建立。
当前,在中国学术界虽然常常把16世纪明末发生的反对封建专制“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抨击禁欲主义、高扬个性、“独抒性灵,不拘一格”的“唯情主义”看作是新的价值观和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并往往用“启蒙思潮”、“启蒙思想”、“启蒙文化”、“启蒙性质”等等来说明这次运动的性质。
如有的学者把明末反封建礼教称之为“启蒙思想”或“启蒙主义”;泰州学派的支系,主张“唯情主义”的大戏曲家汤显祖也被认为是“深具启蒙思想的人”。这就容易使人们错误地以为16世纪明末的反封建礼教、主张个性解放的运动有似发生在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
我认为,上述两种运动不仅在表现形式、而且在实质内容上都有不同,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以“唤起”理性为特征,而16世纪明末的反封建礼教的运动是以唤起人们的情感释放为特征。前者的结果是:自然科学重大的突破、社会科学基础的建立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国家的建立;后者的结果是:虽有少数思想家仍然坚持反对封建专制礼教,但在清军入关后封建专制礼教的强化和对批判礼教的文人学士无情的镇压,使反对封建专制的礼教浪潮被打断了。
二、19世纪中叶后,中国社会在西方“启蒙运动”冲击下的艰难前行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惨败,此后在与西方(包括东亚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使中国人认识到自己国力衰落、政府愚昧而西方国力强盛和政府开明,根源在于中国的思想落后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于是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吏在国家多次被动挨打的情况下一步步认识了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和政治体制的优越。
因而,在这一时期西方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和政治制度的书籍大量被介绍和翻译到中国。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提出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观念,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无疑有着重大影响力。
中国的有识之士,先是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是靠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于是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展了一场制造枪炮的洋务运动,但是所谓的“洋务运动”并未摆脱“中体西用”的束缚,故未能动摇清朝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
在有更多的开明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进一步了解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提出中国要富强必须改变原有的政治体制,用改良的办法推行君主立宪,并于1898年发动了戊戌变法。而这种遵循改良主义路线的变法是软弱无力的,在清政府的重重高压之下以失败而告终。
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仁人志士不得不采取用革命的路线来推翻清王朝统治。1912年,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废除了封建专制的君主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虽然取得了暂时胜利,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一方面中国仍然在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另一方面不仅出现了两次帝制的复辟,而且不断地受着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旧势力的破坏和抵制。中国的民主共和国体系实际上未曾真正建立起来。中国何去何从仍然是需要中国人民不断解决的难题。
三、中国“启蒙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是否已经实现
对五四运动,中国学术界有着种种不同看法,我不能一一介绍,但我认为不能把五四运动和前此的“新文化运动”看作是没有内在联系的两种性质不同的运动。我们也许可以说,前者是一场“反传统”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后者是一场救亡的爱国运动。
正是因为有新文化运动,才使中国人能用新的眼光和新的价值观看中国落后的现实,这无疑包含着希望中国富强的愿望;正是有了“五四”的爱国情怀,才使中国人认识到必须使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的“启蒙”落实到社会生活之中。
因此,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前后相连的过程。“启蒙”唤起了“救亡”;“救亡”深化了“启蒙”,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提出“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专制统治”把两者对立起来,用所谓“救亡”来压制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等诉求。因此,“救亡压倒启蒙”或者“只有救亡才能唤起启蒙”的提法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片面的。
现在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包括“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所争取的“启蒙”思想是否在我国现代社会已经完全实现?这个问题太大,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1985年,我在深圳举办了一次“文化问题协调会”,这次会议有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和深圳二十余位学者参加。会上,我们取得了某种共识:大家认为,邓小平同志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非常拥护。
同时,我们认为现代化的问题是否仅仅被理解为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问题?因为没有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现代化将会落空。这都涉及到我们仍然要继续“启蒙”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的社会要全面实现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我们必须把“启蒙”继续进行下去。
四、中国社会的“启蒙”将如何进行下去
中国接受西方的“启蒙”思潮已有160余年历史,但中国并没有全面地完成现代化。因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两股反“一元化”的思潮。一股是来自西方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另一股是追求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热”思潮。
西方的现代化在发展了两个多世纪后,其种种弊病日渐显露,由“科学万能”引发的“工具理性”,使自然界惨遭破坏;自由经济不受约束的发展,造成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尖锐矛盾和相互敌视,唤起了人们对金钱和权力的无止境贪欲,致使人类社会道德沦丧。
为了挽救人类社会,消除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有以消解现代性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出现。初期的“后现代主义”是“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目的在于解构现代性,反对“一元化”,企图粉碎一切权威,这无疑对人类社会是有益的。
但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并没有提出新的建设性主张,因而到上世纪末,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出将“第一次启蒙”(即17、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思潮)的成果与“后现代主义”整合起来,召唤“第二次启蒙”。
他们提出,后现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为目标。
他们认为,如果“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那么“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应是“关心他者”、“尊重差别”。目前,“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力在西方还很小,我相信它在西方和东方都将会受到重视。
“国学热”的出现,是由于“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引起的,而民族的复兴必须由民族文化的复兴来支撑,因此在对过去的盲目“反传统”的反思中考虑到如何传承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文化,并使之在新时代得到更新。有鉴于当前对自然界的无序破坏,一批中国学者提出儒学中的“天人合一”学说可以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
孔子主张既要“知天”,又要“畏天”,“知天”就是要合理利用“自然界”,“畏天”就是要对自然界尽尊重和保护的职责。
中国儒家“天人合一”的学说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出的“‘人和自然’是一生命共同体”的理论很相近。有鉴于孔子和孔子思想在百多年来受到的歪曲和诋毁,有见识的中国学者认为,要复兴中国文化传统,就必须恢复孔子和孔子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人为地割断自身民族文化的民族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我们都知道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学”——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这种爱人的品德由何而来?《中庸》引孔子的话就是:“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仁爱的品德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基础。但孔子认为,“仁爱”不能只停留在爱自己的亲人上,必须“推己及人”,要由“亲亲”扩大到“仁民”;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儒家的“仁爱”精神不正与“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倡“第二次启蒙”的“关心他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吗?这很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在“前现代”的思想宝库中确实包含着若干人类社会“普遍价值”的思想资源,并对克服“现代性”可能发生的弊病起消解作用。
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一些学者和西方“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之间不仅有所接触,而且已经开启了良好的合作。“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已经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已从中吸取营养;同样,中国学者也已经注意到“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人类社会走出困境的现实意义,并关注着该学说的新进展。
在中国已经发生广泛影响的“国学热”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这两股思潮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有机结合,如果能在中国生根并得到发展,也许中国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第一次启蒙”,实现现代化,而且会较快地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帜的后现代社会。
这就是说,如果真能如此,中国的“启蒙”所得的成果,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将是最为丰厚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编撰中心主任;本文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