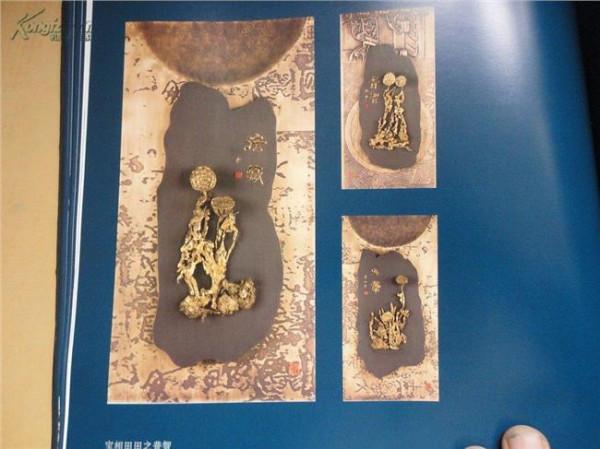姚仁喜广艺厅 视建筑为艺术品—姚仁喜的建筑设计观
记者:乌镇大剧院中,两个椭圆形的剧场空间彼此相交及“并蒂莲”效果,这种设想是受到了什么启发?
姚仁喜:首先说一下项目所在的乌镇大剧院的一些背景情况。因为乌镇的旅游发展已经很成功,目前他们正在着手办一个定期的乌镇国际戏剧节。这种戏剧节在亚洲目前还是比较少的,在欧洲有两个知名的戏剧节:法国的阿维尼翁戏剧节和英国的爱丁堡戏剧节。
乌镇要办一个戏剧节,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大剧场,还包括很多不同规模大小的室内和户外的剧场。我们所做的乌镇大剧院就是乌镇戏剧节所规划的七个剧场中最大的一个。乌镇的另外六个剧场包括一个户外的水剧场,这是一个对原有剧场的改造,以便其更适合演出的需求,另外两个是如同“黑盒子”的双胞胎剧场,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老剧场建筑,位于乌镇的街道上,我们把它调整改造成了一个有阶梯座位,而且更具备表演功能的剧场,还有一个是省家厅。
乌镇大剧院的业主最初提出了两个功能要求,一个是项目是要能容纳一千多人的传统式的剧场,另外一个剧场的多功能性,他们提出项目是要比一般的黑盒子还要大的空间,大概可以容纳500至600多人的一个空间,可以做实验剧场,也可以用作电影节期间电影放映的需求,甚至是可以用作宴会等功能。
剧场的设计有其自身的特点,比如说舞台的上方会考虑布景所需要的固定高度和设备以及舞台的设置等。
乌镇具有浓郁的历史气息,其整个环境非常优美,不过乌镇的建筑大部分都是两三层楼的民居建筑。要在这种环境中放入如此大的一个量体,同时还要确保这个新的量体不能影响到原有的环境,对我们来说,这是这个项目最大的挑战。
所以为了保证同时实现这两个剧院功能,我们就要尽量减少它的体量,最后我们把两个剧院背对背相扣,这样整体的体量自然会减少。同时,这种相扣也带来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两个剧院可以连通使用。所以本来是两个单独的剧场,最后变成了一个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连通使用的灵活的剧场,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体量变小了,功能反而增加了。
“并蒂莲”的效果是我们引用的一种方式,是剧场的整个体量形态和故事两个方面的联系。现代剧场必须具有一定规模的体量和高度,我们除了采用两个不同高度的剧场背对背,还有没有其他方式让整个剧场的体量不会有点惊人,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片状来实现,我们把建筑的体量切割变成碎花,如同花瓣一样。
在设计中,我们将这些碎花做了一些数学上的模式处理,以此来降低剧场对外界的冲击。第二点就是,乌镇是一个水乡,同时江南园林有很多莲花、荷花,“并蒂莲”的效果也就成了文化上一个吉祥的象征。
所以,这就变成一个故事。项目基地处在距离乌镇主要的街道和水道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所以从远处看,整个剧场在视觉上是处在水中的,这种形式也与莲花有一定的联
系。所以我们用“并蒂莲”的概念来阐释了双剧场背对背相扣的这种设计。记者:扎哈设计的望京SOHO其流线的外形褒贬不一,有人提出,这种建筑并没有契合到其周边的背景环境,它可以建在任何一个城市。乌镇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其浓厚的传统文化特征和场地的自然环境是如何在设计中得以体现的?
姚仁喜:首先我想先说一下建筑物与周遭环境的协调性。我不认同所有的建筑都要与周围的环境相协调,因为每一个建筑物与其所在的地点有其特殊性,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相互协调,有时候有些建筑是要扮演其在城市或者非城市空间里所要扮演的公共性或特殊性的角色。
我想这个在历史上是有很多例子的。也许现在很多建筑想要标新立异,所以有人开始觉得这种独特性不能接受。可是,如果说建筑一定要配合周遭环境的观点是一个不可打破的道德上的观点,我是不赞同的。
关于乌镇大剧院项目,因为乌镇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环境,我们着手设计的时候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乌镇魅力的环境中,做一个有加分效果的东西而不是去破坏原有的东西。项目本身的规划是一个较大的体量,但现有的体量是一些江南特色的两三层楼的民居式建筑,而这两种建筑自身的特质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点上我觉得有一个情况可以参考。比如说欧洲的意大利,很多中世纪特征的小镇都很有特色,那里的建筑规模都
姚仁喜是大元建筑及设计事务所的创办者及主持建筑师,事务所于1985年在台北成立,并与2001年在上海成立会元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其独特和创造性的设计天赋让他成了一位颇受推崇的建筑师,其带领的事务所曾被伦敦发行的World Architecture杂志称为“台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执业表现”,其本人也成为了建筑界创新的要角。
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设计的感悟及沉淀,获得了客户及媒体的各种赞美之词,对佛学的学习机研究对其生活与建筑设计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各种的赞美之词,他却非常欣慰又诙谐地回复:我只是在湖里丢了一个石头而已,而我丢石头的初衷只是出于个人爱好。
姚仁喜
大元建筑及设计事务所创始人•建筑师
很小,整个小镇是由弯弯曲曲的街道组合而成的。
在某个层次上,空间的尺度与乌镇是类似的。不过在欧洲这样的小镇,总有一些地方,或者是城镇的中心,或者其他地方会出现一个很大的教堂,教堂前门就会有一个广场,这些教堂几乎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可是在那个城市当中,人们不会觉得那个教堂建筑是突兀的,不会觉得它不属于那个地方。
其实这里是有很多原因的,一方面是他们使用了统一的材料。其次重要的并不是尺度,而是建筑的质感、颜色跟材料是否是一致的。因为某些公共建筑它必须有一定的尺度和体量,在乌镇大剧院中,我们所用的材料,首先在颜色上是与乌镇现有的建筑是一致的,其次在剧院透明的一侧,我们所用的材料是取自于乌镇的一些很旧的木材,这些木材是从乌镇以前的旧房子拆迁或者船上拆卸首级得来的,我们只是对木材做了重新处理。
在剧院另外坚实的一侧我们运用了当地的京砖,这是一种以前用作城墙的砖。虽然这些京砖是新烧的,但他与乌镇原有房子的青灰色的砖是一样的,质感、颜色几乎都保持了一致性。所以整个建筑在视觉上、质感上以及材料的本质上是与现有的建筑保持了一致性。我相信这个项目建成后不会很突兀。
记者:观众厅的形态和细节设计有哪些特点?有没有运用一些先进的建筑技术?姚仁喜:刚刚我们提到了两个剧场相扣
的形态,即两个椭圆形的形状相靠,大厅设置在外面,剧场在里面。大厅设置在比较通透的一侧,外墙我们运用了冰裂纹的木材。在这一侧是一个可以容纳一千多人的大剧场,几乎是透明的,观众可以从大厅看到整个乌镇的景色,我们将这个厅称为蓝厅,内部主要采用了江南一带的蓝染的布的颜色来装饰,蓝色覆盖了整个音乐厅里的墙壁和座位,同时以金色为辅做了装点。
另外是一个长方形的多功能厅,大厅部分就是倾斜的厚重砖墙,光线引入较少,这个厅是采用了暗红色装饰,所用的主题也是蓝染上面的花纹,以镂空的形式最后成了光线的一种表现形式。
所有的图案与故事的来源都与当地文化有关联,最终的设计带来了一个现代化的室内环境。项目并没有运用一些特别先进的技术,不过由于剧场较大的宽度和几何形特点,我们将钢筋混凝土和钢构结合。
我们觉得目前虽然有很多新的技术,有时候反而是一些旧的东西比较难做。比如说我们要在外墙用旧木头做一个非常精准的冰裂的格栅,其实这是最难的。
因为其几何形比较复杂,同时我们用的是地地道道的旧木头,而非工业产品。砌那些京砖也很有难度,因为墙面是弧形的,而且是放射性的,同时我们将每一批京转在某一处有一定程度的转角和垂直,从而凸显出来,这些凸显出来的点状的砖整体看起来是一个放射性的交织的网。这都是非常挑战功法的。所以说我们并没有运用新的技术,可是我们是在把建筑当成一个工艺品在做。尤其
是在现代化的都市,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等都没有手工感,比较冰冷,而这个剧院就体现了非常强烈的手工感。
记者:最初的设计方案在施工时修改多吗?姚仁喜:我们最初为业主提了两个方案,他们选择了其中一个之后,很快就动工了,项目整个周期是非常快的。即便这个项目的几何形非常复杂,因为业主非常信任我们,所以他们几乎没有改动要求,反而是我们自己,综合考虑到项目的复杂性很高,比如说外面的墙和柱子几乎没有地方是平直的,我们就花很多精力把所有的细节、几何形、三维等所有的关系在细节上做了很多优化和调整。
工地后来开工后,我们很高兴,因为项目做得还是很好的,比如说在角度上没有出现问题。后来业主请我们做了室内的设计。
记者:文化建筑的设计及其定位对所在的城市有极大影响。您如何理解乌镇剧院对乌镇带来的影响?
姚仁喜:所有的文化建筑在任何一个聚落或城市都是一个高潮,是一个公共性建筑。到目前为止,乌镇有一种重复与单调性。虽然有个别有特色的庭院或者小型的图书馆项目,不过并不多。这个剧院完成之后,乌镇就会彰显出一定的主题。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欧洲的教堂,它会赋予整个城市一种多样性,公共性与非公共性空间之间的对比就会更强烈。我认为,乌镇剧院会丰富整个城镇的复杂性和趣味性。
记者:从最初开始选择做设计到现在,您个人所坚持的设计理念和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
姚仁喜:设计理念是在变化的,可能像其他人所说的,我做建筑很认真、不妥协。不过有一件事是没有太大变化,就是我对建筑的热情。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会做之前做的事,设计、选材料等。
记者:外界将您评为台湾现代建筑领航者、“带领台湾建筑界创新的要角”,您如何看待?
姚仁喜:他人的看法我只会以一种平常的心态看待。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幸运的,这么多年来可能做了一些先锋的设计。
可能我们为台湾同业或者是年轻一辈提供了一些经验。我们喜欢做建筑,而且比较敢于尝试。我们提供了很多种建筑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为建筑师建立了一种职业上的态度及标准,之前台湾建筑师的较色和职业标准不是非常确定的,大家都还在摸索,我们从一些先进的地方学习,坚持把建筑师这个职业做到一个水准。
总的来说,建筑师这个行业全球是一样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行业,就是古语中提到的“有巢氏”,这个古老的行业不会消失。用坚守古老的原则去做应该会做得很好,这是我所坚持的。
记者:曾以台北为中心发展出来的一波新建筑美学运动对您个人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
姚仁喜:新的机会出现就会带来很多可能性。正如我刚刚所说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愿意接受挑战,做了很多新的尝试,所以很多人会有回应。我之前做过一个都市里的佛寺。当时很多寺庙都是很传统的寺庙的样子,业主想做一个新的寺庙,我当时尝试做了一个完全跟传统寺庙不一样的建筑。
这个建筑出现后,很多人理解到,佛教的建筑不应该都是很古老的,反而可以是新颖的。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我只是在做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先锋。可以这么说,我只是在湖里丢了一个石头而已,而我丢石头的初衷只是出于个人爱好。
记者:社会环境对建筑设计会有比较重要的影响,您认为目前台湾建筑设计环境怎样?姚仁喜:站在一个批判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要考虑的。第一个是过分的商业化,很多建筑,尤其是住宅设计,因为出于销售的目的,开发商就会标榜奢华等特征。
不幸的是,住宅建筑在一个城市当中占到很大的比重,这种趋势会让建筑很虚浮、很表面,它跟城市未必会发生一个很积极的联系。第二点是一种胆怯心理。因为创作是要某种胆量去寻找火花的,可能是社会上的各种限制太多,挑战太少。
第三就是束缚性太大。建筑的限制越来越多,很多制度建立的初衷是好的,比如说对于环境或者节能的要求,可是当他变成一个机构化的条文后,反而会变成某种束缚。无论建筑的规模大小,都是受到这种捆绑式的限制,所以很多年轻建筑师的创意因此会被扼杀。
记者:对佛教的学习与所获得认识对您的生活和设计有哪些影响?
姚仁喜:比较准确的来说应该是对佛学或者佛教的哲学的学习。我是大概15年前开始接触佛学的,宗教不是我所感兴趣的,其哲学是非常深奥的,这不是一种信仰。从佛教的哲学角度来说,我们是要追求一种自由的状态。因为我们目前受到各种束缚,并不自由,如果这种束缚带入我们的创作,便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限制,其实我们最大的束缚是被自己束缚,所以创作上我们常常很在乎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别人是否会认可,是否体现了自己的概念。
这些反而让创作的自由不能发挥。
我喜欢用老子讲的一些话,其中一句是我的座右铭:“为学日益”,学的东西每天是要越来越多的,“为道日损”,如果把它看做一个道来看的话,每天是越来越减少的,“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也”,当你可以到无为的状态的时候就是无所不为,我觉得这跟创作很密切的。
如果我们能够处在一种无为的状态下,设计的自由或者能量会源源不绝。所以要打破观念习惯或者自以为是的一些东西,这在设计的创作过程也是相同的。
记者:您为什么会选择做建筑师?
姚仁喜:在我成长的年代台湾没什么新的建筑出现,当时经济发展很缓慢。在高中,我对艺术和美术很感兴趣,对科学物理反而没什么兴趣。后来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我觉得只有建筑系好像比较接近我的兴趣,所以第一志愿就填报了东海大学建筑系,也被录取了。
当时还引起了一阵轰动,大家觉得很诧异,因为我的分数很高,完全可以去台大。但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后来也发现建筑就是我很喜欢的东西,直到今天我还很庆幸自己选择了自己想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