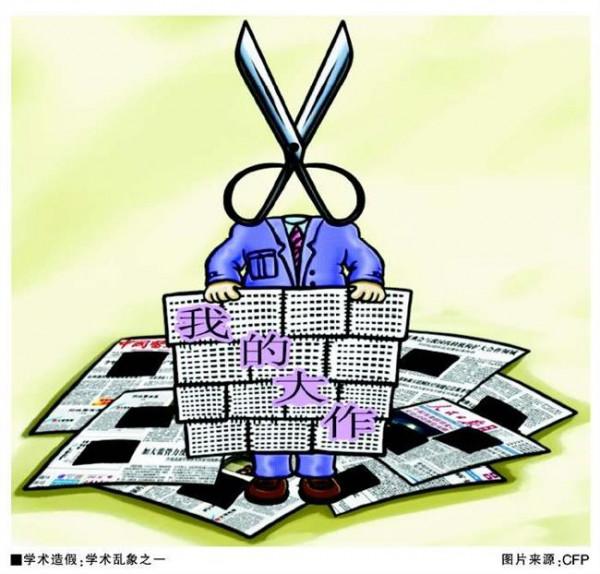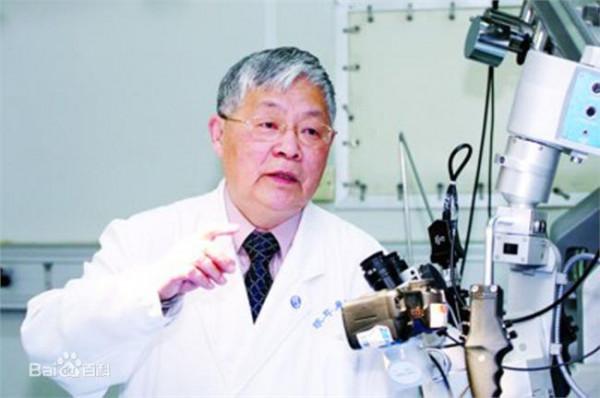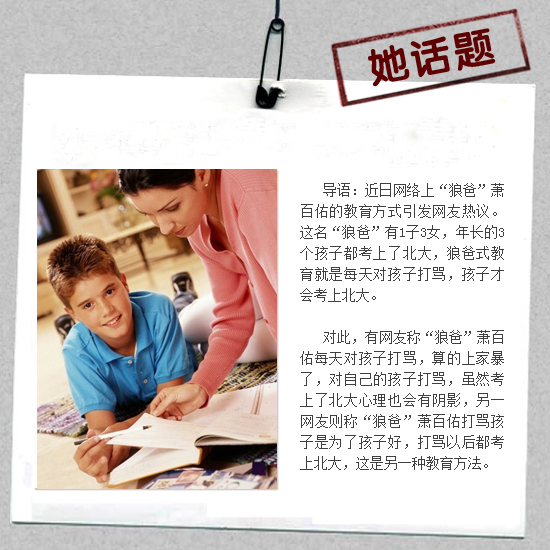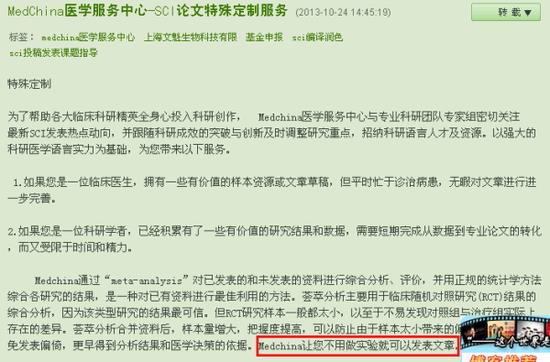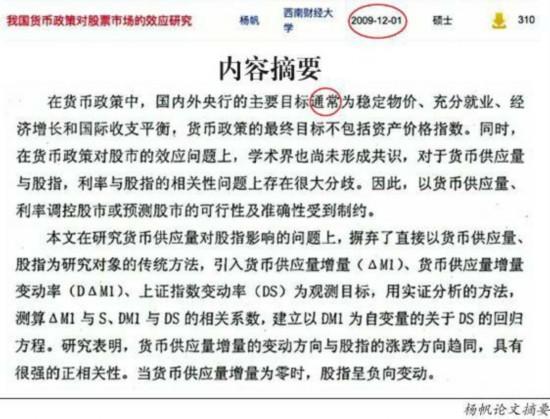马叙伦儿女 马叙伦的儿子 张耀杰:中国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从马叙伦到汪晖
2010年8月14日下午,燕山大讲堂第77期活动在银科大厦1601会议室举行。
此次活动主题为:“中国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从马叙伦到汪晖”。学者张耀杰纵览历史,对从马叙伦以来,到鲁迅、唐弢以降的几宗抄袭公案进行了点评。
以下为讲堂实录:
燕山讲堂77期实录:中国学术史上抄袭争议
精彩观点:
之一:我的眼界所及,无论是作为汪晖的研究对象的鲁迅先生,还是指导汪晖写作《反抗绝望》的博士导师唐弢,在抄袭与剽窃问题上,都曾经留下过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得到澄清的类似瘕疵。
之二:傅斯年揭发马叙伦抄袭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后,马叙伦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但自此只要有机会他就说傅斯年、胡适等人的坏话、攻击他们。1949年3月马叙伦作诗“万岁高呼毛泽东”。建国后获任命教育部部长。
之三:鲁迅和周作人都承认自己早期的文章是“半做半偷”的学习模仿之作。但鲁迅却从未承认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部分。
之四:第一代的鲁迅研究专家、汪晖的博士导师唐弢曾抄袭剽窃并歪曲改写阮无名《文字之狱的黑影》一文用以批评胡适,又因私人恩怨以文字诬陷范纪曼,使范纪曼一再地被严刑拷打,获刑20年。
之五:伴随着“汪晖抄袭事件”出现了“倒汪派”与“挺汪派”。争议中最令人信服的是谢泳,他引用清代经学家陈澧《东塾续集》一语,指出:“前人之书当明引,不当暗袭...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见闻之渊博”。
之六:教授拿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国库的钱,你的学问行不行,好不好,有抄袭还是没有抄袭,大众媒体有责任参与监督。公共人物有错误,得承认错误。永远不承认错误,公众就永远有权利追究你。
主题:中国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 ——从马叙伦到汪晖
主讲嘉宾:张耀杰(历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史专家)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10年8月14日(周六) 下午15点-17点
地点:银科大厦1601室
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来到77期燕山大讲堂现场。今天我们请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苏州德源文化研究所的学术主持人张耀杰老师讲“中国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有请张老师。
张耀杰:2010年3月10日出版的《文艺研究》和3月2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先后刊载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指出《反抗绝望》一书存在抄袭剽窃现象。钱理群、孙郁、赵京华等多名鲁迅研究专家,认为该书只是存在引文不够规范等“技术层面的问题”,恶意剽窃难以成立。
这个话题前一段时间很热。整个过程我没有参加,但参加的几乎都是我的好朋友。这个事件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学术界的人应该有一个总结和说法。子云要我找一个题说一说,我就想到了这样一个题。
先说说我的个人背景。以前我是鲁迅派的人,拥护鲁迅的人,现在我属于胡适派的人,胡适的人批评别人时,总是要给别人留一个机会让别人批评自己,鲁迅派的人从来不允许别人批评自己。我的眼界所及,无论是作为汪晖的研究对象的鲁迅先生,还是指导汪晖写作《反抗绝望》的博士导师唐弢,在抄袭与剽窃问题上,都曾经留下过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得到澄清的类似瘕疵。
限于中国现代教育史和现代学术史来说,最早的抄袭争议,还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北京大学教授马叙伦和北大学生傅斯年。
傅斯年揭发马叙伦的“炎炎之词”
1919年1月傅斯年、罗家伦等十几个北京大学的学生创了一个很有名的杂志——《新潮》,创刊的钱是北京大学出的,蔡元培批的,支持的人主要是胡适、陈独秀这些《新青年》的人。
傅斯年是马叙伦的学生,原来是研究国学的人。马叙伦、刘师培提倡国学,把傅斯年当成最有希望的弟子来培养。没想到傅斯年在《新潮》第一其就发表一篇文章:《出版界评:马叙伦著〈庄子札记〉》,把马叙伦给揪出来了,说马先生的札记如果是自己学习用,说明马先生勤奋,学问做得扎实。但札记出版了,不仅告诉学生来购买,序言中还用“炎炎之词”夸奖自己的札记。然而这札记“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
傅斯年举了札记几页的内容都是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讲过的东西,但没有说是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来的,“似为贤者所不取也”,一个好的学者是不会这样做的。
傅斯年所谓的“炎炎之词”指得是马叙伦在学术著作《庄子札记》中抄袭胡适的学术成果却不注明出。马叙伦“序”里有这样一段话:“仆既略涉‘六书’,粗探内典,籀讽本书,遂若奥衍之辞,随目而疏,隐约之义,跃然自会。”
这句话大意是:我这个奴仆(谦称)既然涉及到古代的六书,粗浅地研究了内典,阅读《庄子》的过程中,做了一些笔记,《庄子》这本书本隐约的含义,就跃然纸上。马叙伦谦称“仆”却是自我表扬,觉得自己的《庄子札记》把庄子隐约的意思都表现出来了。
还要注意的是马叙伦自称为“仆”,“仆”就是奴仆。当时已经是民国了,民国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个大学教授,在当时代表先进文化的读书人,自称“仆”而不是“公民”,不是以人人平等的“公民”自称。可见马叙伦在民国时完全没有公民意识。
1月11日,章太炎的弟子、马叙伦的浙江同乡、另一位北大教授钱玄同,也是新青年的同仁,看到《新潮》杂志后在日记上写道:“大学生所办之《新潮杂志》第一册已出版,中以傅孟真(傅斯年)、罗志希(罗家伦)两君之文为最有精神。傅评马夷初(马叙伦)之《庄子札记》,罗评林琴南之译小说,都说的很对。”肯定傅斯年对马叙伦的批评。
到了第二天,1月12日,《钱玄同日记》中另有“访豫才(鲁迅)兄弟,半农亦在”的记录。当时钱玄同和刘半农两个人编《新青年》杂志,一趟又一趟地动员在绍兴会馆住鲁迅写小说,所以钱玄同自己就写了“访豫才兄弟”。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也写道:“半农来,旋去。晚玄同来谈,十一时去。”
钱玄同是非常喜欢聊天的一个人,刘半农来,一会儿就走了,钱玄同来了一直到晚上11点才走。钱玄同在这儿谈话时,就谈到了《新潮》杂志。
第二天,周作人日记里就出现了一个记录,“购《新潮》一本。”就是说,钱玄同访问鲁迅和周作人时就肯定谈到了《新潮》并说了什么好话,周作人就去买了一本。
过了三天,1月16日,鲁迅日记里留下了给许寿裳寄《新潮》杂志,并且替周作人给张梓生寄《新潮》杂志的记录。这说明他们兄弟俩喜欢《新潮》杂志,如果不喜欢的话,不会又买了几本给他的朋友寄。而且鲁迅在当天写给许寿裳的书信中,表扬《新潮》杂志说:“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由此可知,当年的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都认可马叙伦的抄袭。
当年傅斯年和罗家伦虽然是学生,但是与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都是在《新青年》发表文章的同人,也就是是志同道合的人,以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兴趣参与这个的杂志的人。
傅斯年揭发完马叙伦,马叙伦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抄袭。但他们已结下仇怨。自此,马叙伦一直和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这些人敌对,只要有机会就会说他们坏话、攻击他们。1947年,马叙伦的回忆录《我在60年以前》里造了很多谣言、谎话。一方面说自己多么好,什么好事都是他干的,陈独秀到北大、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都是他出的主意。但一说到胡适、傅斯年就是他们怎么破坏北大、干了多少坏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叙伦以他所惯用的“炎炎之词”对毛泽东歌颂赞美。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等人从西柏坡飞抵北平,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马叙伦与在北平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一起,前往西苑机场表示欢迎。这是毛泽东与马叙伦的初次见面。在陪同毛泽东一起阅兵之后,马叙伦当场写下四首七绝,其中一首这样写道:“万岁高呼毛泽东,与人衣食即春风。江南百姓皆昂首,何为迟余解困穷。”
意思是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要喊毛泽东万岁的,为什么喊万岁?因为毛泽东是“与人衣食”的人,人吃的饭,穿的衣服都是毛泽东给的。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在翘首以盼等毛泽东去解放的,毛泽东为何这么迟还没有去解放呢? 关于“毛泽东万岁”这个事,现在有很多争论,有人说是马叙伦第一个喊毛泽东万岁的人,但有人说是周恩来,也有人说刘少奇。
我想在民主党派中第一个喊“毛泽东万岁”恐怕就是马叙伦了。毛泽东刚进北京,马叙伦在机场就写诗,高呼毛泽东万岁。
这里所说的“与人衣食”,江南的老百姓肯定不是等着毛泽东“与人衣食”的。江南老百姓大部分都是该做工就做工,该种地的就种地,种地的人自己可以打粮食,做工的人自己可以用工资去买粮食,用不着等毛泽东“与人衣食”。等毛泽东“与人衣食”的人,恐怕只有那些不做工,不种地的读书人,像马叙伦。
效果很快就出来了,1949年10月1日,马叙伦参加开国大典,之后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以及高等教育部部长。“与人衣食”在当年北大,鲁迅和马叙伦这些浙江人动不动就说是“饭碗”。马叙伦从毛泽东这里得了一个最大号的“饭碗”——教育部部长,接着是高教部部长。
如果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的人,北大、清华当年那么多优秀的教授,比马叙伦的学问、人品要好的人有很多,但就是因为他第一个叫“万岁高呼毛泽东”,所以当上了教育部长和高教部部长。
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有一个讲话:文化和教育要退到1949年以前。但胡耀邦很快就下台了。现在的教育和文化如果要找出路的话,就是退到1949年以前。特别是这些年来,我们离1949年以前那个环境、制度越来越远。
鲁迅与周作人的“半做半偷”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承认自己刚开始模仿人家写小说时,写了一篇《孤儿记》,是从法国作家雨果那里“半做半偷”的抄袭之作:“为什么说‘偷’呢,因为抄了别人的著作,却不说明是译。那么非偷而何?” 所谓“偷”在文化上就是抄袭、剽窃,这是周作人承认的。
鲁迅在《集外集》的“序言”中也承认过自己“半做半偷”。他在日本留时写了一篇关于居里夫人发明的放射性元素“雷”的文章(他翻译成“雷锭”)、还有一篇关于斯巴达尚武精神的小说,都是抄人家的:
“我现在想想,我当时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陈漱渝在《〈斯巴达之魂〉与梁启超》中考证《斯巴达之魂》的“老家”是梁启超1902年6月15日和7月1日在《新民丛报》12、13号上连续发表的《斯巴达小志》。)
我觉得鲁迅这个态度是诚实的。那篇文章发表在荷兰的留学生杂志上(刘诗培办的刊物),他当时还说过,这个刊物最大的好处是写得越长给的稿费越多。所以这个文章很长,就是为了赚稿费。
鲁迅和周作人当年没有名气,所以也没有人去关注、指责他们“半做半偷”的文章。鲁迅和周作人在晚年有一个表态,这个表态也算是承认了,态度还是不错。比较严重的是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抄袭。
中国有一个习惯,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鲁迅和周作人当年的抄,可以原谅,所有的人刚开始学习写文章都有模仿和学习的过程。现在大学生、中学生写作文,都会抄别人一段话、一个意思,这些东西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抄袭。因为没有拿去发表,没有拿去换稿费。
如果拿出去发表了,写上自己的名字了,就应注明从哪里借鉴人家的东西,如果不说明的话,就是抄了。傅斯年批评马叙伦也是这个意思:马老先生的《庄子札记》抄人家的记录,放在家里,自己用、自己参考,就说明马老先生做学问很认真。如果拿出来发表,输上自己的名字,还说“炎炎之词”,就是很严重的抄袭行为。
鲁迅与凌叔华抄袭剽窃之争
1925年10月1日,接编《晨报副刊》的徐志摩要改版,用了凌叔华临摹的西洋女人敞胸半裸的黑白画像作报头。8天以后,10月8日,《晨报副刊》前任主编、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时的老学生孙伏园在他主编的《京报副刊》上刊登女作家陈学昭(化名“重余”)的文章:《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指出这个画是英国画家琵亚词侣的作品。
徐志摩看后给孙伏园写信,说不是凌叔华抄袭,只是凌淑华临摹后我看了觉得好就拿去用了,没有提画作来源是我徐志摩的责任,不是凌叔华的责任。
这个事本来结束了,但到11月7日,凌叔华在《现代评论》周刊发表《花之寺》小说。11月14日,《京报副刊》发表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