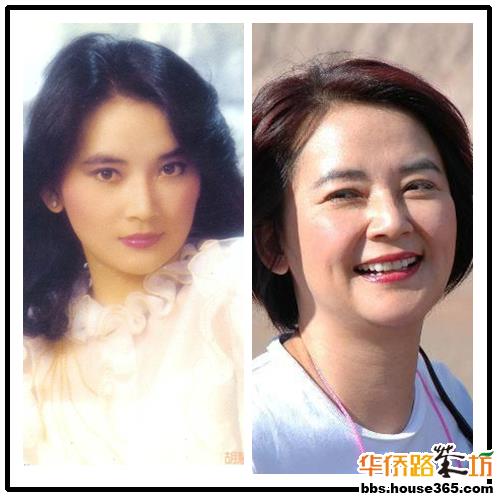雷平阳杀狗的过程 沈浩波:雷平阳《杀狗的过程》
这应该是杀狗的 惟一方式。今天早上10点25分 在金鼎山农贸市场3单元 靠南的最后一个铺面前的空地上 一狗依偎在主人的脚边,它抬着头 望着繁忙的交易区,偶尔,伸出 长长的舌头,舔一下主人的裤管 主人也用手抚摸着它的头 仿佛在为远行的孩子理顺衣领 可是,这温暖的场景并没有持续多久 主人将它的头揽进怀里 一张长长的刀叶就送进了 它的脖子。
它叫着,脖子上 像系上了一条红领巾,迅速地 窜到了店铺旁的柴堆里…… 主人向它招了招手,它又爬了回来 继续依偎在主人的脚边,身体 有些抖。
主人又摸了摸它的头 仿佛为受伤的孩子,清洗疤痕 但是,这也是一瞬而逝的温情 主人的刀,再一次戳进了它的脖子 力道和位置,与前次毫无区别 它叫着,脖子上像插上了 一杆红颜色的小旗子,力不从心地 窜到了店铺旁的柴堆里 主人向他招了招手,它又爬了回来 ——如此重复了5次,它才死在 爬向主人的路上。
它的血迹 让它体味到了消亡的魔力 11点20分,主人开始叫卖 因为等待,许多围观的人 还在谈论着它一次比一次减少 的抖,和它那痉挛的脊背 说它像一个回家奔丧的游子
最近几年,雷平阳连续出版的两部诗集,一部叫《云南记》,另一部叫《出云南记》。他几乎写遍了云南的大河、山川、村寨、丛林、老虎、麂子、巫师、老妇、幽灵、鬼魂。他是在乎诗歌功能性的诗人,像创作木版画一样写诗,用雕刻镂凿的手艺,记录云南的一切。尤其是那些存在于隐秘中的,正在消逝的部分。
他有版画家的耐心,说书人般对故事的敏感,还有一种为正在消失的世界作史立传的野心。他为丛林和树木作传,为乌蒙山和哀牢山作传,为红河和怒江作传。但无论是作传还是写史,最动人的,永远是其中的"人"。
在《电线杆下的约翰》一诗中,他写一位长眠于地下的传教士约翰,盗墓贼挖开他的坟墓,从一堆白骨的手中,抢走刻写着《圣经》的象牙;在《在勐昂镇,访佛爷》一诗中,他写一个老和尚,六十年前遁入空门,四十年前为赡养父母还俗,十年前因妻离子散,撑着一把雨伞,再次遁入空门,他写这位正慢慢变枯的老僧,枕边堆着的那些经卷,有汗味,烟尘,也弥漫着一个老人羞于启齿的孤独;《在蛮耗镇》一诗中,她写一位老妇,年轻时,与从这里骑马北上的红军团长短暂的相爱,守着团长送的一支驳壳枪,度过了60年的时光;在《哀牢山的雨季》中,他写西南联大的一位教授,被山上的土匪用五斤鸦片请上山,为自己的母亲写碑文,他写的碑记,至今仍然深藏在哀牢山的荒草丛中,有着"我们久已生疏的华美、哀叹和感恩。
"
雷平阳的云南,不是云南的城市,而是与现代文明反向的,埋藏在山野中的蛮荒,是仅存的蛮荒,正在被文明取代的蛮荒。因此雷平阳的诗歌,也像是在做碑,在碑上记录这荒野中历史的残片。但这并不是说,雷平阳是一位反现代文明的诗人,事实上,在雷平阳的诗中,并没有太多的所谓原始与现代,自然与工业的二元对立。
他只是试图与这些即将消失的事物对话,甚至融入其中,感受和挽留那种处于时空夹缝中的荒凉。他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自然诗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个"人文诗人"。
我尤其喜欢他那些诗中有人,人有故事的诗歌。在这些诗中,他用故事为人写史,用人为这残留的莽荒中的文明立传。只要有人,则无论是在纽约、伦敦、上海、东京,还是在勐腊、哀牢山、澜沧江、基诺山,就都有同样的灵魂。诗人在为灵魂作传,为承载这些灵魂的土地记录残史。在人的飘荡的灵魂面前:哪里的世界不是世界?何处的人生不是人生?什么是蛮荒?什么又是现代?一列火车和一只奔跑的麂子,到底又有什么天大的区别?
不同的环境,赋予了这些灵魂不同的故事。雷平阳在诗歌中祭奠这些死去或者仍然活着的鬼魂,其背景是万物有灵的原始。对于诗歌而言,也就被涂抹上了一层神秘的油彩,这也构成了雷平阳诗歌的魅力。在《吝啬鬼》一诗中,他写一位姓徐的老鳏夫: 一生担心有人会与他争食 所以,他没有妻子 他在劳作时生病,回到家 死在米柜里,两只手,紧紧的 攥着两把米 …… 送他上山的那天,又是邻居 从他的米柜里,拿出了几升米 想做几席饭,招待为他送葬的乡亲 吊诡的是,从黎明到太阳当顶 锅底的柴火很旺,甑子里的米 却仍是生米。
一个道士 路过村庄,听说这事,诡异地一笑 一边口念咒语,一边抽出木剑 在生米上,深深地划了一个十字 很显然,他罩住大米的魂魄被划碎了 生米很快就做成了熟饭 但人们都看见,道士挥剑的时候 他的灵柩里,流出了一滩血水
这首诗中,除了鬼魂护米,道士挥剑的"荒诞不经"带来的异质感,也体现了雷平阳在诗歌中讲故事,在诗歌中扮演说书人的偏好,和实现这种偏好时所体现出的叙述的耐心。雷平阳的叙述,不往聪明取巧里写,不往轻薄潦草里写,一笔一划的刻凿,像铁匠打铁,石匠刻碑。这种写法,有一种粗拙的、野生的文体感,像村寨中原住民喝酒的粗瓷碗,配合着莽荒深处的云南背景,相得益彰,形成了鲜明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