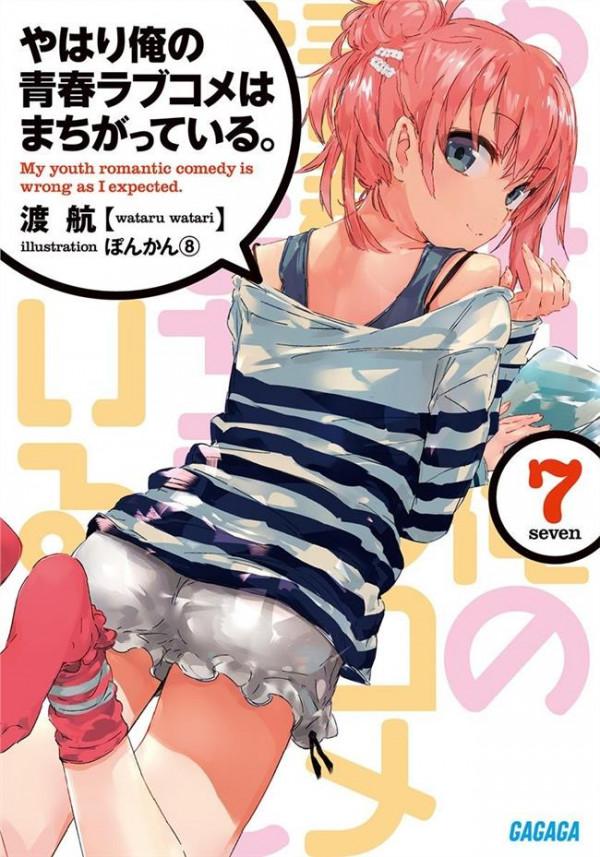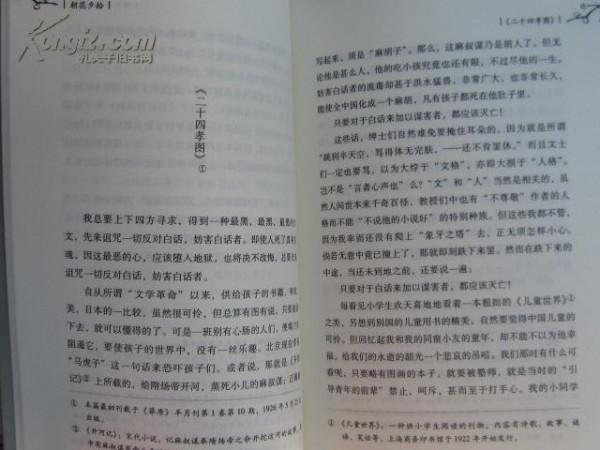鲁迅文学奖李佩甫 从中篇小说《界》谈我的文学我的梦 —听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次仁罗布讲述
4月23日,是第22个世界读书日,孟德斯鸠说:“喜爱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无聊的时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
一本好书往往能改变人的一生,一个人的精神成长,与他的阅读息息相关;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全民族的阅读水平。本期《文化雪域》将以阅读一本好书展开。
4月15日,西藏图书馆2017年首期“西图讲坛”以“我的文学·我的梦”为主题展开,当天特别邀请了我区著名作家次仁罗布讲述中篇小说《界》的创作历程。
“有时,你经过某个地方,某个景,会给你触景生情的灵感,它会变成小说的素材;有时,一次交流,一场经历,也会成为你故事的来源。你的经历与故事,会构制成另外一个版本的小说。于是,最初的小说素材便产生了。”讲座开场,次仁罗布如是说。
历史与经历,是小说产生的最初来源
2005年盛夏的一天,次仁罗布来到拉萨堆龙德庆区柳梧桑达村桑普寺,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底蕴深深地吸引了他。在桑普寺河沟里有座白塔,一位当地的老先生向他讲述了白塔背后流传的故事:一个在桑普寺学经的小僧人,由于把精力都投入到佛学知识的学习上,很多年都没有回家去看望母亲。母亲也常托人给小僧带口信,让他回来看看年迈的母亲。小僧人没能实现母亲的愿望,于是含怨的母亲投毒将其害死。
他说:“这个故事,以及桑普寺的其他传说、悠久的历史,使我感到了其文化底蕴的丰厚。这个故事在我头脑里扎根,并有了故事的雏形。但是,母亲弑儿只是一条单一的传说故事,并不能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说。”
于是,次仁罗布把自己阅读的很多相关历史书籍,听到的一些故事,自己积累的人生阅历等交融、捏合在一起,让小说逐渐丰满了起来。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定在了19世纪上半叶的旧西藏,那段纷乱的历史作为时代背景,呈现在这种历史的动荡中,底层人民艰难的生活状态。
“通过构建一个旧西藏的庄园,将农奴主与农奴、僧人与俗人、底层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描写下来,表现当时的一个社会现状。这个庄园从鼎盛到衰落的过程,呈现旧制度的僵化与腐朽。同时,通过庄园的衰败寓意了旧西藏地方政府的墨守成规和走向衰败的一个必然态势。这是小说《界》从单一的母亲弑毒儿子的故事,慢慢呈现出来的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也是我希望在这部小说里所要表达的一个重要主题。”他接着说。
小说创作的意义,在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注
在小说《界》的创作过程中,次仁罗布努力复原当时的场景,表现不同阶层、不同人物的心态、语言以及服饰。通过这种还原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当时人们的所思所想,感受他们内心的煎熬与挣扎,希望与迷惘。
毕业于西藏大学藏文系的次仁罗布,通读过很多部汉藏史书,这对爱好文学、写作的他来说是一笔可贵的财富。
他说,小说的意义,在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及通过叙写他们的命运,对自身的文化与历史进行一次深刻的反思。
他说:“小说必须是个立体的呈现,看完一部小说就能读懂一段历史,让读者感知当事人的一种情感纠结,他们的生活经历,就是小说创作的意义。”
在他看来,小说要有历史的底蕴,要有人文的关怀,要指出人生存的社会当下,他的尴尬、他的艰难、他的挣扎,这就是小说文本的意义。小说不同于其他文体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次仁罗布表示,广泛阅读关于历史、文化、哲学、自然科学、民俗等书籍,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讲是个必修课。“只有多阅读,你的笔尖才会有所分寸,才不至于脱离现实生活。”
世事无常,承续着藏族传统文学的基调
“事事无常,我珍视一切得来的东西。”次仁罗布说道: “我的小说一直保持着藏族传统文学最根本的基调。”
次仁罗布说,藏族传统文学最根本的基调始终保持在审视人的生命尊严,人活着的意义。“也许,正因为如此,当代藏族文学对于中国文坛来说,是一股新的力量,是不同的声音,是不断对生命的拷问。”
小说《界》获得第五届西藏新世纪文学奖、第七届全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创作新秀奖。它真实地展现了19世纪上半叶旧西藏的社会生活,普通人的情感世界,以及沧桑的民族历史。更展现了西藏旧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况。次仁罗布说:“和书名一样,小说《界》那些无处不在的界线,那些不可逾越的等级,正是人们苦难生活的根源。透过这部小说,我希望大家审视本民族的文化优势与劣势,唤起人们的平等友爱、反思与批判精神。”
著名评论家施战军曾经这样说过:“在内陆文学的先锋写作已经余绪飘散的时候,藏区这个先锋文学的渊薮,依然强劲地活跃着从小说叙述本体出发来探照人的心灵世界的‘先锋派’作家群,目前,次仁罗布就是其中最为醒目的代表性作家。”有人接着说,作为这句论断的最重要的实证,就体现在次仁罗布的小说《杀手》与《界》中。
对此,次仁罗布说,与其他小说创作时一样,在写作《界》时,自己尽量用零度情感来进行写作。“我始终认为文学应该教人向善,给人带来希望。就藏族文学而言,我们应该立足本民族文化,提出另一种生存与价值观念。要利用本民族的人文情怀丰富中国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