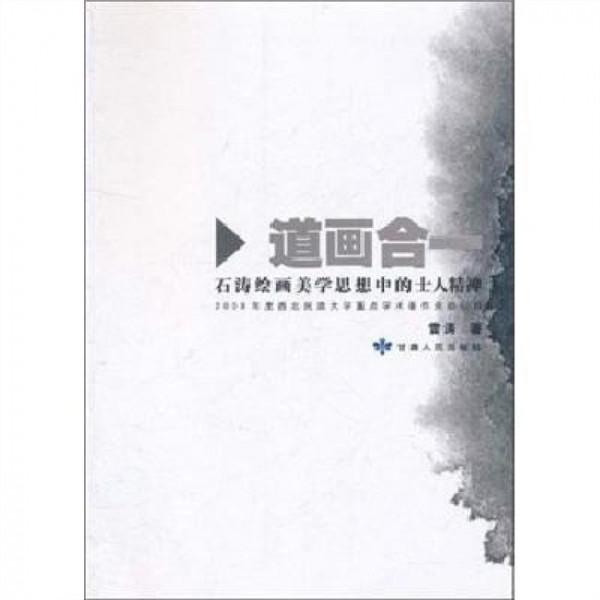黄胄的画 论黄胄的绘画及其在画史上的地位
天才型的画家,往往不师而能。现在画画的人非常多,很多人自幼聘名师指导,进少年宫、青年宫、考上大学、读了硕士乃至获得博士学位,甚至当上大学教授,仍然画得一塌糊涂。而黄胄自学成才,自幼就画得一手好画。他在1943年拜著名画家赵望云为师时,已经 画得很好了,而且正是因为画得好,赵望云才愿意指导他的。
名师指导的学生能超过名师的,少之又少,而黄胄虽然受过赵望云的影响,后来却能独立门户,在画史 上的地位也似乎更高,这是他的天才因素决定的。
黄胄还应该是一位早熟的天才画家。他25岁时画的《爹去打老蒋》就被选入全国美 术作品展览,受到美术界的重视,更得到徐悲鸿的称赞。这幅画当然不算太成熟。那么,他32岁时所创作的《洪荒风雪》就已经很成熟了,这幅画当时获第六届世 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金质奖章。
即是说在国际上已产生一定的影响了。后来这幅画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在历年的展览中,这幅画是必展的作品,至今不但不 算落后,而且仍然是很出色的。齐白石是公认的一代大师,也是天才的画家,但齐白石60岁时,其作品才因陈师曾的推荐,在日本东京府厅工艺馆的“中日联合绘 画展览会”上展出,再产生影响;黄宾虹80岁时才举办平生第一次画展。
前几年,我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讲学,去拜访晏少翔老先生,晏老在解放前的画界是颇有 地位的——他是湖社后期一个分社的领袖,他告诉我:“黄宾虹83岁时,我请他来讲学,讲的是美术史,那时我们只知道他是美术史家,还不知道他画画。
”但黄胄32岁时,绘画已饮誉国内外,而且其作品至今仍很出色,难道不是早熟的天才吗?
黄胄更是早熟而不衰的天才画家。也有很多早熟的画家,有一位19岁就名气大振的画家,40岁后,其画就很差了。我也写过很多文章,提到很多画家30岁左右创作的作品水平很高,40岁后就越来越差了。 我也写过一篇论黄胄的文章,认为他“文革”后的作品不如“文革”前好。
那时我看到很多拍卖会上或者很多杂志上发表他的画,多草草。所以得出以上结论。但近来我受托研究黄胄前后期作品,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处,看到他的精心之作,仍然是不衰的,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的精心之作仍然不算衰。
那时他已70岁左右了,一个画家到60岁时作品不衰,他的作品就不会再衰,而且还有长进的可能。原来,“文革”后,黄胄因名气更大,各种应酬太多,他的健康不如以前,很多作品只好快速完成,有些就很草率,但我看到他的一些精心之作,尤其是挂在一些严肃场合下的巨幅作品,我的看法改变了一些。
我的结论:黄胄是早熟但不衰的天才画家;而且他晚年作画的路子更广。
二、黄胄学习绘画的特点是:无所不师,无所必师。
前面说他不师而能,但在能的基础上加深就要学习了。天才人物学习也和其他人不一样。很多人学习很刻苦,规定自己每天必须读多少书,画多少画,坚持再坚持,但效果未必好。真正的人才(包括天才型)学习是出于内心的需求,所谓如饥如渴,不学反而难过,学习成为一种本能。
据知情人说,黄胄几乎每天画画到下半夜一二点才睡,有时画到天明,稍睡又画,中午只在沙发上睡几分钟,起来又画。70年代,我就听说:“黄胄是纸老虎。”原来他一年画画用去24刀宣纸。这恐怕不是赶任务,也不是有什么压力,而是出于他内心对作画的需求。画画人有了这种需求,其他问题都容易解决了。
从黄胄的画可以看出,他早期的画就没有专师哪一家,他的人物、动物等造型,来自自己的写生,笔墨就是当时流行的画风,但显然比流行的画风更丰富、更完美,也更深沉。即是说,他广泛地吸收了新旧传统的画法,又根据他所表现的对象加以变化。所以,他的画更杰出,虽然个人鲜明的风格不是十分突出,但也不同于一般。
稍后一段时间,他作画更熟练。他基本上是依性情作画,性之所致,笔亦随之。看样子他的画是很神速的。有人说他是速写入画。而他的速写也是性情使然。以性情入画,则画见性情,画惟见性情,方是真画,方是活画。画无性情,皆是死画。画画人纵有功力,若无性情,则画无灵气,虽曰画而非画也。解放以来,画有性情者, 以黄胄为最高。
性情特强之人,所画人物、禽兽、花卉、山水皆性情也,笔也性情,墨也性情,一任性情之放纵,传统、成法皆不在话下。有人说黄胄不懂传统,每一笔皆不合传统。若从传统方法论笔墨,如何下笔,如何运笔,一波三折,平、圆、留、变、重等等,他的笔墨确是不太符合的,但黄胄的笔墨却符合中国画的最高境界——生动,他的画气高韵足,无古法,而自家法立于其中了。黄胄的画的特色也就在其中了。
黄胄的名言是“必攻不守”。则他不守于成法,不守于传统,他自己也是知道的。他把“城”攻下来,让别人去“守”,而他又去进攻了。所以,黄胄不守前人之法,而师法黄胄者却守黄胄之法,这皆是性情使然。有人善攻不守,有人只能守而不能攻。
当然,守得好者也会有地位,明代画家“吴门四家”或守元人法,或守宋人法;而 浙江徐渭也是必攻不守的,在画史上各有地位。但开派的大家必须能“攻”,开派大家的画可能会有很多不足之处,这只好让给守法者去完善了,清代“四王”是守 法派,董巨“元四家”一路画到“四王”手中更完善了。“四王”的性情决定他们只能守而不能攻。黄胄自言“必攻不守”,也和他的性情相符。
我曾说过:“黄宾虹法高,齐白石意高,傅抱石、黄胄气高。”而傅抱石之气高,贵在用笔能虚,然则黄胄之气高,用笔能在虚实之间。潘天寿、李可染用笔贵在能实,大家各有各的特色,绝不随人之后也。
黄胄不是完全不学传统,他经常去博物院看画,并且自己也收藏传统绘画,他还和传统画家以及鉴赏家一起看古画,这不是学传统吗?他的画一见即知具有传统的特色,然又绝不似某一家、某一派,而且用笔也不规于传统,这就是我前面说的,他无所不师、无所必师。没有他不师的,也没有他非师不可的,他广师博取,为我所用,而非我为所困也。
黄胄中年之前,忙于创作,他遗留下来的临摹传统之作品尚不得见,他晚年反而有很多临摹之作。这正如学短跑,开始进步很快,在接近世界记录时,再加快一秒钟,都很困难。所以,他到晚年,必须再进步,一定困感不少。学习古人,也就是取得再进步的办法之一。
我们现在反而能看到他很多临摹之作。我原来想他临摹的画一定是徐渭、八大等和他的画风相近的一路,事实并不如此。清初四僧之首渐江的画冷峻而静谧,和黄胄画的 飞动而热烈完全相反,他也临摹。
他在临摹的一幅《梧石图》中题道:“此乃渐江稿,未解全似,却小有己意味。近百年来以模仿为能事者,改头换面,东鳞西爪,往往自诩似与不似,或介于某家某派之间,或有以此为正宗者,岂不自欺欺人。一九八四年,黄胄。
”这幅临渐江之作,却并不像渐江之画,仍然是黄胄自己的画 风。渐江的画是冷而静,用笔沉稳细劲,而黄胄临时,仍用飞动的笔势、粗细浓淡随意,而且梧下石旁还添画了一个美女。他临明代唐寅(六如居士)的美人图,用的也是他自己的笔法。当然,也总有一点儿古人画的意思在内。他临任伯年的画倒有一些相似,但他总忍不住要加一些自己的东西。
有一段时间他专临明代浙派的画,其中以临吴伟画最下工夫,但他对明代的人物画皆不满意,在一幅《临吴伟东山携妓图》上自题:“见吴小仙郭清狂以至文徵明写 《东山携妓图》,皆不佳,死板无生气。小仙平山过份草草,近于荒唐。
明以后人物画日渐衰落,至任伯年方见起色。黄胄。”看来他对中国画史还是很熟悉的。这幅《临吴伟东山携妓图》,仅构图似之,其中人物的笔法全被他改了。吴伟的笔法是刚硬直率,而黄胄的笔法仍是飞动随意见性情。显得十分生动。
性情太强烈的艺术家临摹他人之书画,太多皆不似。八大山人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很多篇,完全不似;梅清临摹古人之画,也基本不似;担当和尚临摹很多古代及前代作品,也无一相似。外国的画家如弗朗克?6?1奥尔巴赫,乃至培根一生临摹,也无一幅和他人相似,即使把原作和临作放在一起对照,除构图有一点相同外(也不 全同),其他几无同处。
性情中人,处处显示的是自己的性情,他临摹别人的作品,不是先吸收再消化,而是先化之后再吸收,吸收时已变成自己的东西了。所以,他临摹别人的作品,看上去完全不似,似乎白临了,其实他早已吸收过了,画出来时,已是自己的作品了。
黄胄晚年作画,路子更宽,有时专画鹰,有时专画鸡,有时专画猫。都显示出他无所不师、无所必师和以性情作画的特点。
黄胄的最大贡献是给我们留下大量的草原风情的作品。草原放鹰,草原放牧,草原舞蹈,草原套马,草原琴声,草原庆丰收,草原逐戏等等。大草原的风情,美丽的姑娘,强健的小伙子,飞奔的马群,活泼的毛驴,帐篷、草地、河流,无不在他笔下有所表现。现在西部大开发,对于大草原来说,也会有破坏,当西部美丽而原始的 大草原面目全非时,我们仍能从黄胄的笔下领略到当年大草原的风情。那时候,黄胄的作品就更珍贵了。
三、黄胄画毛驴最闻名,但他自己说他是一个人物画家。实际上,黄胄在人物画上贡献最大。
中国的人物画到唐代是一个高峰,至宋代已开始衰落。宋代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就说过:“或问近代至艺与古人何如?答曰:近代方古多不及,而过亦有之。若 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
”宋人已认为人物画(佛道、人物、仕女)“近不及古”了。元、明、清三 代人物画是远远不及山水、花鸟之盛的,清末尚有任伯年支撑人物画局面。其后有徐悲鸿倡导人物画改革,继之有蒋兆和的改革成功。
徐一度对人物画的改革功劳巨 大。他们借鉴了西洋画法,几代人受其影响,其中产生了方增先、刘文西、杨之光等名家。方、刘、杨之外,加上黄胄是徐蒋之后的人物画四大家。其中以黄胄影响 最大。
方增先、刘文西、杨之光都是学院派的,他们受徐、蒋系统影响,一律借鉴素描,以素描为基础,以中国的笔墨表现出来。方增先在素描的基础上,加以传统花鸟画的笔墨形式,素描的关系,也是化为湿笔表现的。他在浙江,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指导他笔墨技巧的是潘天寿、诸乐三、吴之等花鸟画家。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出版了《怎样画水墨人物画》,加上他的几幅作品,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初学人物画的青年中。刘文西也毕业于 浙江美术学院,开始属于浙派,后来他到了西安,又吸收了京派的方法,加之长期受大西北的地理环境之影响,更多的属于京派,他基本上用西方素描的方法,不过 以毛笔水墨表达而已。
刘文西有很强的造型能力,创作大型的主题性绘画较多,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杨之光在广州,他毕业于北京的中 央美术学院,直接受过徐悲鸿、蒋兆和的指导,开始也是用毛笔作素描式的皴擦,后来到广州,又受岭南派的影响,着色也以西洋光线明暗为基调,形成了独立于京 派和浙派之外的特色,但又有京派和浙派的优点在内。
以上三家,不仅在浙江、西安、广州有较大的影响,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尤其在黄胄被批判而被迫停笔时 期,他们的影响一时很重要。
黄胄自学成才,没有接受过学院式的素描训练,但黄胄聪明(如前所述是天才型画家),他不是不会画素描,而是不画那种当时苏联式的学院派的僵死的、过于精细的、于中国画无益的素描,他又是性情中人,画速写十分生动。苏式的学院派素描浪费人的精力,泯灭了 人的灵性,如果根深蒂固,在创作中国水墨人物画时,其素描关系会时时跑出来干涉笔墨的表现。
黄胄没有这些自找的障碍和干扰,他又曾经受过传统派画家赵望云的指导,加之他无所不师、无所必师,使他不受某一家某一派的约束,而独立门户了。
中国画的高下关键在笔墨,黄胄曾说过他画毛驴是为了练笔墨,最终为了表现人物画的笔墨。一旦受了素描的干扰,中国画的味道就不纯了。黄胄的笔墨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规定,如前所述,他一超而直入中国画标准的最高境界——生动,而且有传统中国画要求的最高准则:散、淡。
散就是胸无杂念,包括没有素描式,光暗对比等约束;淡就是绝对自然。黄胄因性情使然,不期然而然的达到“散”和“淡”的极致,所以,他的人物画也生动到极致。
画人物画能画得很准确者,大有人在。形神兼备者也大有人在。但能使人感到可爱的人物形象则不多了。黄胄画的人物形象严谨也许不是他惟一能做的,但“可爱”却超乎常人,他笔下的春兰、渔家少女、草原姑娘等等,都是那样的可爱,看后令人动心,这就难能可贵了。这也就是我上面说的“不师而能”,乃性情中本有,非笔中锻炼而出。
所以,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黄胄的画一出就受到全国画家的关注,争相学习。而且,有了一定的造型基础和笔墨基础的 画家更是重视黄胄。“文革”期间,黄胄画遭到当局的严禁,但学画的人包括画家还是到处翻找以前他发表过的画,有的到照相馆里,找摄影业者翻拍他的画集,到处传观。
“文革”中很多崭露头角的青年画家如石齐等,都是受了黄胄的影响而成功的。“文革”后期,他被莫名其妙地“解放”了,他的作品又大量地发表和参展,影响就更大更广泛了。
黄胄是中国人物画史上里程碑式的画家,是20世纪中后期影响最大的画家之一。即在两千年的中国画史中,黄胄也是杰出的无人能够替代的人物画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