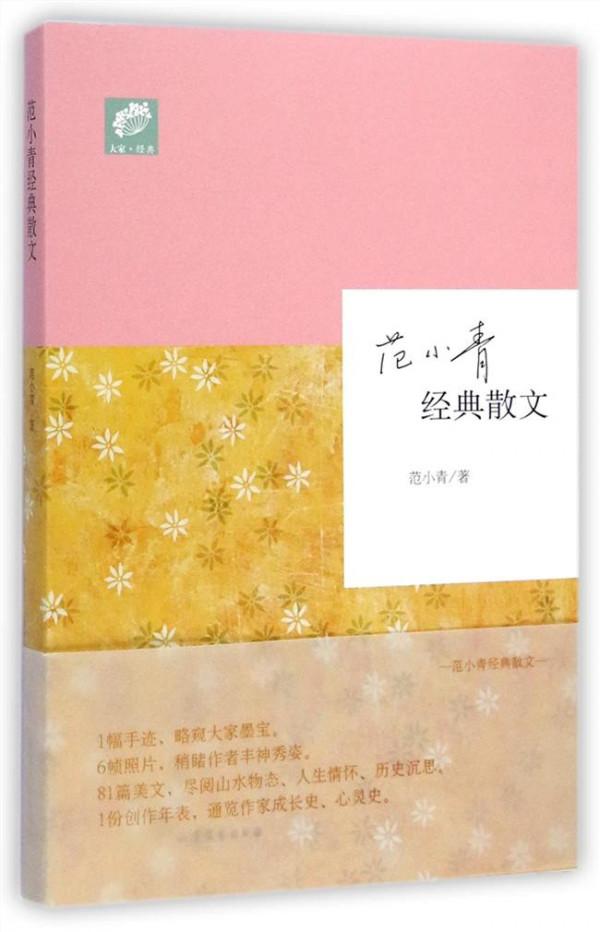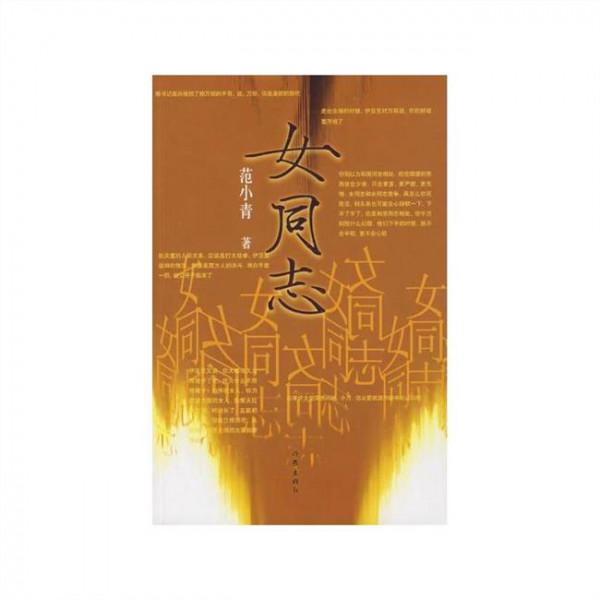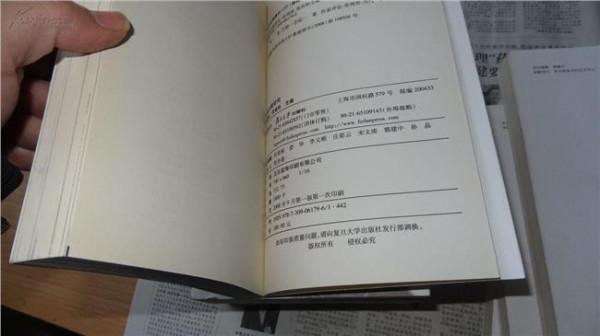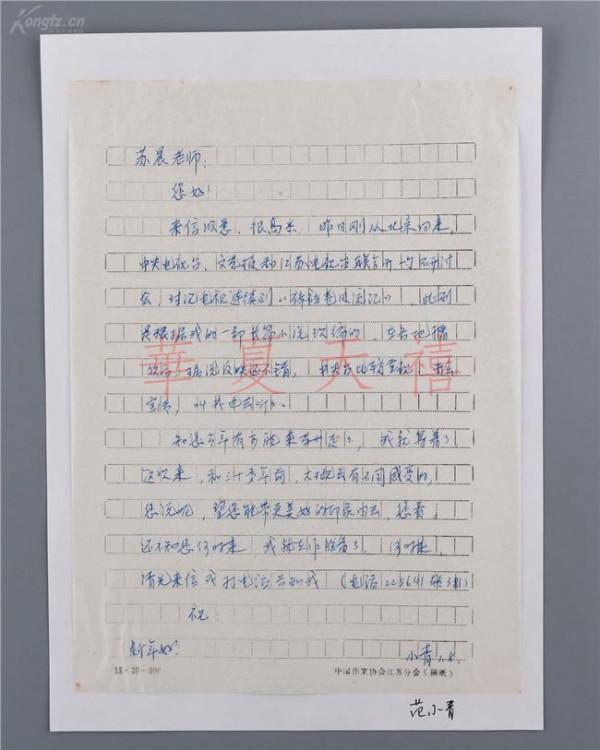范小青的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
《无粮之土》(Land Without Bread)是西班牙最伟大的电影导演路易斯·布努艾尔的唯一一部纪录片,也是纪录片史上意义深远的一部极为重要的作品。它在1933年西班牙试映后被禁,直到1937年,西班牙内战期间,才于巴黎正式公映。
就如布努艾尔自己曾论述:“摄像机是惊异之眼。当电影之眼真正睁开,整个世界都将为之燃烧。” 成长 1900年,路易斯·布努艾尔生于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安哥拉的一户富庶之家。
父亲莱昂纳多·布努艾尔作为雇佣兵参加了古巴独立战争,战后靠进出口贸易起家,1899年回到故乡安哥拉安家落户,育有七名子女,路易斯·布努艾尔是长子。从这样西班牙农村典型地主家庭出身的布努艾尔从小受便到了良好的教育,拥有一定艺术修养。
16岁那年,布鲁奥尔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心灵革命——由基督教堂的簇拥突然变作最激烈的反对者,甚至从教会学校转学。布努艾尔在采访中说是因为他那年受到了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启发,但妻子简妮则宣称是他被教会的腐败贪婪所震撼。
无论如何,立场坚定的讽刺攻击教会成为了跨越布努艾尔一生全部作品的统一主题之一。 布努艾尔成长道路的第二次关键革命是18岁入住马德里学生公寓Resi(the Residencia de Estudiantes)。
那一年,本想去巴黎学习作曲的布努艾尔拗不过父命,只得同意到马德里大学学习农业工程,后偷偷转为昆虫学。但布努艾尔在学校的时光远不如Resi中形形色色朋友对他的影响大,尤其是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运动中那帮前卫艺术小青年们,比如诗人兼剧作家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还有后来享有盛誉的画家达利。
超现实主义为布努艾尔打开了艺术的天窗,更重要的,是让布努艾尔站到了社会革命的前沿,尖锐的向资产阶级,向金钱与集权开火。
同反教会相似,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也将忠实贯穿布努艾尔的大部分电影作品。 超现实主义运动 超现实主义源于法国的达达主义。达达主义追求清醒的非理性,与旧世界秩序激烈对抗,愤世嫉俗,寻求打破一切约定俗成的传统艺术标准与模式,反对艺术的目的性,讲究随机、灵感、任性妄为,提倡“反艺术”,甚至虚无主义。
后来法国诗人、作家André Breton 在1924年发表了“超现实主义者宣言” ,将达达主义发展为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传承了很多达达主义的特色,比如清醒的非理性、打破已有秩序等;但更为显著的影响则来自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超现实主义力求通过各种艺术形式:绘画、诗歌、文学,还有后来布努艾尔的电影,挖掘人的梦境与潜意识,放弃逻辑,从常态的现实世界寻找出荒谬、怪异、不合情理的要素。
超现实主义尤其鄙夷“为艺术而艺术”,强调艺术必须批判攻击旧的世界秩序,通过革命将资产阶级彻底赶下台,从而创立全新的未来。
正因为超现实主义鲜明的政治诉求,超现实主义运动早期与共产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二者最终分道扬镳,归根究底,超现实主义追求一种纯粹的超越与粉碎,而共产主义政党在获得权力之后,也终于站到了现实之荒谬一面,成了他们本来力图推翻的统治阶级。
Francisco Aranda在他的布努艾尔传记中说布努艾尔寻求荒谬,却不是法国超现实主义的荒谬,他的风格深植于西班牙超现实主义:不破坏现实要素本身的客观秩序,比如“马在山上,船在海里”若变作“马在海里,船在山上”就是错误且无意义的。
相对的,荒谬来自于不同要素的组合顺序与整体秩序。只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布努艾尔,才能更好的判断他的电影作品现实批判的关键点。
在《无粮之土》前,布努艾尔与达利合作拍摄了两部鲜明的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作品:1929年的处女作《一条安达鲁狗》和次年的《黄金时代》,后者将成为超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作。
在这两部作品中,布努艾尔和达利充分运用了梦境的交错来表现压迫与反抗的主题,其中充斥了性与暴力和超越逻辑的象征,以及对资产阶级与权势和教会的讽刺批判。《黄金时代》的上映在西班牙引发了反对者攻击影院,扔墨水瓶和捣毁艺术家作品的风潮;在法国公映12天即被禁,五十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现实与荒谬 初看《无粮之土》,观众会有极大的诧异之感。这不仅是因为布努艾尔突然从无序的梦境进入到了严格的现实记录,而是纪录片本身的反传统。
西班牙的拉斯赫德斯(Las Hurdes)位于西班牙中西部的山脉地带,道路崎岖出行困难,拉斯赫德斯人几乎生活在一种原始赤贫状态中,缺吃少穿,没有基本的卫生概念,疾病流行,死亡阴影浓重。
布努艾尔在描述拉斯赫德斯时却完全站到一种“事不关己”的俯瞰高度,配以极馥郁浪漫的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以无比冷静的语调介绍这一与世隔绝、贫瘠落后的村落。拍摄时,为了表现驴子驼蜂窝沿着崎岖山路出行风险极高,摄制组亲自射杀了一头驴,用以再现蜜蜂遍布驴子叮咬致死的惨象。
表面上,《无粮之土》的连贯叙事与客观写实完全脱离了《黄金时代》践踏逻辑的超现实主义影响,但布努艾尔在采访中一直强调,《无粮之土》是《一条安达鲁狗》与《黄金时代》的自然延伸,他的艺术理念并未发生变化。
这一理念,就是从现实中寻找荒谬。体现在《无粮之土》中,就是拉斯赫德斯这个地区贫穷落后的本身。 30年代初的西班牙正处于内战的边缘,佛朗哥领导的民族主义军队得到了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将在1939年战胜共和军建立长达四十年的法西斯集权统治。
佛朗哥宣扬他是神的使者,来到西班牙拯救人民于暴乱和贫困。佛朗哥势力以铁血手腕毫不留情的惩处一切持不同政见的声音,而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反抗精神一直都是其打击对象。
布努艾尔青年时期的密友洛尔卡就在内战初始的1936年遇害。 在这种情况下,将拉斯赫德斯的贫穷落后曝于众目,正是对佛朗哥所谓“拯救人民与水火”法西斯宣传的一记响亮耳光。
对宣扬西班牙和谐繁荣的资产阶级来说,被文明抛弃的拉斯赫德斯的存在是西班牙一块无法抹掉的恶疮,就好比法西斯西班牙的存在是民主欧洲的一块恶疮。 回到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的要素客观性一点,在布努艾尔的艺术理念实践中,拉斯赫德斯作为一个要素整体,本身已构成了不合理的荒谬;使用勃拉姆斯交响曲和冷静不动声色的叙事态度都是为了进一步烘托强调这一现实的自然荒谬性。
在要素自身便完成了超现实主义构建的情况下,不进行人为拆分,如实冷静的呈现要素本身比任何花哨的后期都更有说服力,更能质疑已有的社会秩序。
有人从纯粹的记录角度看待《无粮之土》,比如当年首映后有人批评布努艾尔没能多反映一下拉斯赫德斯入口La Albarca村的建筑特色,就完全忽略了布努艾尔的超现实主义艺术理念。
反抗专政、质疑现实、讽刺权威、宣扬革命,从来都是布努艾尔电影的最终呼声。看不到这点,就无法理解布努艾尔的艺术;而不了解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政权的真相,就无从理解《无粮之土》。
结构 许多评论都注意到《无粮之土》的旁白叙事采取了一个“是……但是……但是”的双转折结构。比如说拉斯赫德斯五月六月最为困难,连土豆都没有;但人们可用野樱桃来补充;但这却使他们得上惯性痢疾。
再比如教会学校偶尔给孩子们一小块面包;但孩子们的父母因为没见过面包不敢让他们吃,会把面包扔掉,于是学校决定让小孩们在学校吃;但这也造成了社区的内部分化。
超现实主义电影的著名评论家Ado Kyrou在评论《无粮之土》时说,这样的“是-但是”结构在描述拉斯赫德斯的穷困落后时造成一种希望存在的假象,然后再次转折,将微小的希望彻底粉碎。最终,要改变这样的人间炼狱,只能依靠从下而上的反抗与革命。
除了旁白的逻辑结构,《无粮之土》的视觉画面也充分反映了布努艾尔的一贯剪辑特色。布努艾尔对炫技类花哨剪辑的深恶痛绝世人皆知,他曾经说过,一旦摄像机跳出来打断叙事,他就立刻失去兴趣离席。
他自己的摄影风格十分接近法国新浪潮之父巴赞的理论:静态角度,固定机位,中景构图,布局细节丰富。布努艾尔很少用特写,一旦使用,便有明确的强调意义。比如在拍摄河边一个因病躺了三天的小女孩时,镜头给了小孩面部大特写,还有她浮肿的咽喉——小女孩的天真与她的悲惨命运形成鲜明对比。
又比如在拍摄唯一的教会学校时,镜头走过课桌下孩子们的光腿光脚,然后给了墙上一张西班牙古典蓬蓬裙美女图片定格特写,同时配解说:“这位高贵美女在这做什么?”除此之外,布努艾尔还特意强调了尽管拉斯赫德斯的贫穷令人难以想象,这儿的孩子却接受跟其他地方完全一样的道德教育。
其中一个孩子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尊重私有财产”——又是近景特写。
可见,每一次镜头的放大都是“荒谬”的再一次强调:贫穷是资产阶级贪婪与对弱势人群忽略的直接结果,“尊重私有财产”只能进一步推进这个恶性循环。 遗产 评论家Joan Mellen在综合评论布努艾尔的电影生涯时提到,布努艾尔认为一个艺术家的职能并非是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法。
布努艾尔曾写过:“在任何社会中,艺术家都有责任。他的有效性当然是有限的。一位作家或画家并不能改变世界。
但他们能构成一个极其重要的不服从边缘。感谢他们,当权者永远不能断言人人都赞同他们的行为。……一旦权势感觉它是完全正义且被赞同时,它会立刻摧毁我们仅余的自由,那就是法西斯主义。” 正因为如此,在《无粮之土》中,布努艾尔并未停止拍摄,把钱花在改变拉斯赫德斯人的生活状态上,也没能救治那个可怜的小女孩(为了场景重现甚至还杀了两头无辜牲畜!
)。因为任何他能提供的帮助都将是小规模的、暂时性的。相对的,他在长长的电影生涯中忠实如一的刻画资产阶级社会与教会的贪婪丑陋,而社会的弱势群体及边缘群体则是布努艾尔舞台的中心,就算反角,也是体制与社会的牺牲品,也都有人性与情感的微妙光辉。
所以《纽约时报》杂志Carlos Fuentes的评论《布努艾尔的审慎魅力》中才说“他为真正的电影自由设立了最高的标准”。
1939年西班牙佛朗哥政府上台后,布努艾尔开始了他长长的流亡生涯,先到美国,与达利交恶后在红色恐怖中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驱逐”,辗转好莱坞五年,终移居墨西哥,1949年入籍。
1960年,布努艾尔被佛朗哥政府请回拍摄《维莉蒂安娜》(Viridiana),剧本竟骗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电影直接送交61年嘎纳电影节,一举摘得金棕榈。
此片对教会和思想禁锢的辛辣讽刺批判在西班牙集权政府中引起轩然大波,“广电ZJ”被全体撤职,《维莉蒂安娜》足足被禁16年,直到佛朗哥去世。 布努艾尔“电影自由”的高度和他对社会制度不合理的持续批判我觉得也只有斯坦利·库布里克能与其比肩。
他的遗产,除了超现实主义理念在电影艺术中的运用,更是一个艺术家对社会肩负的责任,是审查背后依然我行我素的智慧,是不畏迫害与噤声始终如一贯彻主张的勇气。这一切,才是一位真正伟大艺术家应有的历史姿态。 《电影世界》2009年11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