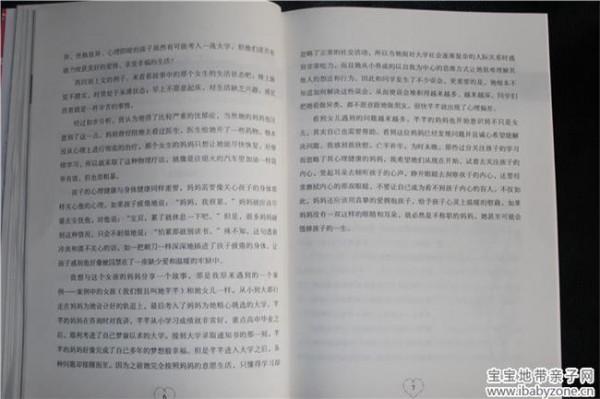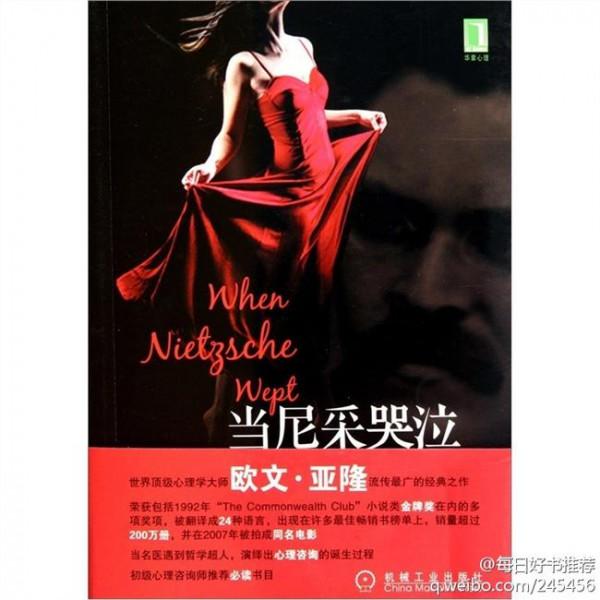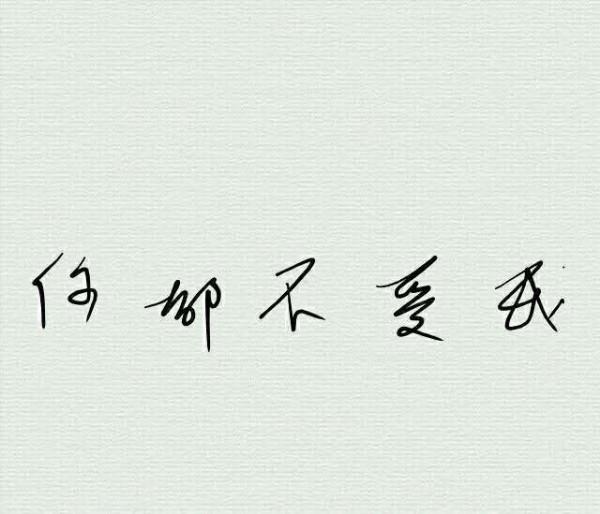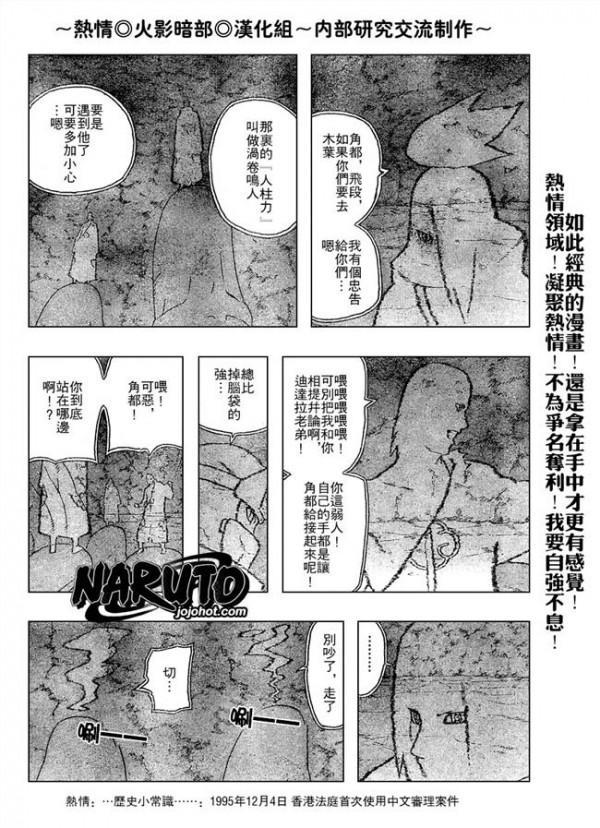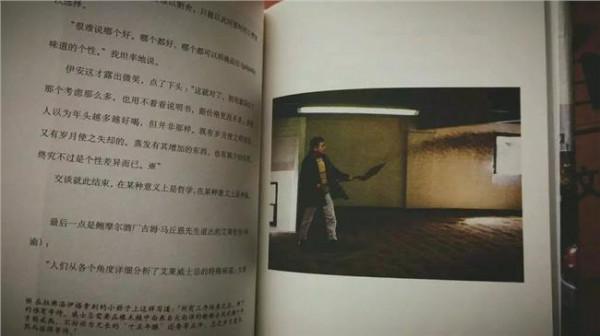陈染名言 理性思维的女性感性化呈示 ——论陈染小说的语言魅力
(四)叙述上的呈现 严格来说,叙述应该单独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论述,而不应该归在语言当中,但是,鉴于女性写作的特殊性(其叙述往往跟语言紧密结合并且决定语言风格),本文仍将其归入语言,以求更完整地把握陈染的语言风格。
1.叙述方式 与许多写作的女性一样,陈染的叙述方式是一种自白内省式叙述。这种叙述方式便于她从女性体验出发,从个体体验出发来抒写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哲学思考。同时,在叙述中,陈染还不时结合叙述分流、意识流等手法,体现出作者为语言表达所作出的努力。
这首先表现在她的文本中人称的变换上。个人化写作决定了陈染的小说大部分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这为她表达个人体验提供可更大的空间,像《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凡墙都是门》、《破开》、《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等,均用第一人称叙述。
然而陈染并不是一味地用第一人称叙述到底,根据自己的表达需要,在文本中经常出现人称的变换。最典型的当是《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在这个文本中,一共有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以“黛二”为叙述者进行第一人称叙述;而第二部分转而变成第三人称对“黛二”进行审视;第三部分却以“大树枝”为叙述者进行第一人称叙述;第四部分则更直接的以“黛二独白”、“伊堕人独白”交替叙述,然后转为第三人称;第五部分是以“黛二”的母亲为叙述者进行第一人称叙述;第六部分又转为第三人称叙述;而最后第七部分则又回到以“黛二”为叙述者的第一人称叙述做“总结陈词”。
这样的饿表达很容易让人想起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作者这样写无非是想争取最大的自由度来表达女性体验和个体体验,在这里,陈染语句上极具张力的特点已经扩张到整个文本,难怪戴锦华会认为“这是一部过度表达的作品,每一细节都包含着多重读解的可能。
” 实际上,在陈染的很多文本中,像《私人生活》、《无处告别》、《凡墙都是门》等,均有这种人称的转换,这些文本或多或少也都存在着“多重读解的可能”。 其次,陈染叙述中还经常出现一些无交代的场景变换。
在叙述中陈染似乎沉浸在自己的语言与体验当中,感性自由地表达,只在乎表达的需要,而毫不顾及现实与读者,在现实场景与梦幻场景之间毫无交代畅通无阻地延续自己的思路。如: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作文本写日记的时候,我的哈欠一个连一个,我本子上的字迹也像哈欠一样一串串起起落落、歪歪斜斜,如同鬼画符。
我的头越来越沉,身子好象被抽掉了骨头,坐立不住。 这时我的母亲忽悠一下就走到我面前,奇怪的是,她没有同往常一样,一边推门,一边叫我的名字…… …… 我被自己的哭声弄醒过来,发现自己原来还趴在作业本上,作业本居然被我的眼泪洇湿了一小片。
(《私人生活》) 又如: 我忽然用力拨开他的打手,终于大声地说,“我是来告诉你一件事!
” “什么事?”他对我疑惑不解地问。 我愤怒地盯着他的脸孔,“我就是专程来告诉你……哪儿是私部!它在这儿,在那儿!” 我在他早年摸我的地方,“回敬”了他。 我十分用力地摸了他!
T这个时候,表情惊讶,神态复杂。 当我想平息自己身体内部莫名的紧张和激动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其实站立T先生面前纹丝没动,我的手一直攥得很紧地垂在大腿两侧,并没有抬起来过,也不曾触碰过他的身体。
我的两只僵紧的小手,如同两块死去的石头。 而上边所发生的那一幕,不过是在我的想象中完成。(《私人生活》) 这中场景的转换同样出现在陈染的多个文本,此处不再罗列。这里要说明的是,通过梦境和想象,作者可以表现一些用写实无法表现的人物心理,而且,既然不是在现实当中,作者更加可以不顾逻辑与常理来表达自己的体验与感悟。
不过,这种场景的转换尽管是很感性化,但其最终目的是要延续作者的思维或通过精神分析来表现人物,只有在这种理性思维的前提下,作者才会任其思绪飞跃,笔走蛇龙的。
再次,陈染的个人话叙述带有明显的泛化倾向。陈染似乎不满足于停留在单一性别的女性体验或单一个体的个体体验,她总是试图通过抽象整合来将个人体验提升到生命体验的层面上,这也是陈染不同于或高于其他女性作家所在。
贺佳梅在《个体的生存经验与写作》一文中也提到:“对超越性精神本体的关注使陈染努力对个体体验做泛化处理,而尽量避开宣泄式或自我抒发式叙述。
她常常力图对个体体验作出某种宏大的整合。” 在《沙漏街的卜语》中,陈染有一段话创造性地化用克尔凯郭尔的“个人代表集体”的观点:“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是我的成长期抑或成人后的任何阶段,我永远都无能为力地处于少数的状态而存在。
幸好,我并不为自己身初处少数这一尴尬地位而自卑,恰恰相反,我始终以为浴缸中那些覆盖整个水面的爽身泡沫并不能洗掉身上的污渍,而倒是涂抹在身体上的那少少的几滴浴液清洗剂起着本质的作用。
多数人很多时候就是那年茂盛的泡沫,是一种虚弱而空洞的力量。能够在较长时间里以及较高的层次上,安于寂寞,我以为才是真正的力量。” 正是这种理解,促使陈染在文本中不断将个人经验作泛化处理。如: 她的热情之高就像我小时侯第一次玩“过家家”。
其实,她就是在过家家,而且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在不自觉地玩过家家,在自己的小王国里充当一个角色,高兴着生气着快活着愤怒着。在自己设计的一个假装的故事里,玩着玩着就认真起来,生活也就有了意义。
(《消失在野谷》) 汽车猛一刹住,拥挤不堪的乘客在惯性作用下全部做前倾状。一位矮小戴眼镜的老头倒向迎面站着的孕妇,急中生智,顺手捏住女人的鼻子。待车身稳住,人们姿势复原后,一片哄笑。
老头才抱歉有尴尬说:“对不起,我实在对你……无从下手,不!是没地方扶,全赖惯性作用。” 老头的话颇具象征意。人活着不就是靠惯性作用?为什么活着?因为活着。然而惯性本身并没什么。悲剧在于总意识到人以之存在的惯性。
(《归,来路》) 这一点也是陈染的独特所在。与陈染风格十分接近的林白,也是以写女性写个人出名,但她就没有陈染这种“个人代表人类”的写作动机。徐岱在比较陈染与林白的时候就说过:“同样是一种‘回望’,陈染的做法是对生命存在作出某种提纯……与陈染一样,林白的个人化无可置疑,问题在于她未能通过这条回归自我之路,真正深入到生命意识的深处,写出那种鲜活生动的生命体验。
” 因此,与陈染相比,林白的写作就显得狭隘和局限了。
2.叙事模式 陈染在《与往事干杯》中这样写道:“我并不喜欢叙述事件。当我写到事件经过的本身时,我感到笔墨生涩而钝拙;然而,当我写到由事件而引发的情感和思想时,我就会妙笔生花得心应手兴味十足……我喜欢在诉说感情和表达思想的地方驻足流连,无休无止地梳理品味。
” 这段话充分表明了陈染对于叙事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决定了她的叙事模式。陈染很少从头到尾完整地叙述一个故事,而是通过回忆、联想等零碎的片段来拼凑故事,她似乎从不在乎故事的完整性,而将整个写作中心放在“由事件所引发的情感和思想”上。
故而陈染的叙事不是一条射线,也不是一条简单的曲线,它的高度自由延伸简直就像一副正在生长的非线性几何图。
当然,叙事终究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像非线性几何那样没完没了地生长。整体上,陈染的叙事更像一株蔓生的牵牛花,有它的根,也有生长的方向,每长一段,就会生出旁枝来,而且她并不是伸出旁枝就肯罢休,而是在那枝上“驻足流连,无休无止地梳理品味”,直至开出一朵花来才肯继续往前生长。
所谓“根”,是指小说文本的哲学底层,是一种理性思维,也是陈染通过一个文本所要表达的东西;而“枝叶”则是指这种理性思维基础上自由延伸的体验和感悟。
故此,我们也许可以将陈染的叙事模式称为“牵牛花式”。在她的几个重要文本,比如《私人生活》、《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无处告别》等等,均采用这种模式。 这种叙事模式打破了时间的连贯性,使得时间空间化,作者可以在空间里表现时间。
这正迎合了陈染所擅长的描述式语式,而避开了故事性强的讲述式。实际上,陈染在使用这种叙事模式的时候占了很大的便宜,她总借回忆之名来介绍未知的人物身世或补充交代故事情节,而在故事整体上得到完整描述的前提下,她就更有理由和资本来展示那无休无止的女性体验了。
然而陈染的叙事又有散文那种形散神不散的特质,总有一种灵魂贯穿着她的文本,而这种灵魂并非单纯的理性的东西,而是理性与感性在审美上的结合,这使得陈染的叙事享有较大的自由度而又不至于凌乱。
这点,也是陈染有别于林白等其他女性作家的地方。林白的叙事也相当的自由松散,但她显然是自由过头了,在她的文本中同样充满诗性和哲思,但她的叙事却显得凌乱琐碎,当然并非说林白就不如陈染,林白也并非意识不到自己的这点不足,而是有意为之。
在《语言与声音》一文中,林白这样写道:“在我的写作中,我最喜欢做的就是让局部的光彩从整体中浮现出来,把整体淹没,最好有无数珍珠错落地升上海面,把大海照亮。
” 而陈染不同,即便她文本中有很多珍珠般的局部,也不会“错落地升上海面”,而总有一根线将一颗一颗的珍珠串连起来。 总之,“牵牛花式”的叙事模式,避开了宏大叙事的框框架架与传统叙事的严谨结构,使作者在叙事上享有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陈染在展示女性体验与感触时,就显得更加如鱼得水了。
可见,独白内省的叙述方式和“牵牛花式”的叙事模式,为其语言的充分表达提供了重要条件,而第一人称叙事者以倾诉的态度进行叙述,又让人读起来亲切可感;同时,这种叙述方式和叙事模式又是富有创造性的,这本身也表现出一定的审美价值,也是构成陈染语言风格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陈染小说语言审美价值的呈现我们可以看到,修辞上绚丽多彩繁丰新奇;语感上柔缓舒展富有弹性;性别上温婉阴柔优雅伤感;叙述上直白倾诉亲切动人。而这几个方面并非截然分开,只是笔者论述需要才加以划分,实际上,在陈染的文本中,这几个方面都是毫无痕迹地互相交融,其有机统一使得文本在整体上呈现出抒情诗的美感。
诗的自由的思绪和语言只有在她的理性思维的范围内才允许出现,而且必须以高蹈优雅的姿态出现。这种理性思维在她的文本中或从整体上指导整个文本,或在局部上表现作者对某个话题的哲性思考或生命体验。
而这种理性思维又使得她的语言富有哲理性,这点在上述几点中均有论述,需要指出的是,语言的诗性与哲理性是交融在一起的,不可分割,而且常常是结伴出现的,它们共同构成陈染小说语言最主要的两个审美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