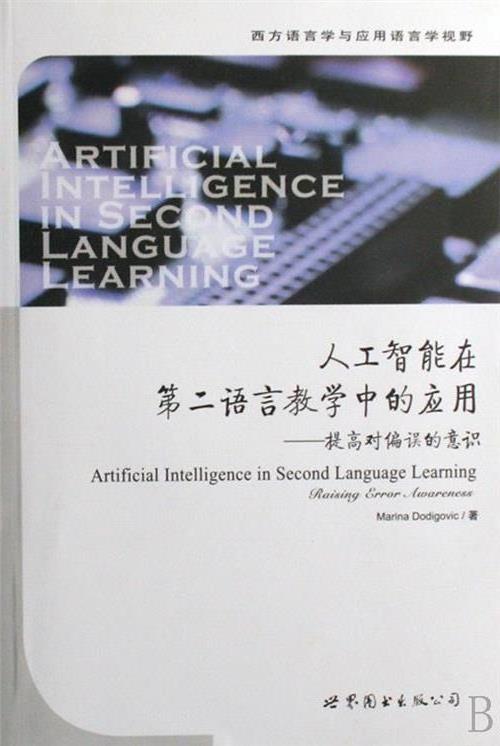潜在能力:人在早期学习第二语言时大脑的反应机能
在同一地球村生活的村民们,他们的后代直接受益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语言已不再是障碍。今天儿童的语言学习经历非常丰富。在婴幼儿最早几年的关键时期,他们的学习速度最快,同时这也是神经可塑性极高的时期,最利于大脑收集和存储像视觉元素和声音基本单位等来自外部世界的基本信息。

当婴儿听到一种语言时,他的大脑会产生与这种语言的声音相对应的神经表征。这些表征为日后学习语言中更复杂、更高级的词汇和语法等知识打下了基础。语言处理过程中的神经表征在人生最初的几个月内已经建立起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既不会被覆盖,也不会丢失,会一直储存在大脑里,在特定环境下通过神经模式表现出来。

但这也引出了下一个问题:既然人生早期已经建立了固定模式的神经表征,那么日后学习第二语言是否会受母语的影响呢?
由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Lara Pierce率领的一个研究团队对人出生后的早期语言经历做了对比分析,试图解释人生早期接触到的母语是否会影响后期大脑对第二语言的处理。
研究对象共有43人,分为三组,年龄分布在10-17岁,都具有出色的法语能力。
第一组为法语母语者,自出生起只接触法语,没有其他语言经历。
第二组为汉语和法语双语使用者,自出生起就接触汉语,并在三岁前开始学习法语。
第三组为来自中国的国际收养儿童,被法语家庭收养,自出生起接触汉语,但从收养后(6-25个月大)开始学习法语,汉语接触因此突然中断。

研究小组利用fMRI(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记录了三组参与者在执行PWM(Phonological Working Memory,语音工作记忆)任务时大脑的激活情况。研究小组利用PWM的特性,希望能通过PWM任务测试来了解人生初期语言经历的神经模式,同时也从神经学上验证PWM是否对这些初期语言经历较为敏感。
三组研究对象成功执行PWM任务的前提是利用短时记忆储存所接收到的声音刺激——法语伪词(实际不存在的词,但是发音规则符合法语,如vapagne、chansette),用伪词作为试验对象的好处是它不会受到受试者已学语言中习得部分的影响,比如意义、语法等。研究人员记录下三组对象的大脑激活区域,通过神经学分析,发现人稍晚接触第二语言会影响人后期语言习得的处理过程,即便是出色的二语学习者也是如此。

在排除了各项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后,聚焦fMRI结果发现,即使参与者的人生早期只错过了一小段儿法语环境,即使他们最后也都说一口流利地道的法语,但他们处理语言中的发音时表现出来的却是迥然不同的神经模式。

在语音工作记忆网络中,功能性的连接只在左脑岛和其他左偏侧区域之间建立起来,也就是说法语母语者在处理法语语音时,动用的是与法语语言更相关的区域。然而,另外两组在这一区域的激活表现微弱,他们在神经系统中启用的是另一种处理程序,这套程序原本用于处理另一种语言——汉语。但这不意味着左脑岛就完全置之事外,与非母语的语言形同陌路,其实它也发挥了作用,只是相比之下程度较弱而已。
以往研究也显示,双语习得者早期学习二语时,在处理语言任务时,双侧激活在额区、颞区和顶区表现更强烈,与该研究团队在双语习得儿童组中发现的结果相同。同时,右半球颞上回的激活通常与音乐、非语言的声音处理相关,而与皮尔斯设计精密的语音识别联系不大。

由此说来,麦吉尔大学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前人的结论,即双语使用者依靠执行控制和认知控制功能处理语言,随带激活的是大脑双侧部分区域、注意力和认知控制区域。
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即使双语儿童和收养儿童激活的神经模式截然不同,但是他们的法语水平依然自如流利,丝毫不逊于母语者。双语儿童和收养儿童依靠一套替代性的神经系统,获得了与母语儿童同等的法语语言水平。

这一解释也得到过前人的证实,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双语者与认知控制区相关的额区、颞区和顶区会做功能上的改变,与语言处理相关的子网络的连接性和精确性也会随之增强。因为研究对象参加测试时处于10-17岁的年龄阶段,是否这些影响会随着青少年时期一直延续到成年时期。这都是未来非常值得探究的领域。

麦吉尔大学的上述研究结论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乔姆斯基的语言观。老乔在解释他玄乎的普遍语法时,就提到语言是天赋。儿童在出生之前,并不知道他要选择何种语言作为母语,但是他出生之后,都可以从容地学会。这种能力不是针对个别语言而言,而是对所有语言适用。

语言之间存在共性,儿童拥有一套天赋的“语言习得装置”,只要初期设定好参数,就可以轻松调到对应的语言频道。老乔的理论对后世语言学的影响无疑是翻天覆地的,但它也富有争议性,多年来,总有语言学者不断努力挑战他的权威。

老乔自己曾开玩笑说,唯一靠谱的办法只有核磁共振。但使用了核磁共振技术的麦吉尔大学的团队只重点研究了法语和汉语,因而现在说他证实或推翻了老乔的理论都还为时过早,但人们的确在这一途径上看到了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和潜力。

总而言之,该研究得出的推断和结论都告诉我们,人生早期建立的语言(汉语)中语音的神经表征与后期建立的二语(法语)的语音神经表征是不同的。最早期的神经表征就像爱情一样忠贞,历经时间、环境的变迁,一直在那里,不离不弃,守护我们。当我们在新的语言环境中遇到困难时,它会从大脑的神经长河中,焕发出新活力,赋予我们新的语言习得能力。所以,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也不是鱼与飞鸟的距离,而是你拥有着如此深情的大脑,你却不知道它用行动在默默地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