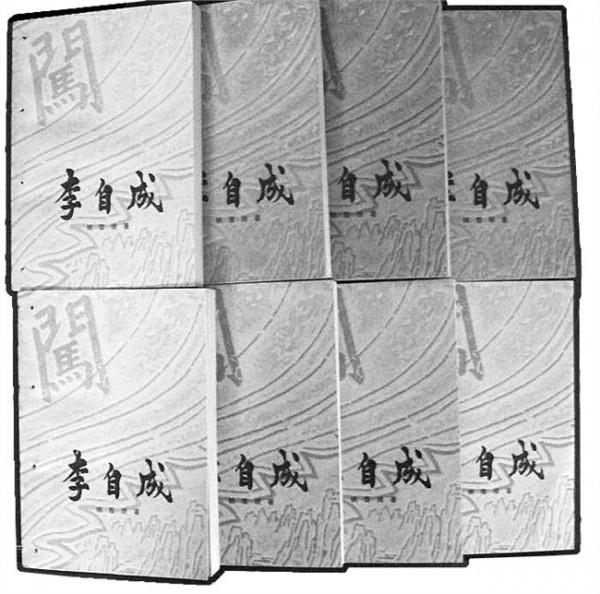〖滕代远〗探访滕代远故居
今天(7月26日)十二点二十从凤凰离开江天广场。我是匆匆从陈斗南古宅,与其孙子陈奇伟老伯触膝而谈时,被妻子兰儿电话催促而回。意犹未尽,我们相约今后再来拜访陈伯。我还是有些遗憾。车子开出虹桥头,拐到原来的凤凰汽车站,去怀化的路已经改道穿过小区。这是凤凰的门户,却路面破烂不堪,整个是遍地积水,坑坑洼洼,车子几乎不能行驶。
我心里很是不满。说:“这哪像一个旅游城市的门面形象。路面烂就能看出县政府的腐败。无所作为。而这些小区的劣质的仿古建筑,是凤凰最大的败笔,祸害无穷。”
车过沱江大桥时,桥头高悬“危桥”二字。我真的不知道,凡是从怀化方向进入天下凤凰的游客们,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会有何观感。凤凰已经破坏无余。
当车过石羊哨大桥,不远处应该是后来修建的代远桥。这是通往麻阳县著名的历史人物滕代远故乡的路。我停车询问路边一个朴质沧桑的老汉:“老人家,滕代远的老家在哪里?”老人家不假思索回答:“哦。滕代远的老家,叫大门坡。
到前边过桥,直接走,只八公里路。”老人做了个八的手势。皱纹蹙缩地向我微笑。我也微笑的致谢。前行四五百米就是石拱桥。前面一辆载人的三轮车。我超车而过,但到了桥那头却是两条岔道:一条沿河而上,一条进入山里。停歇从车窗问三轮司机。年轻和善的司机告诉我:“往这边走,直接走到一个水泥坪就是了。”于是,我往山里奔驰。好在细雨蒙蒙,山色青葱。空气清新,满目润泽。
可是进去两三里,又遇到分路口:一条往左泥沙路,一条朝右水泥路。虽然我疑心应该是水泥路。因为毕竟滕代远是新中国第一任铁道部长。但是桥头那分路就是,沿河是水泥路,而进山是沙石路。我还曾感叹人走茶凉的可悲,如果代远还建在,不至于通向元帅级国家领导人的故里道路,会如此不堪吧!
还好一个老农在路下边作田,我伸头问询。那老人也很熟练的回答:“哦,戴木坡,就往左手边进去。”看来不同村落的人对滕代远故乡,叫法是不同的,不过大致发音相似。青山绿水间,有许多新楼房,与古老的青石房基,黄色土砖砌就的黑瓦屋,反差很大,很不和谐。我在心里逆想,不知滕代远的老屋,会破落到何种程度。
道路越走越幽深,山势越发高峻,而且山上松柏越来越青葱蓬勃。转过一个茂密的松柏山嘴,正好逢岔路口,一根分支的水泥路向右手延伸山林离去,而左手边的路旁山脚,立有一块石碑,大书“滕代远故居”几个石雕文字。下车一看,石碑旁的青石板上,雕刻有故居游览参观的示意图。图上标示祖坟,碾坊,故居,代远小学等故居文物位置。之间是石板路连接。不需询问,只沿着山道红砂岩石板阶梯子,往半山腰故居蜿蜒而去。
我与妻女,女儿的大学同学,一起拾级而上。整个村落建在半山腰里,古风犹存,苗寨模样黄墙黑瓦,古朴明艳,因地取材,天人合一。但山下路边已经有几栋楼房了。刚好住雨不久,满山松柏里的蝉鸣,是经雨淋湿一样。山色为之清幽如许。
或者是欢迎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吧。我心里微微很些激动。似乎等地很久的一个梦想,终于如愿以偿了。似乎是盼望已久的一个朋友家拜访,终于置身其家门了。我不由加快了登山的脚步。因为示意图上的故居的高墙飞檐,让我出乎意料的惊喜。故居不会是我原来担心的破落的土屋,而是一个宅子。应该是好老人家。
很远就望见了石级前的树荫里的小木亭与高高的马头墙与翘檐,故居到了,围墙外的进大门石级两旁,左是柳树柔枝吹拂的一丈见方的池塘;右边是一平地里的干碾坊,大小碾盘都有,碾槽原封不动。这应该是富裕人家的标志。因拥有碾坊,就是财源细水长流。
从前是一个甚至是几个村落只一个碾坊。《边城》里的翠翠的心上人傩送就面临过娶拥有碾坊与渡船的选择。但傩送还是心里选择了守渡船的翠翠。翠柳下的水塘,水浑浊色如黄泥墙。但少年滕代远一定在此洗过手洗过脚,而碾坊里的牛拉石磨的隆隆声,肯定同年的滕代远也经常听到过。
而一人多高的红砂石块砌成的石墙,墙上再砌上人把高的黄泥墙,墙头盖瓦防雨侵蚀。墙下的通道是两米宽的二十几米的石铺进门路径。这是一百年前,滕代远曾经走过的地方,也是每天进出的必经之地。
踩在那石缝的青草,俯视那湿漉漉的岩石,徒生说不出的感触与滋味。远远看见围墙门楣上,“南阳堂”三个白底黑字,很是鲜明。误以为这是故居大门。可是走近才发现,正式大门在围墙拐角处,两根青砖柱子,上面架起木骑马楼,盖点青瓦,显得朴素安静,一种虚空无物的山林气息,扑面而来。
一种历史云烟淡淡萦绕在树林山峰中。从墙头可望见正屋的翘檐屋角,门楼瓦檐下挂着一块木匾“滕代远故居”题写书法一般,落款人很陌生。而原来的门楣上是白底黑字“吉迪”二字,我不知何意,应是原物。
因出自乡村私塾之手吧。可是走近推门,却沉沉的栓着,敲门喊门也没有回音,从门缝望去,只能看到石板路径与砖石屋墙,以及墙壁上的关于滕代远的生平简介。屋角的菜地,包谷树长势喜人。绿箭横披,包谷棒子红樱妩媚。典型的农家院落。门外无锁,是里面上栓。我期待主人在家。兰儿去敲门,也没有人迹。
我让兰儿待着,自己独自从小池塘的亭子边,往一个小山包走去,石板路已被草封树掩,树叶草间,宿雨如露,能打湿鞋子裤脚。两旁高大茂密的松柏树叶,还在掉落雨水。很凉爽很虚静。小雨刚过,青山如洗。石板上泛着水光。
我估计走上去,松柏树林的某处应该是滕代远的祖坟山。果然翻过山梁,那是三四百可大松柏的疏朗的林子,刚下坡处的石径左侧就是一片青青的坟墓。一层一层的,我看了那墓碑,红色岩石打造,很古老的墓碑样式,其中两块是滕代远祖父祖母的佳城。右墓碑“故父藤滕绍康墓”“男藤国梁,孙代勋,代远。曾孙藤久翔。民国十六年清明节立。”墓联为:“山开丙向阴阳利;向立壬山子孙贤。”
左墓碑“故母谭引香墓”墓文“民国十九年清和节立”墓联为:“后脉来路远;前山对将高。”墓碑里也可以看到作为孙子辈的代远名字。而滕代远的母亲是民国七十一年过世,应该葬于此。因其地过于幽僻,柏木森森,不可久留。
徒生感慨,拍照即归。我想这个普通厚实的土包,就是一代人杰滕代远的来路,本来也应该是他的归宿,可惜死于北京,葬于八宝山,落叶不能归根,也是一种人生憾事吧。我慢慢走回去,这墓地小时的代远应该祭祀过祖先,焚烧过香纸,祭奠过酒肉吧。墓碑上还注明其叔父是国权,国楠。大概扫洒墓园的只有与这方泥土融为一体的叔父后人了。
我回到小池塘,兰儿她们还在等我。问我到哪里。我说:“到滕代远祖坟山看看。风水很好,满山松柏,后依青山,前对山垄,是龙脉之地,可惜滕代远没有埋回来。”
满地是黄泥,水湿淋淋。但如果远至代远的家门而不入,还是很遗憾。有所不甘。心中涌起点惆怅,像是寻隐者不遇。于是,我从碾坊过坎下人家。可是还是大门紧闭,在沿石级而下,终于看到一个和善的中年妇女,正在门前洗衣。一问从她口里得知:“前门不开,人在家里,后门可进。这么绕上去,看到挂着两个灯笼的就是。只是这石板路很滑,也可以从下面公路往前走,在走石板路上去。”
我问:“这老屋是以前的房子吗?”
妇女微笑答:“原来是滕代远祖上老房子,后来维修了一次。样子还都是现的。往这小道走,要小心啊,很久没有人走这路了。”
草丛里的石径,是百年前的老路,也许因为近些年,故居前后门都修了比较宽的石板路,这路就废弃了。但这才是玳瑁村世世代代人曾经走过的石径。
我笑问她:“你们这院子叫什么名字啊?”
她用麻阳话回答:“这叫戴木坡。”
我说:“戴木是种什么树木了。我们那有抱木洞,抱木树遍山都是。我只看到你们这遍山松柏树啊。”妇女笑道:“我也不晓得戴木是什么树木,反正从祖上就那么叫的。”
我们做到简陋的后门,果然挂着两个陈旧的灯笼。可是木门还是关着。敲了无人应答。我绕上后边的高坎往院落瞭望拍照。一个中年男子正好走过来。我就问他:“滕代远故居里有人吗?”他说:“有啊。刚才听到就在里面啊。”我说:“门拴着啊。滕代远还有后人守屋吗?”男子说:“他的子孙都在外面去了。守屋的婆婆,是政府安排的。”他伸头瞧了一眼门后,说:“门没有栓,你重推一下。”
这后门进去,是短短的矮墙,种有桂花树与闲花野草,像个普通的花园,右侧是黄泥墙矮屋,有人居住,应该是守故居的老人居所。雨地里晾着三件衣服。竹竿搭在桂花树之上。这里可以观察故居的侧面全景。通过一个巷道,就是一道小门,就此进入了正屋,小门进去也是一个通道,左边是一间客房,右边是代远父母卧房的墙板。
小巷直通堂屋客厅。靠里是家堂所在,暗淡里八仙桌上供放着滕代远的头像。两边是太师椅。左边一门通滕代远的书房兼卧室;右边一门同其父母卧室,都摆放老师的桌椅卧床,木壁板黑黑的沧桑着,里面没有电灯,暗淡的难以辨识。
空寂的诗人心慌。只有后边窗棂可以露点微光。房门槛很高,门槛下有垫脚岩石,房内有地楼板。而堂屋是土地板,与那时农村老屋相差无几,而不同在于:与堂屋家堂神龛相对,是一个连成一体的会客厅。
屋顶上安置了透明采光的亮瓦,天光射下,洒在下面的两张太师椅上,中间是空空如也的募捐箱。而背后砖墙上有绘制的字画。虽然普通,但也可见此家与别家不同。
中间是一大写的“福”,两旁是条幅:“百年诗礼延余庆;万里风云入壮怀。”有点墨气淋漓,壮怀激烈。而条幅两旁是两幅画相对应:左竹摇曳,右梅横斜。总体旷远脱俗,书香飞逸。而顶上是一大横幅山水扬帆行舟万里图,画轴左右空白处是联语“读书经世文章;道德传家根本。
”白墙黑字,国画山水,虽说粗糙,但绝不低俗。看到这些字画山水图,对于长大的滕代远,自然有其非凡之处。会客厅里的墙壁上的潜移默化,谁能料想到对少年代远的影响之深,而谁能料想到代远对民族历史的推动之大!
从客厅出,右边是厨房与仓屋,很宽敞。左边一门出,石雕门槛,很端庄精致,这是正屋大门,门楣上书“文昭第”,这是砖墙高耸,飞檐凌空。十步之遥才是我们先前久敲不开的故居院落的门楼,门后两个木栓都拴上了。一道短墙过去即使菜园,菜园过去是黄土磊成的厕所猪圈,里面传来猪叫声。
静悄悄的人家烟火风烟悄静。隔离的短墙在雨水里坍圮了一半。泥砖撒落于地。菜地的辣椒树,苞谷树很整齐。而长豆荚,南瓜藤到处牵连,各处快乐的蔓延,依稀当年情景。一棵手臂粗的银杏树,犹如白杨叶片飞扬。
兰儿与灵儿,灵儿与同学,都在院落里,在空荡荡的故居里逗留拍照,阅读墙上的文字介绍,堂屋墙壁是滕代远及家人的图片,暗淡里难以看清。不久她们走了,我还在空荡荡的老宅里。听四周风声与蝉鸣。看客厅里的玻璃橱窗里的文字介绍,其中有一首代远夫人林一的诗《忆往事》。
其中有“同甘共苦数十载,延安窑洞庆相逢。”之句,这是八六年滕代远纪念馆在麻阳县城落成之际,林一到麻阳即兴写就的律诗。正屋们内有一橱窗,上面有几本留言簿,落满灰尘,我独自翻揭,有不少各地留言,但知名者少,虽然如此,但对滕代远的钦佩敬仰,溢于言表。
我翻阅之际,有种冲动想为代远故居留言表示敬意。于是,翻开一本零五年的留言簿,竟然是一本全然没有墨迹的本子,我借古人言“身前身后事,千秋万代名。”落款:“辰溪唐军民于2009年7月26日下午1,20分拜上。今日我带着妻女与女儿的两个武汉同学瞻仰滕公故居,老屋依旧,空荡虚静,虚若无物。我在空荡荡的老屋里,遥想先贤。听户外密密如繁雨的蝉鸣声,感慨不尽!”
我走出后门,轻轻关上木门。把一个神圣的空间轻轻掩上了。兰儿她们已经下到石级下的公路上。我离开代远故居。在石级上碰到一个年迈的牙齿稀疏的老汉。我问他:“老人家!你好!滕代远这里还有什么后人吗?”老人微笑答我:“滕代远啊,他有个儿子,还有几个孙女儿。
都在外面工作,不会来了。”我问:“你看到过滕代远吗?他是哪时离开这地方的啊?”老人为难的说:“那我都不清楚。他离开家时,我都还没有生。他儿子都还在肚子里。”我惊讶的问:“老人家,那你只有六十岁儿啊?”老人说:“我今年七十岁了。
哦。你刚到滕代远老屋里参观啊。他离开戴木坡好多好多年了。下面就是他小时读书的小学堂。边上是后来建的新学堂。”我本想问问更多的往事。可是兰儿在下面催促。我只得告辞了老人。
下面公路旁是一个水泥坪,坪场里边是一栋新式教学楼,校名“滕代远小学”球场外的小溪边,有棵合抱的粗古柏,我匆匆拍照。兰儿说:“那古树下的土屋,就是滕代远当年读书的学堂。”果然这低矮的黄土砖砌的瓦屋,门上挂着“代远少年时求学的学堂”的匾额。这就是一代政治家军事家的发蒙启学之处,掩藏在山林下溪旁,普通不过,简陋不过。可是历史从这里走来,风云从此地兴起。
老人的话让我想起了滕代远离家前,曾娶过一个老婆,乡下知书识礼的女子。可惜后来代远投身革命,四海为家,家书断绝。后来娶了林一夫人。而家里的妻子一直守寡,与儿子相依为命,支撑门户。这是一段难与人言的故事。历史不载,故居不记。
我停车的楼房门前,正好有三个本村人在闲谈。我禁不住问:“请问你们一二事情的。滕代远的大老婆有几个孩子啊。”其中一个妇女笑笑。很隐晦的说:“呵呵。他屋里那个堂客啊。只生过一个儿子。儿子生了一个孙子,一个孙女。
都不住在这里了。他儿子住在麻阳城里,大桥边上有房子。六七十岁了,老了神经有点问题了。孙女抵老头的职,听说在广州铁路上工作。孙儿在学校教书。在哪里教书啊?我也搞不清楚啊。哦,可能是在麻阳县城教书。”
我忍不住问:“那滕代远大老婆,死后葬在哪里呢?”其实我只是委婉的打听这苦命女人的下半生命运。
那三个村民不假思索。抬头望着滕代远的祖坟山的翠色柏树。说道:“那不葬到滕代远的祖坟山啊!”我明白了。这善良能干的女人,为滕代远,守了一世的活寡,也守了一世的老宅,还守了一世的山林。可是很可悲,最后这老宅成了滕代远的故居,却没有一点文字言及这默默苦守的女人,也没有一张图片展示家里一房儿孙的情形。
我们离开这秀丽古朴的村落,其实一般称作玳瑁村。这漂亮的地名,应该是因为出了滕代远之后,而改了的新名字吧,可本地土人却无人知晓。正如武汉大学原名叫罗家山,却被闻一多化腐朽为神奇,诗化为“珞珈山”。兰儿听我说及滕代远家里妻子的遭遇,很是感慨。
说难道连自己的妻子女子都不来看看吗?我说这道有情可原。因为毕竟他那时已经有妻室儿女了。因为新中国强调一夫一妻制,代远肯定要避嫌。可悲的是如今竟然还不能提及他的前妻与子女,这太缺乏人性与天理了。毕竟现在不比那时思想禁锢啊!终究我们必须面对历史,而不是隐瞒历史,甚至歪曲历史啊!滕代远的前妻是可悲的,但幸运能归葬祖坟。滕代远是可悲的,只能远葬北方。何时魂兮归来啊!
六零年代远母亲过世,代远因公务繁忙,没有回家。之后就再也找不出理由回归故乡,重温旧梦了。那时他的第一任妻子还在故居洒扫庭除,等待远人归来呢!微雨有绵绵不尽的下了,我更感慨一个乡下女人的故事行将湮灭,实也是滕代远的人生故事的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