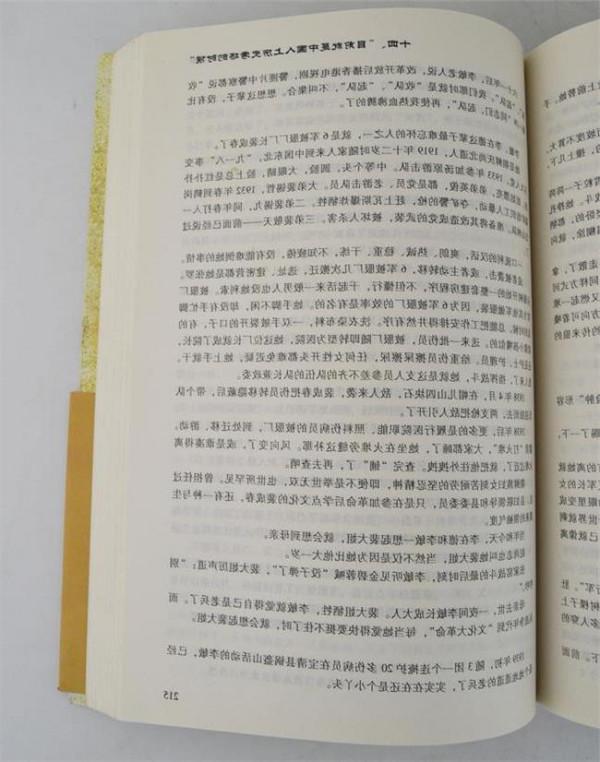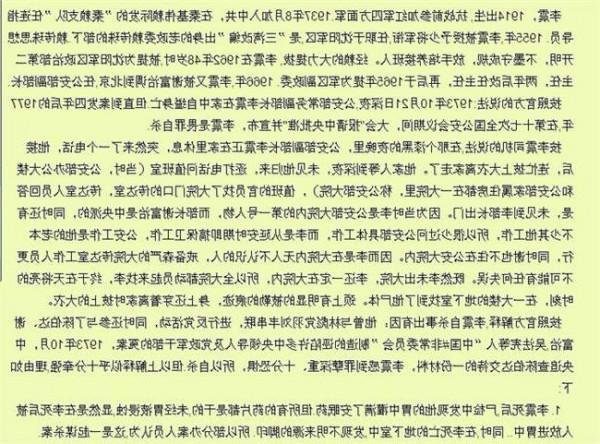刘复之的后代 刘复之:"文革"期间轰动一时的"李震之死"
1973年10月18日,我奉周总理之命,尚在天津办理一起匿名恐吓信案件,接到公安部里的电话通知,要我回京参加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当天我驱车回到北京。
10月19日,因为于桑还在洛阳没有赶回来,李震让会议推迟。
10月20日上午,李震主持核心小组会议。会上,于桑、曾威因为“算旧账”问题发生激烈争论,几乎动粗。李震和我都站起来进行劝解。我说:“争论问题不要这样。”李震让会议暂停了下来。
21日没有开会。
22日上午9点钟左右,我接到李震秘书郑爱萍打来的电话,他说:“上班时间已经过了一个钟头,李部长还没有来,我找了很长时间没有找到,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这时,我没有太在意。我问:是不是熬夜了?是不是总理有事把他找去了?”我让郑爱萍到李震家里、五号楼找一找,向外面打电话问一问。
过了一会儿,郑又来电话说,还是没有找到。他显得有些焦急。这时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要郑爱萍立即通知在家的核心小组成员到五号楼会议室碰头。当时我是管常务的副部长。
我来到五号楼下西侧会议室。施义之、曾威、张其瑞也陆续到了,于桑在部外开会赶了回来。
郑爱萍向核心小组成员汇报了上班后四处寻找不到李震的经过。我觉得奇怪,李震能到哪里去了呢?大家继续寻找。人们分成几路在院子里搜寻。我和曾威在五号楼,找遍了楼下楼上和三层的小阁楼,都没有结果。
这时,空气紧张起来,我们在五号楼的会议室里,惶惶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于桑向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报告找不到李震的情况。
在忙乱一阵以后,有人发现李震的夹大衣在五号楼的过厅里挂着,大家觉得更奇怪了。
将近上午11点钟的时候,有人慌张地跑来报告,说有两个工人查找到地下热力管道二三十米的深处,大约在李震房前东北侧那个小亭子的地下方向,发现李震吊死在管道上。这时候,大家非常震惊,我也愕然。于桑又向总理办公室作了电话报告。
于桑接到周总理的电话指示:不要动现场,保护起来,不要光由公安部的勘查现场的人员下去,要立即请北京、天津的专家一块来勘查。并且要卫戍区立即派一个加强连,加强警戒,把所有地下管道口都布哨封闭。
总理的指示,非常精确。这样使李震自杀的现场保护得完好无损,又由几个部外单位的专家共同进行勘查,写出了材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报告。这一切,形成了施义之等人力图把自杀搞成他杀的不可逾越的屏障。
根据中央的指示,施义之、曾威等人组织调查组,进行李震的死因调查。
头两天,核心小组在一起听汇报,分析研究情况。后来,我感觉到异常了。施义之、曾威、张其瑞明显地把我和于桑撂在一旁,有些活动不通知我参加,甚至连核心小组向周总理的汇报,也不通知我去。因此以后的情况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李震尸体搬到了大礼堂时,施义之提议核心小组成员去看看。有一个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汉臣。刘汉臣主管刑事侦查。我们到大礼堂的楼下小休息室时,刘汉臣在一旁站着,没有说话。
李震尸体平放在两张小桌子上面,用一块白布蒙着,头露在外面。我看了看,能清楚看出李震的舌头从侧面伸出,舌尖被牙齿咬着,这表明是上吊自杀身死的。面对这种情况,我的心情不好,也很纳闷。事后造反派造谣诬陷我当时表现幸灾乐祸,这纯属胡说八道和蓄意陷害。
可是,在李震上吊自杀的事实面前,施义之等人却反常地坚持说李震不可能自杀,肯定是被谋杀的,要侦破。
但我没有料到,施义之的疑心竟是冲着我来的。
事隔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公安部老法医赵海波在看了李震遗体后曾脱口说出是自杀,还有外省来的法医也反映是自杀,他们因此受到审查。从此没人再提“自杀”这两个字了。
在李震自杀以后的四天里,五号楼被怀疑是“出事”的地方。周总理指示封闭五号楼。我们部领导人集中转移到东大厅办公和活动。
23日、24日、25日这三天,施义之让一些人排队、研究谋杀的可疑线索、对象,回忆李震当天的活动,逐人逐次排查接触过李震的人,以及来往的电话等,寻找谋杀的可能线索。由于重点在寻找他杀依据,情况被人为地搞复杂了,也弄混乱了。
但同时,自杀的事实也进一步显露出来。
办案人员从李震穿的上衣口袋里掏出几十片“速可眠”,在地下管道里上吊的地方,又捡到掉在地上的若干片“速可眠”,加上解剖时从胃里取出的30多片,正好100片。
公安部机关卫生所反映,几天前,李震亲自向卫生所小杨要过一瓶100片的“速可眠”。
在李震办公室里,发现有把剪刀放在桌面上,窗户上的尼龙绳被剪断了。刑事技术人员检验,这个剪刀和尼龙绳子被剪断的切口是吻合的,黏附着同样的纤维丝。而且桌面上、剪刀上都只留有李震的指纹。地下管道里留下的指纹、鞋印,也只是李震一个人的。
上述重要证据表明,李震是自杀,不是他杀。可是,施义之一口咬定“李部长不会自杀”,并声称,“不破此案不瞑目”。
我亲历了“突然袭击”
24日,我清楚地感觉到被施义之等人怀疑上了。
25日晚上,我被告知到中央开会。这时已将近午夜12点,小雨霏霏。
我们从公安部东大厅出来,曾威和于桑坐一辆车,施义之和我坐另一辆车,一前一后,相隔只有几步,都披着军大衣,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入。往常,参加中央的会议是朝东往福建厅走的。这次相反,我们被领着朝西往新疆厅方向走去。突然间,埋伏在两厢的人冲出来抓住于桑,于桑回头看我,披着的军大衣掉落在地上。我还没反应过来,从两旁出来的人已把我架住了。我亲历了“突然袭击”的刹那感受。
我被带到西大厅的东北角,进行搜身。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进来向我宣布:“中央决定对你保护审查。”只说了这一句话。我没有任何对抗的动作。我即时反应说:“好嘛”。我心里明白,这个逮捕的决定是经过中央作出的。不过,这下搞错了,完全搞错了。我没有想象到中央会采取这样严厉的方式来审查。
这个时候已是10月26日凌晨。我被架着进入电梯下到大会堂西北门的院子里。这里已有北京卫戍区的吉普车在等着。我上了车,两旁坐着监护人员,车子朝着南长街方向开去。我料到将被送到安定门外交通干校那个监护所去,而不是秦城监狱。这条路线我很熟悉,我曾几次到这个交通干校的监护场所审问过人。到秦城监狱的路线我也很熟悉。
我被关进安定门外交通干校的北京卫戍区监护所单人牢房里。这个被改做监狱的交通干校,院子里有三座两层小楼。关我的是北楼二层靠西头的一间。牢房的代号是“251”。这个房间曾经关过王恩茂,墙壁上留存有造反派乱写乱画打倒谁谁的字迹。后来,我在中楼和南楼都关过一段时间。
事后知道,在我被拘押期间,施义之等人发动公安部机关开展对我的大规模揭发批判,逼迫很多人发言表态,又派人四处调查,讯问我的亲属,我的一些同事、战友也受到审查,还查到了我的出生地广东省梅县。这个冤错案件,沾染着浓浓的“文化大革命”色彩。
事后知道,1973年10月23日、25日,中央政治局接见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时,周总理曾指出,李震之死存在着自杀和他杀两种可能。但这两次会都没让我参加。
施义之等人始终坚持李震是被谋杀的。事后知道,1973年11月11日,正在中央“读书班”学习的祝家耀(十届中央委员)、杨贵(十届中央候补委员)被派到公安部工作,任核心小组成员。祝家耀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是一起造反起家的。祝家耀进驻公安部以后,完全同施义之站在一起,武断认定,“公安部的阶级斗争白热化”。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公安部机关一度被搞得乌烟瘴气。
施义之还把李震自杀同所谓“算旧账”联系在一起。他们以查“于、刘的问题”为名,先后调阅了所谓“算旧账”和批判“算旧账”时的一些同志的发言,查阅了我在第十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和第七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有关文件,调查了我在检查“算旧账”时找一些老局长座谈的情况,以及“五七”战校从黑龙江迁回秦城的情况等。
后来,从祝家耀保存的材料中清查出一份名单,因为李震自杀而被公开和秘密审查的干部职工有133人之多,其中局级以上干部29人,处长级干部31人。
据我老伴王岫联回忆,我被抓走的第二天,就有人到我家里进行搜查。王岫联是“重点怀疑对象”,被叫到公安部南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轮番逼问。先是让她“交代”李震自杀前后几天我的活动。那些人没有得到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便硬逼她“坦白”。
王岫联说:我怎么说,他们就是不相信,几个人轮番地逼供,最后我干脆一句话也不说了,装“哑巴”了。这一下,他们就更恼火了,认为心中有鬼,态度恶劣。但是王岫联丝毫没有害怕。她心里清楚,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过了几天,王岫联也被抓走了。王岫联和大女儿刘红林分别被监护看管在北京卫戍区的招待所里,失去了自由。
我的二女儿刘红燕和儿子刘红森在福建当兵,幸而得到老战友北京军区副政委张南生、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卓雄、福州军区副政委佘积德等人的保护而未被拘捕审查;大女儿刘红林在天津工学院上学,被“保护审查”后又不分配工作;只有12岁的小儿子刘红宇在家,得到老保姆邵玉君勇敢的照顾。
李震自杀,证据确凿
1973年10月30日至31日,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吴阶平主持下,一批著名专科医生和法医,对李震尸体进行解剖检查。1973年11月9日凌晨3时,由参加李震尸体检验的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林钧才等签署写出了向中央的书面报告,排除李震死于他杀。
当时参加李震尸体检验的人员有:刘汉臣(北京市公安局);吴阶平(中国医学科学院);李延吉(法医,上海市公安局);陈仲芝(法医,广东省公安局);吴声屯(法医,天津市公安局);韩木林(法医,北京市公安局);赵海波(法医,公安部);李伯龄(法医,公安部);朱燕(检验师,北京药品生物制品检验所);张孝骞(内科医生,首都医院);陈敏章(内科医生,首都医院);王直中(耳鼻喉科医生,首都医院);韩宗琦(口腔科医生,北京医院);马正中(病理科医生,北京医院);林钧才(北京医院);吴蔚然(北京医院);董炳琨(北京医院)。
与此同时,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四个省、市公安局参加现场勘查的技术人员,对现场痕迹进行了检验,于1974年2月2日上报中央《关于李震死亡案件现场痕迹物证检验工作情况报告》,也排除他杀。
1977年3月,公安部党组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报告中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1977年12月,公安部在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向到会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和公安局长以及公安部全体干部传达了中央批准的公安部党组关于李震自杀问题的报告。但是,都没有向我个人通告一下。我认为,我是无辜而受株连的人,无论在法律上和道义上,不告诉我都是有缺失的,不对的。
我回忆,被关进交通干校监护所的第二天,来了两个不认识的人要我写材料。我花了四天时间,细致地回忆了李震自杀前两个月,特别是前一个星期我从天津回到北京这一段的情况。我把自己的活动逐日写成详细材料,按照正常手续要求监管人员替我报送周总理和党中央。我申明是清白的,与李震之死毫无关系。
从此,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话,没有任何人提问过我。我与外界的关系完全被隔绝了,只看见五个哨兵专门看管着我。
令我不解的是,自杀现场勘查得一清二楚,为什么还如临大敌地把我抓起来,长期不释放?为什么把明显的自杀搞成谋杀去侦破?
我被释放前后
坐牢的日子长了,异常苦闷,觉得中央直接过问这样一个案件,怎么也搞成这个样子。这时的心境与“文化大革命”中受批斗完全不一样。坐单人牢房心里十分受压抑。蹲在小屋里,五个月不放风,不洗澡,不换衣,不说话,不准关灯睡觉,不准脸朝墙,不准自由上厕所等等,身心受到极大折磨、刺激和践踏。
冬天暖气不热,西北风飕飕地从门缝中钻进来。我要了两床被子,再把棉大衣都盖上了。
因为休息不好,特别是睡不好觉而神经衰弱、耳鸣头晕,以致一度出现幻听、幻视。
1974年,我57岁。每天在小监房里转圈,尝到了“单间牢房”“专哨监护”的滋味。大窗户封了,只能通过高高的小铁窗户,看到狭小的天空,偶尔看到一群鸽子在天空飞过。寒假期间,听到西面小学校的风琴声音,清静、寂寞、闷气。
后来,每个月可以替我买一斤点心、一卷手纸、三条光荣牌香烟。但看书不给铅笔,不让写字,我利用火柴棍碳化以后当笔,在只给看的《毛泽东选集》上做了一些眉批,也偶尔写了一点儿感想。释放回家以后,岫联看到这些东西,怕又被搜查去当做靶子,擦了一部分。
大概在1974年4月前后,我感觉隔壁房间晚上有声音,有人说话,影响我休息。我曾怀疑隔壁房间有人捣鬼,给我安了窃听器或其他音响。
1975年,我释放出来以后,经过北京医院检查,认定我是高度的神经衰弱,有假性幻听。在我一生里,这是受刺激最大的一次,长时间关进单人牢房,无处说话,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折磨。
历史往往捉弄人。五年之后,1980年,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侦查预审,施义之、郭玉峰都是被审查对象。我曾到秦城监狱提问过郭玉峰。郭玉峰和施义之当年都曾神气一时。我明白地告诉郭玉峰:必须老实交代问题。我们的做法完全不同于“四人帮”那一套,我们绝对不搞逼供信。
回忆1973年10月26日,我被拘捕的第二天,老伴王岫联和大女儿红林也相继被隔离审查。同时被拘捕审查的还有秘书莫固基,老战友、天津医学院党委书记乔国铨,侄女刘漾、林呈夫妇,刘映、王成夫妇,侄子刘耀和战友的孩子崔空防等二十多人。还有一些同志和亲属,包括在远郊区工作的大儿子刘畅也受到影响。
我的家被反复抄查,放文件的小铁柜被贴过六次封条,至少搜查过六次,连线装的《二十四史》也翻了个遍。施义之和他的后台把“自杀”当成谋杀来侦破,实在很笨又可懊。
后来得知,施义之等人在抄家时从我的公文包里搜走四样东西:一、党的核心小组关于搭配各局领导班子的名单,他们混淆黑白,认定是于、刘拟定的“黑班底”;其实是在党的核心小组会上议论干部过程中我的记录。二、一张写有“老将归位,小将回营”的便条,把这当成我的罪状;其实这也是听传达毛主席谈解放干部时我记下的,施义之等人竟把这当成了我反对提拔青年干部的证据。
三、我在“批林整风”和1937年党的核心小组会上的个人记录。
四、叶剑英副主席办公室主任王守江给我打电话的记录,传达叶帅要我告诉叶导英,接触社会关系要谨慎。施义之抄走这个便条,是不对的,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施义之又为此心虚,捏造说是从我的办公室里取走的,不是抄我家时从我的公文包里拿走的,企图倒打一耙,以此证明我是“诬告”、是“翻案”。
还有一份材料是我听传达时作的记录,有这样几句话:“派性上去的要下来,派性下去的要上来。”“智有所用,高抬贵手,笔下留情,还我财富。”这些话,我记不清楚是谁说的。但是正确的话,却也受到批判。
1975年5月,我从交通干校监护所释放出来已三个多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光明正大地请施义之转送,反映我被关押在交通干校时经常受到隔壁房间的声音干扰,导致神经衰弱,要求治病。华国锋在我写的这句话上批示:“已告施、杨同志,刘有病先治病。
此件报送总理阅批。”周总理批示:“同意先治病。交通干校的审查方法值得一查。即送小平春桥、先念、登奎同志核阅。”邓小平批示:“同意总理批示,好好查,并应如实报告。”交通干校的审查方法的确是有问题的。后来,另外一个专案组的负责人巨光和潘汉斌告诉我,他们的审查对象也反映有声音干扰。经查实,在关我的隔壁房间的人经批准确实使用收音机。
1975年8月,我又写了第二封信,还是请施义之转报周总理。这封信反映施义之抄走了叶剑英办公室给我打电话的记录,我认定,这种做法不对。李震自杀后,我的侄女还被追查我和叶剑英、邓小平的来往关系,逼她们写揭发材料。而后又心虚把它烧掉了。施义之等人指责我写第二封信的“矛头是指向华国锋”、“分裂党中央”的。这实在可笑,乱扣帽子,根本谈不上把矛头指向中央、“分裂中央”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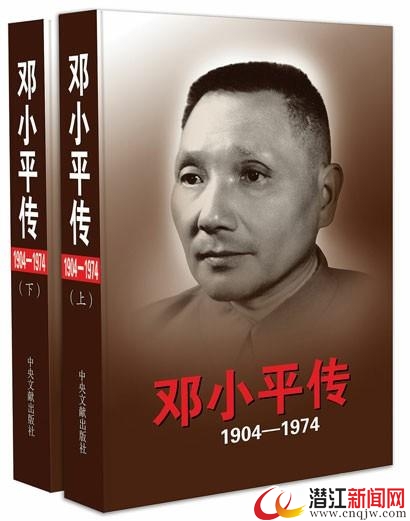
![炎黄春秋朱永嘉 [转贴]炎黄春秋:上海“文革”期间的军政关系 【猫眼看人】](https://pic.bilezu.com/upload/e/45/e45ce45ee0e23555ac1f9d37e225a6e4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