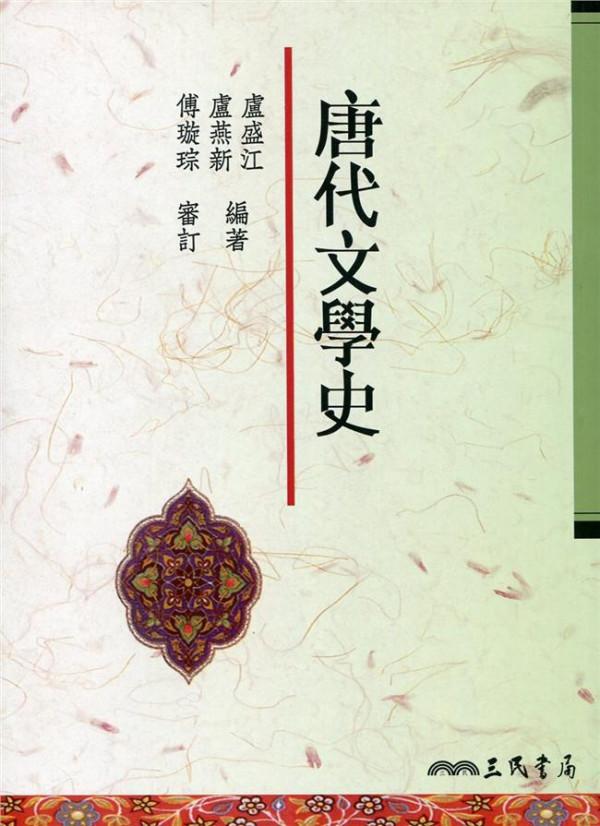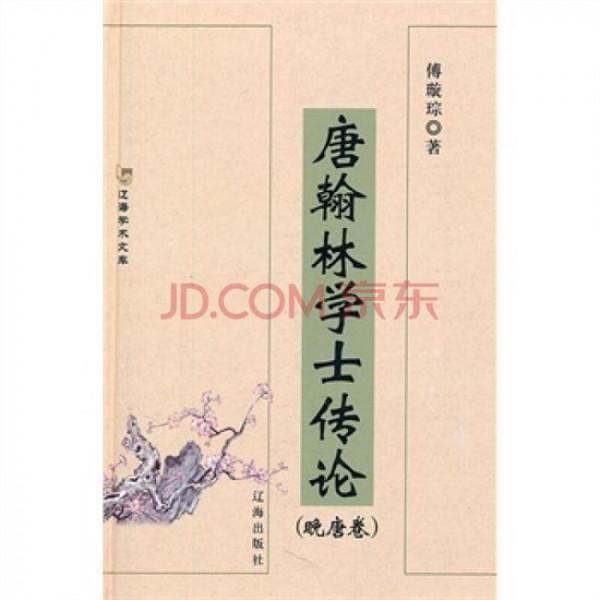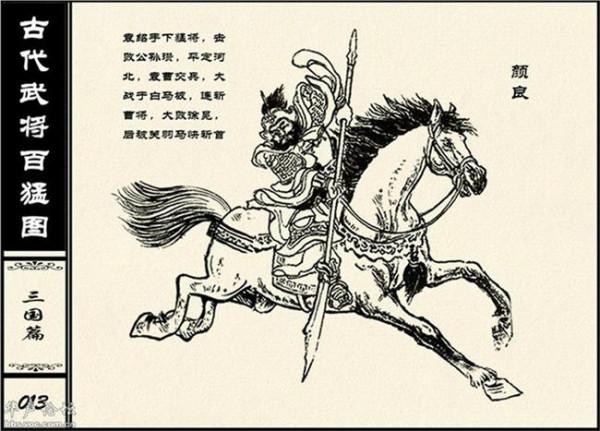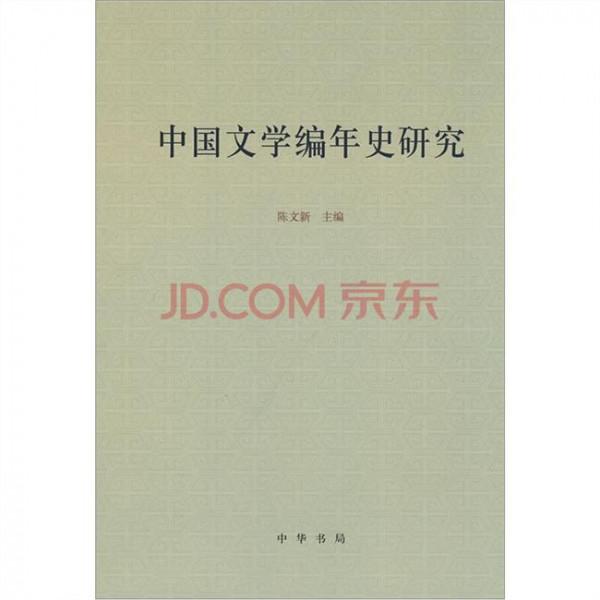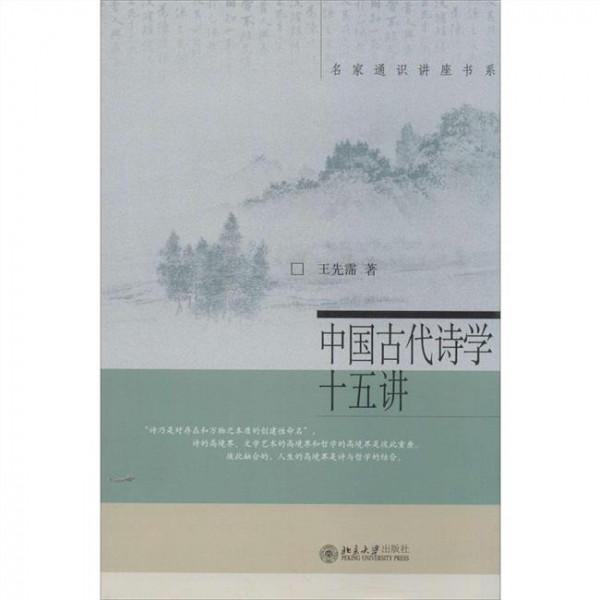陈尚君傅璇琮 【名家解读古代文学】傅璇琮:陈尚君教授与唐代文学研究
陈尚君同志于1977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次年秋,以专业第一、总分第二被破格录取为研究生,自此即受到年已届八十三高龄,仍担任系主任的朱东润先生亲自指导。
朱先生颇欣赏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到晚年更寄予厚望,认为尚君同志将给复旦带来光荣。朱东润先生对青年学子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能对尚君同志作如此的赞许,确实表现出极为难得的伯乐风范与大家气度。窃以为,以尚君同志十余年来在唐代文学基础研究也就是文献资料考证上所作出的业绩与贡献,他也必将为中国的唐代文学研究带来光荣。
我这样说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尚君同志已经发表和出版的论著以及这本论文集,是最好的证明。这本论文集列入“唐研究基金会丛书”,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葛晓音教授与我推荐的,很快得到学术委员的认同。之所以推荐,也是葛晓音教授提出的。
葛教授的重点是治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着重于文学发展趋势的把握和诗歌审美流程的探索,极有新见,但是她很看重尚君同志的文献资料考证工作,认为他的著作凡是治唐代文学的,都应必备。我想这是能代表我们唐代文学研究界的共同认识的。
1982年,中华书局曾汇集王重民、孙望、童养年三位先生有关《全唐诗》补辑的著作,出版《全唐诗外编》一书。出版以后,随着唐诗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陆续发现《外编》收录佚诗仍未完备,且考订亦有未确之处,需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校订和续补。
这项工作就由尚君同志毅然承担起来。他一方面对前人已做的唐诗汇录辑佚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梳理,另一方面对唐人著述总目和今存唐宋典籍,作全面的调查。他所查阅的书,其面之广确实是惊人的,不只是唐人著述,凡宋元以来的总集、金石、方志、谱牒、说部,以及敦煌文献、佛道二藏、域外汉籍,都巨细无遗地加以搜辑,据他自己估计,先后检书超过五千种,仅方志就有二千多种。
这种竭泽而渔式的网罗,其收获即为辑得逸诗四千六百多首(其中新见作者八百多人),相当于前此各家所得总和之两倍多。
与此同时,又对《外编》作不少校订工作,即(一)覆校原书,改正误字;(二)补引书证,提供较早出处;(三)考订作者事迹,补原辑遗缺;(四)删芟误收唐前后人诗以及与《全唐诗》重出之诗。这样,就于1992年以《全唐诗补编》的名义由中华书局出版,可以说是清代中期以后唐诗辑佚的最大成果。
《全唐诗补编》完成后,接着就作《全唐文补编》。从1986年着手,至1991年初步完成(后又陆续修订),其间查阅了不少正史、政书、类书、地志、石刻等书。在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之外,又录得唐人遗文六千二百多篇,编为一百六十卷,相当于前人所得唐文四分之一强,且其中有大量极珍贵而稀见的文献,对唐代各方面的研究有很大参考价值。
中华书局于八十年代前期曾计划组织一套多卷本《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其中唐五代卷由厦门大学周祖譔教授主编。尚君同志于此书承担了不少过去无可考、难于找到书证的条目,出力多,用功深。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如女诗人姚月华,《全唐诗》收其诗六首。
尚君同志考出其《怨诗寄杨达》二首出《才调集》卷十,《怨诗效徐淑体》出《乐府诗集》卷四十二,而另外三首诗,《有期不至》为白居易作,《楚妃怨》为张籍作,另一首亦疑为他人之诗混入。
又如李愿条,令狐楚《御览诗》收其诗二首,《全唐诗》同。中唐时另有一李愿,为名将李晟子,元和、长庆间累历节度使。我与许逸民同志等合编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误将此二人合为一人。尚君同志所写的这一条,引用韩愈于贞元十七年作《送李愿归盘谷序》,及元和时韩愈、卢汀所赠诗,证实此李愿与令狐楚同时,当是《御览诗》所载二诗之作者,与李晟之子非同一人,同时又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考出另有一李愿。
类似的情况,如唐末有二陈峤,一未仕,一仕闽为殿中侍御史。
这在《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已加区分,但尚君同志所写此条之可贵处,为找出更早出处加以印实,前者据《南部新书》,后者据黄滔之《黄御史公集》卷六《司直陈公墓志铭》与《祭陈侍御》二文。
又如房由,为唐初兵部郎中房德懋之玄孙,天宝十三载登进士第,与戴叔伦、郎士元为友。尚君同志所记其事迹,出处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郎官石柱题名考》、《千唐志斋藏志》之《卢自省墓志》,并考《全唐诗》卷二O九收其诗一卷,但沿《唐诗纪事》之误署作房白。
这一点在以往《唐诗纪事》研究者中都未曾指出过。我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举这些例子,意在说明,辞典系成于众手,个人的独特成就往往不易见出。尚君同志在这里已不仅仅是写辞条,而是在史实的梳理、考析上,作出一篇篇浓缩的学术笔记,这在辞典的编纂上是极为少见的。
我于八十年代中期曾邀约二十多位研究者,共同进行《唐才子传》的校勘和笺证工作。从笺证的内容说,要求做到这样三点:(一)探索材料出处;(二)纠正史实错误;(三)补考原书未备的重要事迹。1987年至1990年陆续印出四册《唐才子传校笺》。
出版后的反应还是比较好的,但也发现一定数量的错误和疏漏。于是我就请尚君和陶敏同志作一次全面的检核,结果就是他们两位写成的三十余万字补正,作为《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出版。正如蒋寅同志在《文献整理与唐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一文所说,第五册“补正”,“最大限度地展示了陶、陈两位多年积累的资料和考订成果”,“展示了唐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水平”,并说“他们的工作不仅使《校笺》的资料进一步完备,也使诗人生平事迹的考订更臻精密”(《书品》1996年第3期)。
尚君同志在文献考订上不限于文学,还做史学方面的工作,譬如他为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作了补订,补录唐代科举人事七百多则,相当于徐松原书的五分之一。这是近代所作订补工作份量最重的一种(此文已在《唐代文学研究》第四辑上刊出)。
又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唐人别集505家,537部。尚君同志又作《新唐书艺文志补——集部别集类》,根据史书、方志、笔记、唐宋人文集等记载,新补406家,446部,所补约当原来的六分之五。此外,他还计划从事于《旧五代史》的重辑,这将比陈垣先生之作有更大的进展。
3从近十余年来尚君同志的著述,来看这本论文集,则对他的治学路数与研究风格当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觉得,尚君同志治学,一是勤而博,一是细而精,这两者往往是结合的。就是说,要搞一个专题,总要在这一专题所涉及的资料范围内,尽可能求全求实,同时在资料搜辑考辨的过程中,细心发现前人未曾注意的问题,抉隐发微,提出新见。我认为这样做学问,特别是现在,是很值得使人思考的。
譬如本书中的《全唐诗误收诗考》,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1985年中华书局所编的《文史》第二十四辑。在这之前编辑部曾将此稿送我审阅,我一看就觉此文出手不凡,在当时研究清编《全唐诗》,这是最有份量的一篇。关于《全唐诗》误收诗,宋代陈振孙,明代胡震亨,清乾隆时《四库提要》,清末刘师培,以及当代学者钱鍾书先生等,都有所提及,但对误收情况作全面清理的,只有这一篇文章。
此文收入本书时作了增订,近五万字,考出唐以前人所作,宋及宋以后人所作,而混入《全唐诗》的,诗七百八十二首,又句五十三,词三十四首,所涉作者一百十五人,全文引书逾三百种,可见用力之勤。
又唐人编选的诗歌总集,今存者约十余种,尚君同志在《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中,广泛收集材料,力图列出全部唐人所编诗歌总集目录,并对各书的名称、卷数、编者、编纂过程及著录存佚情况予以辑录考订,共考出137种,较今人已论及者多出八十余种,在各集考订中,并提供大量今人未曾注意的材料。
又如唐开元、天宝时人殷璠的《丹阳集》,即为唐人选唐诗的一种,其书久已亡佚,《殷璠<丹阳集>辑考》则从宋代的《吟窗杂录》等书中辑录殷璠自序、诗评,并考证所收十八位诗人的生平事迹,使我们对殷璠于《河岳英灵集》以外另一部已亡佚的诗选了解到大致面貌。
近年我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即请尚君同志将此重辑本列入《新编》中。另外,《唐诗人占籍考》是一篇颇有新意之文,文中根据现有研究成果,作了唐代诗人的地域分布及唐前后期变化的统计,对探索唐代文化地理极有参考意义。这一题目是可以作为一部专著来写的。
以上是这本论文集中以勤而博见长的(当然其他篇还有,如考劳格读《全唐文》札记等,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我想再提一下以下几篇以细而精见长的,可能更引人入胜。
本书中《杜甫为郎离蜀考》、《杜甫离蜀后之行止原因新考》两篇,考察杜甫后期的行止、思想,及诗歌风格,可以说是发前人所未发,是建国以来研究杜甫生平创作最值得玩味之文。过去一般认为杜甫在成都依严武幕,严武奏请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后严武卒,杜甫无所依靠,即离蜀东下。
这几乎已成为定论。尚君同志经过文献资料对比、分析,认为在杜甫于永泰元年离开成都草堂携家东下时,严武尚未去世;杜甫只是在途中才闻严武死讯,因此他之离蜀与严武之卒无关。
而杜甫在严武幕时仅为节度参谋,并不带郎职,只是在他离幕后,严武奏请朝廷任命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并召他赴京。杜甫是带着返回长安、效忠朝廷之心离蜀东下的。考出这一点,对了解杜甫后期在夔州、江陵、湘中的思想与创作风格,十分重要,即使人换一新的视角。
尚君同志对杜甫离蜀前后的诗篇作了细心考察,同时充分吸收史学研究成果,重新审视岑仲勉等史学家的看法,提出新见,对一般人容易忽略的检校郎官之为虚衔究竟始于何时作了踏实的考析,这对唐代的职官研究也是有助益的。
尚君同志确是很会做翻案文章,这些文章使人读了自然产生一种会心之感。如《全唐诗》收有张碧诗二十首,过去一向认为张碧乃中唐德宗贞元时人,因孟郊有《读张碧集》诗,是一铁证。本书中《张碧生活时代考》,即从此诗着手,考出此诗实为五代马楚时徐仲雅作,如此,则张碧就应是唐末或五代时人。
这看起来并不算大问题,但能考出诗非孟郊作,推倒过去公认的说法,这确是读书得间之功。又如《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一文,也很有特色,文中对温庭筠一首有名长诗《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考出此李仆射并非李德裕,而应是李绅,订正了夏承焘先生《温飞卿系年》的权威之说,因而得能重新考订温之生年,并进而考定其漫游南方和从军出塞之时间与路线,分析其在开成、会昌间与当时政治斗争的关系。
当然,这几年来最有影响之作是对《二十四诗品》的辨析。这应当说是尚君同志近年来最有力度的考证文章,引起唐诗学界和文论学界的极大震动。尚君同志在未写成文时曾与我口头谈起过。我本能地感到这确是石破天惊之说。我是赞同他的看法的。
我觉得这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主要解决了两个大问题,一是全面考察了唐宋元明长时期内对《二十四诗品》记载之有无,并有力检出元明间人所作《诗家一指·二十四品》(尚君同志初考为景泰、天顺间怀悦作,北京大学张健同志认为有可能出于元代虞集);二是确证苏轼的那段话与《诗品》无关,仅是指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列举其所作的两句一韵的二十四个例子。
我觉得,《二十四诗品》究竟是否司空图所作,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我们应从材料本身在历史上存在的客观事实出发,而不应以所谓诗歌理论历史发展的主观推断为据。
过去往往对史料考证不够重视,认为考证只不过是限于文献资料本身,无关宏旨。不说别的,仅从上述尚君同志的几篇考证文章,就可看出,资料的考证往往与作家作品的整个思想发展,与某一时期文艺观念的演变,有着密不可分的交叉联系。而考证,从治学路数来说,并非只是所谓饾饤之学,实是一种细密、清晰的理性思考,没有对某一学科有整体的把握和考察,没有具备一种综合的科学思维方式,是根本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工作程序的。
综观尚君同志的治学路数,我觉得有三点值得提出:一、熟练掌握目录学,对唐宋典籍的存佚状况可说已烂熟于心,据此即能较自如地工作,对所涉课题作竭泽而渔式的网罗,力争全面掌握史料。二、有较明确的史源意识,在研究中能做到溯本寻源,有理有据,追求博证而不一味博,力求提出新见而又“实事求是,多闻阙疑”(清劳格语),充分尊重前人和今人已有之作。
三、治学兴趣广泛,虽专以考证为主,但对唐代的各种人事典籍,对唐前和宋代的典籍,都有兴趣,不局限于少数大家,也不仅局限于文学方面(这点我特有体会,每次与他见面,所谈多涉古今中外,不少佛学和医书的知识我多是从他得来的),这样就更能发现为人忽略的问题,而又能从多方面加以论证。
4尚君同志自七十年代末进入复旦大学学习、工作已有二十年,他得益于复旦师友的治学风尚当是不小的。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后,复旦中文系集中了不少有个性、有成就的名学者,其中有好几位的著作我很早就拜读。我念中学时即读过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
五十年代前期在清华、北大上学时,读过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赵景深先生的几部戏曲、小说论著,后来又读过王欣夫先生关于文献目录学的书,王运熙先生的《六朝乐府与民歌》,蒋天枢先生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陈子展先生关于《诗经》、楚辞的直解。
以大学中文系而言,我读复旦学者的书算是最多的了。我在清华中文系念过一年,深感清华自二、三十年代所形成的学风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独特的地位与贡献,但可惜1952年院系调整后即流散了。
而此时复旦则处于兴盛期,这一点就当时南北几所有名的大学来说,是很突出的。我不敢轻易对复旦学风有所评议,不过我觉得复旦中文系几位前辈学者,学术个性都极鲜明,不依袭旧说;议论通达,力争创新,而又重实证,重传统,各抒己见,但又能和衷相济,兼容并蓄。
对年青学子,要求极严,而又鼓励他们读书得间,不囿师说。因此我觉得,复旦学风确使人有宽松的学术环境与严格的学术准则之感。我想这对尚君同志的治学是有很大影响的。
我自八十年代中期认识尚君同志,即不时见面、通信,还合作过一些项目,不敢说知之深,只觉得有一种学术之缘。但我不敢说能把握他的治学路数,我只能谈谈个人的一些感想。谨求教于唐代文学研究界与尚君同志本人。
[编者附记]:本文原系作者为陈尚君教授的新著《唐代文学丛考》所写的序,本刊发表时,对个别文字略有删节,并对标题作了改动。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