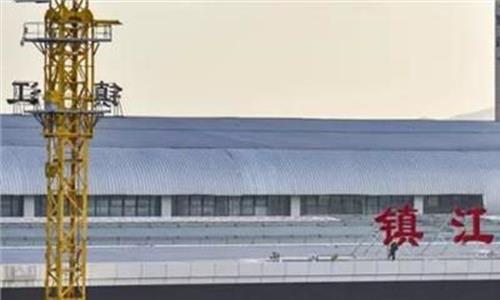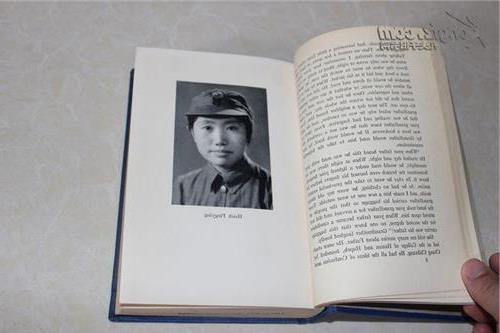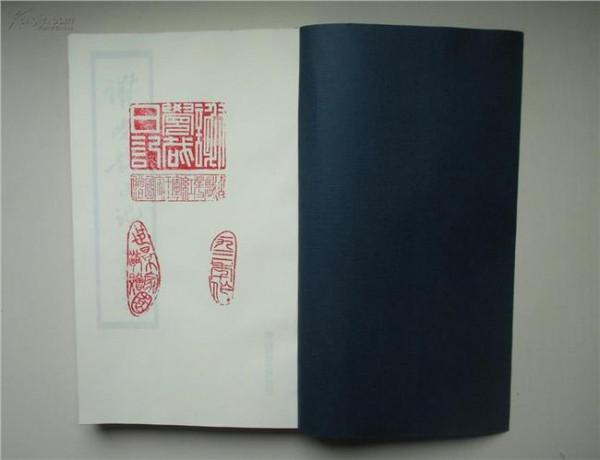谢泳《传记文学》 谢泳:“传记文学”和“文史资料”
我至今清晰记得十几年前在太原高增德先生家里第一次见到完整台湾《传记文学》合订本时的情景,可以说是亦喜亦惊;喜的是台湾传记文学的丰富和水准,达到了很高程度;惊的是如此规模的学术建设,竟是私人出版机构完成的。把这些杂志合订本细细看过后,当时也曾起过建议内地出版社设法引进的动议,但没有一次成功。这
次看到成批引进的内地版《传记文学》杂志社的部分产品,感到这实在是对学术界和读者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虽然目前引进的几种传记,多数作过删节,甚至删节较多,但在目前情况,这样的处理,读者会非常理解。
传记文学的发达水平,实质是一个地方开放程度的体现,严格说来,传记文学的繁荣建立在开放这个前提下。中国文化传统中史传文学的发达程度,其实和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相关,所谓“董狐之笔”,这是良史产生的基本条件。
台湾《传记文学》追求的理想,就“传记文学”这个概念本身来说,它重在“传记”,所谓“文学”只是对“传记”文笔的一种要求。我个人理解,台湾《传记文学》的传统中,是“传记”第一,“文学”第二,前者决定后者,后者依赖前者存在。
这种“传记文学”观念和中国内地流行的“传记文学”明显不同,从学科角度观察,台湾《传记文学》在史学领域,而内地的“传记文学”一般放在文学领域判断比较恰当。台湾《传记文学》类同于中国内地的“文史资料”,虽然因为两地政治制度的差异,在总体上体现出的风格还不同,但在史学层面,它们是一个类型的史料。
当年唐德刚评价办《传记文学》杂志的刘绍唐时曾说,内地编辑的政协“文史资料”就相当于台湾的《传记文学》,这个评价大体是不错的。
“文史资料”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目前还没有人特别加以研究,其实它是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以特殊的方式保存了“民国历史”,在当时历史处境中的回忆者虽然可能因环境限制,在真实程度上不好和台湾《传记文学》对等比较,但两种史料互相比较阅读已成为“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方法,这个以政治任务形式完成的学术工作,由于它的系统和连续性,事实上成为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学术工作。
而真正喜欢读书的人,在当年就把“文史资料”作为了解历史真相的一个主要方向,原来《读书》杂志的主编沈昌文在他的回忆中就反复强调过“文史资料”对他的影响,那个时代留下来的、今天还作为研究和一般阅读的书很少,但“文史资料”是少有的例外,在这一点上,它和台湾《传记文学》获得了同样的命运,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1959年4月,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是周恩来。在一次招待60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周恩来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较大的时期,对这一段特殊时期,周恩来给政协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征集文史资料。“文史资料”的编辑,不同于党史、国史和地方史,它是通过统一战线和政协渠道,征集和出版“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提供别人不太重视或不大了解的许多内容,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文史资料”工作是在周恩来倡导下开展起来的。
周恩来提出,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完整地记载下来。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当时“文史资料”的主要撰写者,是各地的政协委员。
那时的政协委员,大多是中国各界名流、社会贤达,他们当中既有军政界的名人,也有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很多人在中国不同时期的政治、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一些人更是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们以当事人、亲历者的身份而写作的回忆文章,可以匡正传统正史的缺失和谬误,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政协“文史资料”的出版,不但在中国获得了成功,在外国也有重要影响。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和欧洲的著名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所中,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资料。政协“文史资料”比台湾《传记文学》的一个明显长处是它的广度,现在县级以上的政协都编辑出版有“文史资料”,行政级别越靠上越完善。
省级以上的政协“文史资料”都比较成系统具规模,而县级“文史资料”,因为靠近地方,有些情况为外人所不知,不能不给予特别注意。
资料使用的一个原则是,越靠近研究对象的史料,一般说来也越丰富越比较可靠。现在因为有了李永璞编《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五十二种文史资料篇目分类索引》(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和《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全46卷,附总目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研究者可方便使用“文史资料”,台湾有《传记文学》,内地有“文史资料”,这是史学界可以引为自豪的一件事。
无论《传记文学》还是“文史资料”,都非常注重人物传记的选择,就这个问题的一般阅读感受而言,我以为《传记文学》的传统值得我们借鉴,我想这也是黄山书社乐于引进“传记文学丛书”的一个理由,这也是一种独特的学术眼光,我认同他们的选择。从个人阅读感受来说,我判断传记在学术研究中的原则是:
一、先西后东,先旧后新。这里的“西”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所以可以把香港和台湾包括进来。同样的传记,我要先读西方的,先读1949年前的。
二、自传尤先,他传靠后。自传虽然也常有不准确的时候,但自传作为初始材料的地位不应当动摇,因为自传是我们了解传主生平的原始起点,应给予特别重视。族谱、碑传一类史料的源头一般也离不开自传。不是说自传完全可靠,而是强调自传的原初史料线索,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说法,同时人做的传记尤先,异时人做的传记靠后。
三、第一本传记尤先,此后的传记靠后。因为第一本传记通常接触的史料有初始性,特别是史料的线索有原创性,以后的传记是一个不断扩展和丰富史料的过程。第一本传记一般都很短,越写越长是传记发展的基本特点,有史料扩展的原因,但也有把简单史料放大的爱好,我的阅读经验是关注第一本传记,留意最后一本传记,用第一本和最后一本对比,大体可以了解史料扩展的脉络。
当然这不是说中间的所有传记都没有价值,而是从史料来源角度判断传记的完成过程,大体说来,传记的难易程度是递减的,第一本最难,越往后越容易。
台湾《传记文学》传统中明显优于我们的地方,是其对口述历史和自传非常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学术的基本追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内地版“传记文学”丛书先行引进的几本传记中,以自传为首选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