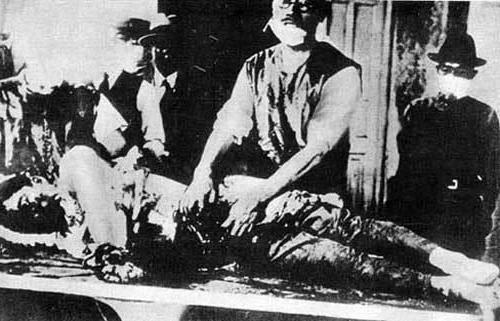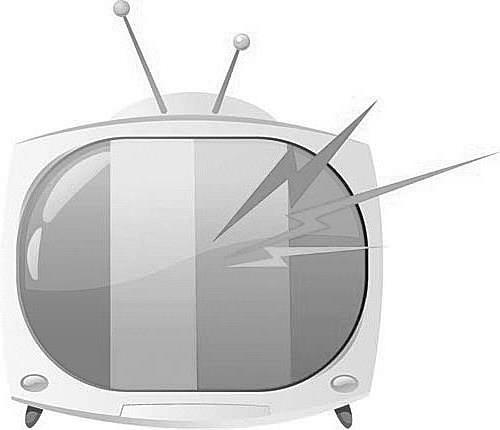二战中有多少中国人死于德国纳粹集中营?
卢永华说,由于年代久远,集中营保存的资料有的已被销毁,有的则由于多次转移而变得残缺不全。有关5名遇难中国同胞的资料也只是对他们身份和进入集中营时间的不完全记录,并没有他们如何被关进集中营以及在集中营中的生活经历等方面的情况。
因此,人们无法准确地知道,这5名中国同胞当时在集中营里经受了怎样的境遇,但根据涉及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有关描述,人们完全可以想象这5名中国同胞在这座集中营里会有怎样的悲惨经历和遭受了怎样的非人折磨。
毛特豪森集中营是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后于1938年8月开始修建的,是纳粹迫害犹太人及反法西斯人士和奴役战俘及无辜平民的重要场所。这座集中营及其附近的49座附属营地里共囚禁过20万人,其中10万多人被枪杀、毒死或折磨致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特豪森集中营被改建为纪念馆。在发现遇害者中有中国人后,中国政府决定以中国驻奥使馆的名义在这座集中营为遇难同胞立碑。2003年5月11日,毛特豪森集中营举行了中国遇难同胞纪念碑揭幕仪式。
深色的大理石纪念碑上镌刻着:“纪念在此集中营遇难的中国同胞”。
根据现存资料,在毛特豪森集中营遇难的5名中国同胞是:
唐阿汀,男,1908年5月3日生于广东。
夏津凯,性别不详,1902年10月26日生于浙江。
王楠平,性别不详,1909年8月10日生于中国某地。
阿明杰,性别不详,1910年5月9日生于中国某地。
乔治·谭,男,1903年1月3日生于柏林。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中国人
(2005年报道)60年前的今天,苏联军队走进了用带刺铁丝网围起的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救了数千名囚犯,他们目光呆滞,身体瘦弱不堪。奥斯维辛博物馆历史研究中心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设立的4年多时间里,共有130多万人被关押,其中110多万人在集中营丧生,大多数是犹太人。
此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关押的还有吉卜赛人,波兰、苏联等国的战俘以及30多个国家的平民,其中包括中国人。
可能有一个中国幸存者
奥斯维辛国家博物馆历史研究中心负责人皮珀博士昨天晚上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中发现了中国人,只有1个。
奥斯维辛国家博物馆提供的资料显示,这名幸存的中国人是男性,名叫TailaKotLuanKun,编号为181292,被捕原因不详。根据编号判断,他于1944年4月10日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直待到1945年1月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苏联军队解放。
当记者问及如何确定这名囚禁者就是中国人时,皮珀说,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后,当时的工作人员对所有获释者进行了登记,包括询问他们的国籍,这名囚禁者在登记时说自己是中国人。
皮珀还告诉记者,这名中国人在纳粹集中营被解放后,可能还多待了几天,进行了登记,但以后的去向他们就不得而知了。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新闻处官员章禾告诉记者,根据使馆掌握的信息目录,目前尚无波兰正式官方材料确认奥斯维辛集中营遇难者中有中国籍公民。
但据波兰前驻华大使齐奂武先生(ZdzislawGoralczyk)称,在遇难者名单中发现有一个名字,从拼写上判断极有可能是中国人。不过不清楚此人真实身份,究竟是中国公民抑或是已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没有明确说法。
曾长期从事二战史研究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寅达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研究过程中接触到一些材料显示德国纳粹集中营里有中国人,但人数很少。郑寅达教授告诉记者,在集中营里,管理人员通常会在囚禁者的衣服上标明国籍,例如,来自法国的囚禁者衣服上就会标上“F”,代表法国的简称,但没有发现囚禁者服装上出现代表中国的字母“C”。
这些证据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纳粹集中营里没有大批的中国人,只有零星的几个。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的中国人
(2005年)4月10日,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档案馆工作的一位女士热情接待了记者,并展示了一份从数据库中查找到的有关3名被关押中国人的有关档案材料。
此前,记者曾在集中营负责人那里得知,时至今日,在集中营能够收集到的死难者档案中,大约只有3万多人的信息,而真正的死难者人数约为5.6万。因此,不能确定其中是否有中国人。
面对由档案馆工作人员提供的3个曾经被押中国人的档案,记者希望能够了解到他们在集中营被解放后的命运如何,但遗憾的是档案中并未留存更详细的说明。
从档案资料看,这3名中国人是从其他地区转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他们当中有2人明确是政治犯,即在当时从事了反对纳粹政权的活动;另外1人被注明是遭驱逐者,但很有可能也是出于政治原因。至于是否有中国人以苏军战俘的身份被关押,则无从查证。
记者研究了3名中国人的档案材料,并根据档案纪录的姓名拼音,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和出生地等信息,分别是:WanLiLei,1897年12月25日生于中国山东,职业是锁匠和鞋匠,1943年9月19日被解押到布痕瓦尔德,1944年7月23日被转送它地,政治犯;JoTonTschau,1914年生于中国浙江,职业是厨师,1945年2月6日被解押到布痕瓦尔德,政治犯;WuChungMing,1912年12月22日生于中国浙江,职业不详,开始被关押时间不详,1943年12月13日被转送它地。
从年龄分析,这3名中国人如能躲过大屠杀并存活至今,也已是年近百岁的老人了。但考虑到当年的战争环境,他们尚在人世的可能性很小。
汉堡明日集中营里的中国人
20世纪初,从中国回来的欧洲商船渐渐多了起来,很多中国船员的妻子也跟着四处漂泊。
日子久了,有些船员的家属因为疾病或生小孩,不能再随船队出发,就暂住汉堡,在首饰街聚集。当1921年中国领事馆建立时,首饰街一带已居住了2000多名华人。当时的《汉堡晚报》称这一带为“小中国”。
百名中国人逃离纳粹魔掌
首饰街华人的生活越来越红火。
1929年10月,来自浙江宁波的老海员陈纪林,在唐人街成立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协会——“水手馆”。不过好景不长,随着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华人的噩梦开始了。
1939年前后,纳粹政权逐步加大对移民的迫害。
1944年5月初,“水手馆”陈纪林接到纳粹内线的密信,说纳粹准备向中国人动手。他紧急告知了当地华人,几日内,100多名中国人逃离唐人街。1944年5月13日,秘密警察以凭空捏造的“通敌罪”将首饰街的中国人全部逮捕,投进位于威廉斯堡的“明日集中营”。
140多名华人集中营受凌辱
虽然唐人街几乎被毁灭,但有一家名为“香港饭店”的小旅馆,至今仍延续着百年前“汉堡小中国”区的历史。
旅馆不大,只有一层楼,总共加起来不到15间客房。50多岁的女店员布基特指着墙上挂着的两任旅馆老板的照片,向人们讲述起旅馆创始人张先生的故事。
在纳粹当局于1944年展开的“中国行动”中,张先生也未能幸免。
在狱中,中国人遭受严刑拷打,部分人不堪重负和凌辱而死,但凭借坚强的毅力和不懈的抗争,张先生与其余140多人活了下来。战后,他们重获自由。然而,由于战争重创,中国人都纷纷离开了汉堡,只有张先生等少数人留了下来。
张先生重新盘下“香港饭店”,克服重重困难后,几乎以一己之力延续着唐人街的历史。战后,曾经以来往汉堡的中国旅客为主要客源的旅馆生意,因中国人的离去变得举步维艰。
张先生闯过了一道道难关,将“香港饭店”的生意坚持下来,并操持得有声有色。
1983年,张先生去世之后,这家旅馆由他的女儿接管。现在,这家“百年老店”虽然经历诸多风雨飘摇,却仍然稳稳地屹立于“小中国”区的街角,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
***元帅女儿回忆集中营里的黑暗岁月
德国法西斯6月22日向苏联发动了战争,侵略的铁蹄踏上苏联的国土,我们疗养的地方首当其冲成了沦陷区。顷刻间,远离祖国的我又失去了革命的“家”。
疗养院的孩子里,只有两个是中国孩子,我和***的儿子。他仗着男孩胆大,趁黑夜逃出了疗养院,想跑回莫斯科,可被无情的炮火炸死在途中,那年他才12岁。
这是我后来离开德国集中营,回到苏联才知道的。
没有多久,我们十多个夏令营的孩子被德国鬼子塞进闷罐火车,押往德国境内。火车整整走了一个星期,挤在臭气熏天、瘟疫蔓延、死人病人成堆的囚车里,我都麻木了,不知道哭泣,不知道害怕,也不知道死活,直到下火车,站在刺目的阳光下,看见自己的影子在晃动,这才相信自己还活着。
进入集中营前,每个人都要换掉身上所有的衣服,没收携带的物品。我眼睁睁看见一个德国鬼子拿走了父亲送给我的派克钢笔,那是父亲给我的惟一纪念。我不知哪来的胆量,悄悄将一枚列宁胸章含进嘴里,我不想再失去这个国际儿童院的纪念。这个能带来杀身之祸的举动居然躲过了德军的严格检查。
以后,这枚胸章成为我的希望,期盼有一天能从这个城狱回到祖国,回到父亲的身边。
晚上,月光照在囚室的窗棂上,我用手掌摩挲着胸章,只有这时我才能拿出来摸摸,慰藉自己:明天或许就会自由了,明天或许战争就结束了……然而,天一亮,所有的明天又化为皮鞭、做工、吃发霉的黑面包。
对明天的期盼和明天的无情整整伴随我在集中营渡过了4个寒暑。
我被押送纳粹集中营,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知道。
我的失踪,让斯大林操了不少心,在苏联红军进入战略反攻收复沦陷区时,他亲自下达指示:解放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城市,一定要找到***总司令的女儿。到收复最后一个沦陷城市也没有找到我。
大家都以为我遇难了。
谁能想到此时的我会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即使想到了,那也肯定必死无疑,因为我是中国八路军总司令的女儿,一个患病的弱女孩!
在集中营里我受尽折磨,亲眼看见许多无辜的人被屠杀,至今想起心里都颤抖。
集中营,这个和法西斯联系在一起的名称,在我面前展示了一个血腥残暴、丧失人性的场面。我亲眼目睹过法西斯屠杀手无寸铁的犹太人,看见一个个苏联战俘走进一个大房子“洗澡”后,再没有活着出来,他们被毒气活活憋死。
记得一次,德国兵当着我们一群孩子的面,打断了一个10岁的女孩的手臂,然后又让这痛哭惨叫的女孩,用自己的断臂一铣一铣为自己挖一个坟坑,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用大皮鞋将这个受尽折磨的孩子踢进坑里活活埋掉!
所有的罪名就因为她是有犹太血统的女孩。
至今,那“扑通扑通”的盖土声还常常盘旋在我耳边,只要想起来,心就阵阵地颤悸!
当时,我在法西斯眼里是个瘦弱不说话的支那女孩,他们任意嘲笑我,耍弄我。动不动就毒打我,因为我骨瘦如柴,他们都懒得动手打,用大皮鞋就可以把我踢出几米远。
那些年里,我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好的,鞭痕棍瘢,终日累累。进集中营后,我患了颈部淋巴结核,因为得不到治疗,结核块溃疡,脓血糊满了衣领,变硬的衣领又不断磨擦结核块,加剧了溃疡。
一天,一个德国兵看押,看见我脖子肿胀得厉害,就带我到集中营的医务室治疗。那个医生用深凹的蓝眼珠子注视了我一眼,那眼光充满了鄙视。
白衣天使沦为侵略者,竟比魔鬼还要恶毒三分。他抓起一把剪刀,压住我的头,上来就是一剪刀,剧烈的疼痛使得我浑身颤抖,忍不住大哭了起来,这丝毫没引起这个医生的怜悯,他在没有麻醉,没有消毒的情况下,活生生用剪刀剪开我脖子上的结核块,把脓血硬挤了出来。
犹如酷刑的治疗结束后,这个混蛋医生竟然觉得是他的恩赐,要我谢谢他。我头一扭,捂着脖子,哭着跑回牢房,身后传来一阵大笑。没有几天,结核块又开始溃疡,这次溃疡面积比上次还大,还时常受高烧的折磨。
那时德国鬼子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否则我的结局不会是一把剪刀,恐怕比那个活埋的犹太女孩更加悲惨。尽管我活到走出集中营的那一天,可我哪里还有个人形?18岁的大姑娘却还像个15岁的小孩,发育几乎停止在进集中营前的水平上。
瘦弱得皮包骨头,脖子上的淋巴结核成片的溃疡,整天淌着脓水。因为长期与世隔绝,我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整整4年没有说一句中国话,俄语讲得也不流利,德语又没有学会,我只能终日默默无语,显得我更加神秘和孤独。
至今我说话都不太流利,残酷岁月的痕迹刻得太深,太痛,以至影响了终身。(凤凰网历史频道综合新华社、西安晚报等多家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