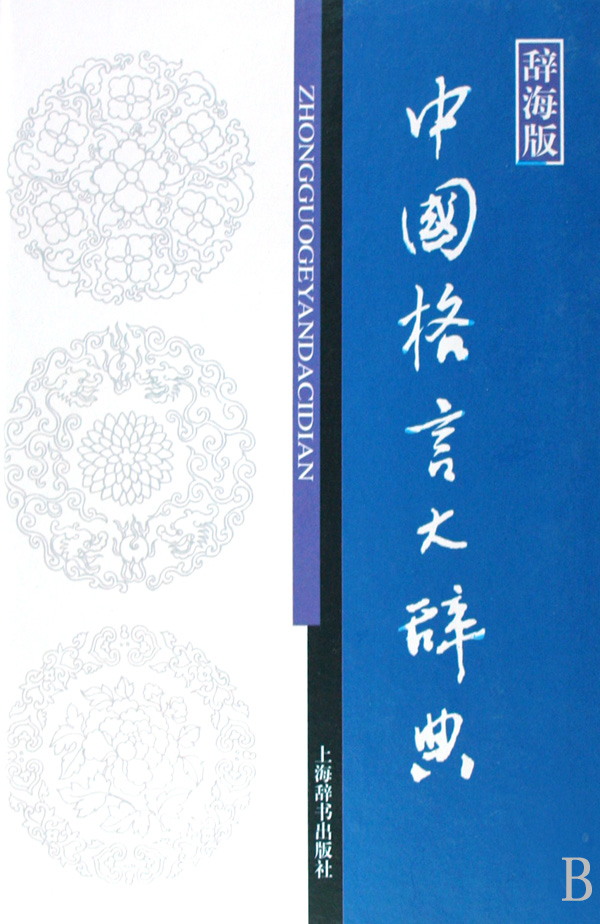任继愈季羡林 季羡林任继愈同日辞世 他们的走带走了一个时代
7月11日,当代中国两位学界泰斗季羡林、任继愈同日辞世。人们通过各种媒体表达了深切的哀悼,更传达出对两位老人的无限追慕。
季羡林一代大家纯真本色
本报记者 路艳霞 实习生 王砚文
昨天上午11时45分,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的纪念大厅中,为季羡林先生连夜搭建的灵堂向公众开放。灵堂布置得十分朴素,巨大的黑色幕布上写着“沉痛悼念季羡林先生”,幕布正中是季羡林的遗像,照片上的他身穿蓝色中山装,在春柳吹拂下笑容慈祥。
耄耋之年完成最艰巨的两部书
98岁的季羡林辞世后,各种媒体的纪念文字、纪念照片铺天盖地,这让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感慨良多,“这十余年来,一代大家钱鍾书、钟敬文、启功、林庚、王元化、任继愈、季羡林相继辞世,对学界来说,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陈平原说,这些大家大都是上世纪30年代进入大学,或者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他们的学问学贯中西,不像现在只是狭窄的追求;他们都是厚积薄发,不像现在急着出成果。
季羡林对学问始终孜孜以求,他在其自传中曾说到,平生最长最艰巨的两部书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一部是长达80万字的《糖史》,一部是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季羡林的学生、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王邦维说:“举凡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学问都纳入到他研究的范畴:从佛典语言到佛教史、印度史,从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到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从唐史、梵文的翻译到散文、序跋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的创作,他无一不精深涉猎。
”
季羡林的学生、著名学者葛维钧对恩师治学之严谨至今记忆犹新。“他对我最大的影响也是在治学的精神和态度上。他写《糖史》的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但他仍然不管严寒酷暑每天都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经常是看了半天,一个有用的资料都没有,只能怅然若失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不过,有时候发现了新的线索,又兴高采烈起来,他的喜怒哀乐通常都是跟做学问联系在一起的。”
北大中文系教授陆俭明早在1983年季羡林任中国语言协会会长时,就因担任秘书长与之结识。“他的生活很规律也很特别,每天晚上9点书房灯就灭了,凌晨3点灯又亮了,然后一直工作到早上8点,中途任何人都不能打扰,非常勤奋。”他用“一丝不苟”来形容季老治学的严谨,“每次写东西,季老总是要反复推敲、思考,写了初稿以后会不断地修改。他还有一个随身的小本,有什么东西就赶快记在本子上,很多散文就是这么来的。”
辞世前还在酝酿“大国学”
昨天下午4时30分,季老的“关门弟子”钱文忠到达灵堂,他快步走入大厅,对着遗像跪倒,连着九叩首。前天,钱文忠在其博客中说:“我原本应该在《百家讲坛》开始录制‘弟子规’,但是恩师的突然辞世,使我实在没有办法录制,只能向听众,特别是远道而来的北川同学表示歉意。”
钱文忠说,最近几个月来,季羡林独子季承一直照顾陪伴他,老人家心情非常愉快,胃口很好,仍然酷爱吃胡萝卜羊肉饺子。7月10日下午,季羡林还用毛笔题写了“臧克家故居”、“弘扬国学,世界和谐”,还为汶川广济学校题写了“抗震救灾,发扬中国优秀传统”。但是11日早上,老人觉得眼皮无力,感觉不好,301医院的医务人员进行了1个小时的全力抢救,最终回天无力。
据钱文忠介绍,作为一名学者,季羡林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他近来正在酝酿提出“大国学”的概念,他认为,“大国学”应该包括56个民族的文化财富,还应包括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的文化成果。不仅如此,他还高度关注民间办学,他授权一家著名的民办大学筹备了“大国学研究院”,并且建议民办大学也要办人文通识教育中心,该校原本决定在8月份揭牌。
幽默快乐始终感染身边人
中国书店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刘晓晖管季羡林叫“长寿眉毛老爷爷”,每次去301医院看望,她一叫“长寿眉毛老爷爷”,季羡林总会面带羞涩的微笑,捋一下眉毛,童真的表情让刘晓晖回想起来又温暖,又难过。“没想到季老的《季羡林说国学》重印稿费还没来得及交给他,他就走了。”
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刘晓晖前后编辑了季羡林的6本书:《季羡林说国学》《季羡林说和谐人生》《季羡林说自己》《季羡林说写作》《季羡林:读书有用》《季羡林禅心佛语》。因为工作的关系,她和季羡林有不少交往。
季羡林住在301医院已有好几年,别看老人家蔫蔫的,他突然冒出的幽默不知令多少人快乐不已。2007年是季羡林本命年,季羡林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老人家笑称:“这叫红男绿女。”原来,一旁的秘书穿的是绿色衣服。
他还说,还要再过个本命年,活到108岁。还是那一年,刘晓晖和同事一同给季老送荣誉证书,拍照环节结束后,老人家突然蹦出一句:“我表演完毕。”老人家曾谈起过因为经济原因,上世纪50年代与宋版《资治通鉴》失之交臂的往事,谈毕,他竟然一拍大腿:“我当时就应该当了裤子,把它买下来。”
季羡林叫刘晓晖“小友”,成为忘年交主要是因为两人有关于小猫的共同话题。季羡林说:“我家里有四五只猫,它们在稿子上撒尿我从不打它们。”“小友”说:“我的小猫会开冰箱,上厕所,它10岁了,但现在没了。”老人家一听这话,就像小孩子一样赶紧把嘴闭紧了,从此再也不提猫了。但是,他对小动物的爱却一直持续着,病房里的毛绒小猫、小鸡、小猴子一直陪伴他走完最后一程。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不知给季羡林拍过多少照片,“他连吃饭都让我拍,从不拿我当外人。”在他看来,“像季老这样智慧的人不多,他始终不给别人难堪。别人请他题字,他从来是微笑着,从来是来者不拒,实际上,他更多是在考验身边的每个人。”
任继愈爱国心相伴悠悠学术路
本报记者 李洋
7月11日凌晨4时30分,我国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任继愈为人低调,尽管其学术成果对当代中国具有深远影响,却坚持不出自己的全集,也拒绝学生们为他出纪念文集,对身后事更是交待一切从简;他直到今年2月仍每周一和周四到国家图书馆上班。
如今,任继愈离去,他的诸多事迹才通过朋友和晚辈们的讲述,呈现在公众面前。
建立宗教学会和无神论学会
在任继愈担任过的诸多职务中,有两个身份看起来是完全对立的。一个是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一个是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而且,两个学会都是他亲手建立的。我国佛教史专家杜继文从上世纪60年代就与任继愈交往,杜继文介绍,任继愈创办的这两个学会恰恰代表了他在学术上的两个重要贡献。
“他最大的学术贡献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并开辟了用马克思主义视野观察宗教问题的先河。”杜继文总结。而且就在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提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这一理论的提出,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贡献。这些研究涉及到提高民族素质的重大问题,对当代中国和日本等国家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杜继文回忆,任继愈曾说过“社会主义不仅要脱贫,还要脱愚”;还说过“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就是同中国爱国主义相结合”。在任继愈一生为学中,他正是将这种爱国情怀,这种对国家前途的忧思深深融入到学术研究中,这在中国现当代学者中,并非人人都能做到。
爱国爱事业不爱金钱
任继愈的门生、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白化文说,在自己众多的老师中,任先生有一大特点别人并不具备。“他实际上指挥组织了很多国家级国学研究项目,比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有一天,白化文接到老师的电话,说《中华大典》的民俗典要交给自己编。
“我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就说我哪能成啊。结果,说了半天,他最后撂下四个字:就是你了。我哪敢不接啊。”接下来的日子里,白化文深切感受到,任继愈从来不当挂名的主编。“其他卷的主要负责人也都是他挑选的,编纂中的原则、方向等重大问题他都亲自定夺,重要稿件都要过目。”
同样感受到任继愈如此认真的,还有杜继文。他记得,为了劝说自己参与编纂《中华大藏经(续编)》,91岁高龄的任继愈还在大冬天里,一级一级台阶爬了5层楼,找到自己家里来劝说。而且,在五六个人组成的编委会中,任继愈拿的工资仅仅是自己的一半左右。
“他组织大家编辑这些大工程,从来不想钱的问题,有时候晚辈们觉得他有点儿‘愚’。他爱事业、爱国家,却不爱金钱。”就在今年,任继愈已经住院后,还趁身体稍微好转出院时,直奔有关国家领导人家中,商议这部书的编纂问题。
不出全集的大师
如今,任继愈去世,人们却发现,和他交往的漫长岁月中,老先生从没有拉着别人为自己事忙活过。正如他的老师熊十力评价的:“诚信不欺,有古人风。”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对任继愈先生的九十大寿印象颇深。“那天大家都在馆里开会,馆办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是任老的生日,大家就准备给他过生日,但他坚决反对,劝了半天,最后还是全体鼓掌,就算把生日庆贺了。”
其实,任继愈的八十大寿、七十大寿等也都没有专门庆祝过。他的助理李劲回忆:“他曾经对子女说,不过生日是因为在这样的时候人们都会说些违心的话,比如 ‘长命百岁’,没有必要。”他的学生们也曾想借他过生日之机,编辑一些纪念文集送给他,也被他婉言谢绝。
李劲说,老先生也不愿意出版自己的全集。“他觉得一个人不可能写的所有东西都是有水平的,全集里一般都是有水分的,那还是不要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