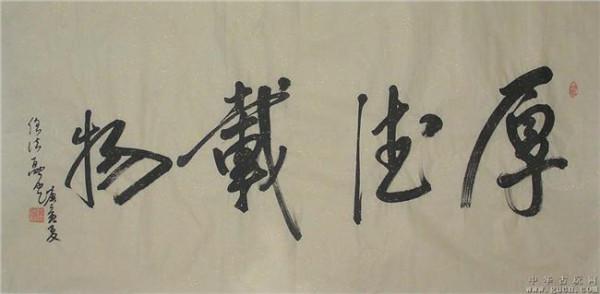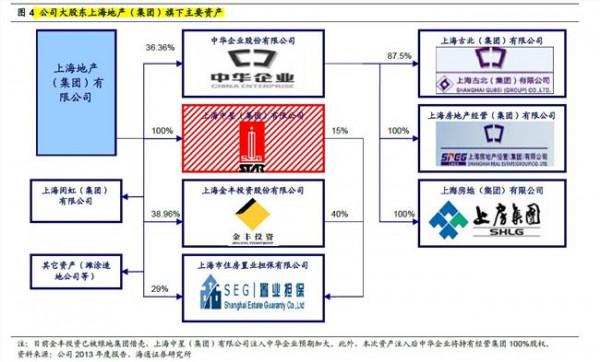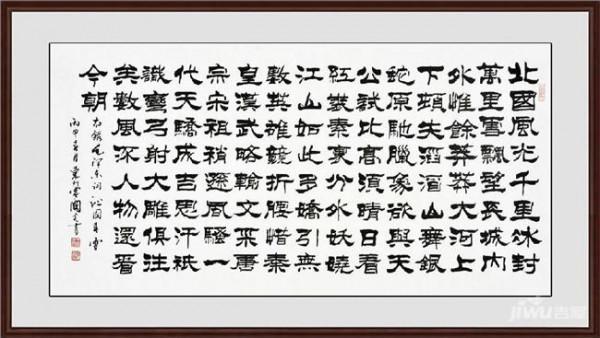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 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
书摘 原始的巫教是一种自发产生的自然崇拜宗教。由于氏族组织的狭窄和交往的阻隔,各个氏族的崇拜对象不仅因地而异,甚至和其他氏族创造的神相互敌对。自从建立了地域性的部落联盟,随着各个不同的氏族部落之间的交往的发展,人们的视野也扩大了。
他们逐渐感觉到各个不同的氏族部落所面对着的是一个共同的统一的自然界,就是日、月、星辰、雷、雨、风、水、火、山岳、河流等,因而在各地流行的自然崇拜对象实际上是共通的,有可能把各种纷歧繁复的自然崇拜整理成一个系统。
同时,正如地上人间的各种互相对抗的社会力量被拥有至高权威的部落联盟首领所统一起来一样,在自然界,也应该有一位支配着形形色色的自然现象的统一的至上神。统率着各种自然力的天神观念在这个时期产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是适应于巩固部落联盟的需要,为了维护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威而发展起来的宗教意识形态。 从此以后,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威便和他的最高祭司的宗教上的特权密切结合在一起。
据《尚书,舜典》记载,舜在代替尧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时,曾举行了一套宗教仪式: 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大意是说,舜为了表示自己取得了最高祭司的宗教上的权力,首先祭祀天神,然后按尊卑次序祭祀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等六宗, 以及名山大川丘陵坟衍等群神。
为了表示自己取得了最高首领的军事行政上的权力,把象征四岳群牧所掌握的部分权力的圭璧预先收回,然后选择某个吉日再亲自颁发下去。
墨于虽然处处替劳动者的利益着想,却经常不自觉地给这种反映阶级利益的思想披上一件普遍性形式的外衣,天真地认为劳动者的利益同剥削者统治者的利益可以相调和。墨子所讲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在理论上包括了上下各个阶级和阶层。
“三表”讲“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意味着统治者和人民可以同利。墨子认为他所设计的治国之道,既是为了百姓利益,对统治者也有好处。
他的主张好比是草药和税赋,来自下层,而能利之于大人,以此表明,他从事政治活动的目的不是谋取一部分人的利益,面是要使混乱的国家上下都得到治理。违背了他的主张,大人和贱人同时都要受害;实行了他的主张,大人和贱人同时都会受益。
例如王公大人好战,百姓固然遭殃,到头来也害了他们自己:“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鉴于智伯之事”,则“为不吉而凶”(《非攻中》)。又如久丧之法使上下同受其害: 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使士大夫行此,则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
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节葬下》)再如执有命之说,亦复如是: 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倍政之本。
(《非儒下》) 若不信命而自强不息,上下则同受其益:王公大人“强必治”、“强必宁”,卿大夫“强必贵”、“强必荣”,农夫“强必富”、“强必饱”(以上《非命下》)。
在墨子看来,王公大人的听狱治政,卿大夫的守职驭民,同农夫耕稼、百工行艺一样,是社会的职业分工,都是社会所必需的有益劳动,因此,他把“君子听治”包括在“赖其力者”之内。
墨子本 来是颂扬劳动,反对剥削的,在这里他却混淆了剥削与劳动的界限,抹杀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这是因为他没有阶级观点,不懂得阶极关系与职业分工的不同。墨子所说的全社会上下同利在阶级社会里并不能实现,但这类超阶级的观点作为一种政治口号和主张,却时常在历史上出现。
马克思在分析十九世纪法国小资产阶级的时候曾说: (2)“狂举”。“狂举”与“正举”相对,源于公孙龙的《通变论》。《通变论》说:“举是乱名,是谓狂举”,“非正举者,名实无当”,考其实例,“狂举”指分类不当,名实不符的错误。
例如以羊有齿牛无齿将牛羊分为异类就是“狂举”,因为齿的有无只是类中之异;以羊牛皆有角而将两者归为同类亦是狂举,因为角可以为异类所共有,若以羊牛有角无尾(指毛尾)、马无角有尾来断定羊牛与马是异类则是“正举”。
墨经对于公孙龙的上述观点,有所吸收,却又不全部赞同。 《经下》:狂举不可以知异,说在有不可。 《经说下》:牛性与马虽异,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之非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无有。
曰:“之牛与马不类,用牛有角,马无角,是类不同也。”若举牛有角.马无角,以是为类之不同也,是狂举也,犹牛有齿,马有尾。 墨经认为,以齿,尾,角三者的有无作为区别牛与马的标志,都是犯了不知类的“狂举”的错误,这又比公孙龙进了一步,在探讨牛马之异时,认识深化了,排除了更多的外部次要特征。
可惜它没有正面说明牛与马的本质差别。 墨经还指出,告子的“仁内义外”说也是“狂举”。
《经说下》指出: 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其为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是狂举也。 “爱”(仁)、“利”(义)是“此”,即人的主观上的思想品质;“所爱”、“所利”是“彼”,即爱、利所施予的客观对象。
品质与对象可分内外,而品质内部,对象内部不能再分内外,“仁内义外”说的错误,是把本来均属主观范畴的一类事物,分属于主、客观两类之中,是不知类,故为“狂举”。
(3)“过”。《经下》说:“知狗而自谓不知犬,过也。说在重。”不懂得狗与犬乃二名一实,是犯了“过”的错误。“过”是指概念不清晰、名实关系不明确的逻辑错误。
所以当某地沿用与实不符的旧名时,称为“过名”,若不知是过名,就会引起混乱。 《经下》说:“尧之义也,声于今而处于古,而异时,说在所义二。”《经说下》解释说:“尧之义也,是声也于今,所义之实处于古。
”尧行义的实际作用发生在古代,今天人们只知其名声而未得其实惠。若不懂这种名实关系的变迁,以尧善治古推断尧亦能善治今,也是一种“过”的错误。后期墨家重视时代的变化,不迷信古人圣贤,在历史观上比墨子前进了一步。
(4)“不辩”。 《经下》: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不辩。 《经说下》,所谓非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其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 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有两种做法皆可导致“不辩”的错误:一是在同一对象的两个名称之间争论,你说是狗,我说是犬,两者皆当;二是在两个不同对象上争论,你说甲是牛,我说乙是马,双方没有形成真正的对立,这两种做法都不是真正的争辩,因为不是争“彼”,即不是在同一对象上争论是非。
“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这才是争“彼”,体现了排中律的要求:A或是B,或是非B,二者必居其一,而以“当者”为真。“不辩”是一种在辩论中回避矛盾的错误,其结果是“俱无胜”。
综上所述,后期墨家的逻辑理论相当完整严谨:它有关于逻辑学的总论,有对思维形式的分析,有对推理(特别是类比推理)较细密的研究,有对逻辑错误的揭露,也有逻辑学的实际应用。
它的逻辑学贯串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精神,因此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战斗性,成为先秦时代最高水平的逻辑学理论,在整个中国逻辑史上都占有光辉的地位,直到今天仍给人以可贵的教益。它不足之处是理论分析尚嫌粗略,对于逻辑规律如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 缺乏明确论述。
韩非是我国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封建中央集权专制提供了政治理论的根据。秦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虽然不再公开打法家的旗号,然而法家思想的精髓却被继承下来。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封建地主阶级便采取儒表法里或阳儒阴法的学说。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战国末年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即将形成的形势下提出来的,它的理论核心是通过加强君主专制强化中央集权。
具体地说,韩非的法治理论就是为封建帝王提供统治术的。韩非理想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形式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于·扬权》以下只注篇名)“要在中央”是指立法大权归统一的中央政府掌握,这表明诸侯分权的政治局面即将结束,郡县制将要完全取代分封制。
“圣人执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权力最后决定在皇帝手中,即实行君主专制独裁。这样加强君权的主张,是适合即将出现的封建大一统的要求的,它自然也会受到秦始皇和后来封建帝王的欢迎。
韩非强调法、术、势三者互相结合。 法,就是成文法,“法者,编著之图籍,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难三》) 术,就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术者.
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同上) 势,就是势位,指国君的威势,即政权,“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主之所以尊者,权也”(《心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