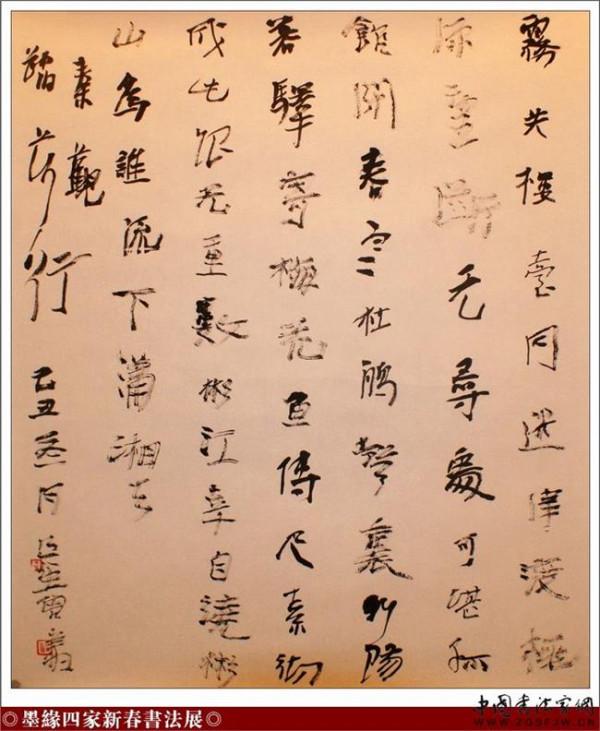王家新汉语的未来 王家新:汉语的未来
初春的一天,我意外收到北大附中林芳华老师的一大包邮件,打开一看,原本是她为学生们开设的“艾米莉·狄金森诗歌选修课”的课程小结及学生们的“作业”——诗!
我曾到那里讲过一次诗歌。我似乎又看到教室里那一张张纯洁而好奇、稚气而严肃的脸庞。我问这些孩子们读过什么诗,他们回答:“古典诗”,那么现代诗呢,他们则一律回答“读不懂”;似乎我还问过诗来自何处这类问题,他们的回答则和他们的父母几十年前回答的一模一样:“诗来自生活!”当时我深感我们的教育仍是在遮蔽而非开启心灵,然而,这些幼小的心灵是多么珍贵啊——他们不仅是这个国家的未来,而且也是汉语的未来!
但是,当我沿着林老师寄来的这一页页打印稿读下去时,我惊讶了。我没想到中国的中学还可以开设这样的文学选修课,还有人在默默地做着这样的心灵启蒙工作,更没想到那些看上去与诗无缘的孩子仿佛在一夜间展露了他们的诗心与才华。当然,这些诗仍不无稚气,但在读它们时我却想到了诗人西穆斯·希内所描述的那阵透过桤木林滴下的雨“它那低微的益增的声音……每一滴都令人想起/ 钻石似的绝对!”
这里,我一直在使用“孩子”一词。我想这不仅因为我已属于“父辈的一代”,更因为我也有一个已上高中的儿子,因为我的孩子自幼也曾迸发出某种奇异的想象力和语言才能,他那时说出的一些“话”和歪歪扭扭写下的“诗”,也曾把我和我的朋友们“吓了一跳”。
然而,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当他一步步被纳入某种“规范”后,这种诗的才能被压抑了,他的“话”也不像小时那样有趣了。一次,听到他为了考试正在大背什么“个人与国家与集体的三者关系”时,我同样被吓了一跳。
只不过这次已不是喜悦,而是悲哀了。孩子们一步步被塑造成能被体制所接受的人,但其代价却是一些更珍贵的东西的丧失。问题还不仅在于学校的教育。1992至1994年间我不在国内,待回国后竟发现儿子的理想已完全变了——已由当艺术家变为当什么“总经理”了!
我没想到一个人人下海的时代竟如此迅猛地改变着社会,甚至波及到孩子们的心灵!我试图“管一管”,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我已深知在一个“唯物”的时代、在这滚滚红尘中做一个“饥饿艺术家”的艰辛和荒谬。我也不忍心让孩子们长大后再来从事我们这门痛苦的行当了。那就让他们去吧。
但,内心中不变的仍是爱,是某种已变得渺茫了的期望。面对现行教育状况和已变得法力无边的商业消费社会的腐蚀力量,一方面我无比沉痛地听到了鲁迅先生当年的“救救孩子”的呼声,一方面又深感到个人的无能为力。似乎中国的作家和诗人很难、也很少介入到教育中去,似乎教育与文学已被默认为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
而这种“默认”真是意味深长。我们当然可以为自己找出种种措辞,然而,所谓文学的“良知”何在呢?我想起了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那惟一的亮色,那是在阴森的死亡的灰惨色调中当一个孩子出现时才出现的亮色。
导演斯皮尔伯格着意对它进行了破例的彩色处理,因为这是绝望中的希望,是他作为一个电影思想家不泯的良知所在。与这种亮色相呼应,电影中还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让我不断想起:救了一个人也就是在救整个世界。
因此,应当感谢林芳华老师。她是在做我们这些所谓的“诗人”应该去做而未能去做的工作。不仅如此,她还让一个鲁迅或斯皮尔伯格意义上的“孩子”重又出现在我们面前,而这比任何事物任何力量都更能唤起我们的良知。说到底,我们需要去“救”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孩子,更是我们自己。
从这里谈开去,像林老师所做的这种工作,不仅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诗歌,为了一种语言和文化的未来。惠特曼有一句广被引用的话是:伟大的读者造就伟大的诗人。这里,他指出了读者与诗人、文明与诗歌的相互造就的关系。
在我看来,这种关系有点像荡秋千:诗歌能“荡”多远,完全依其推力而定。它有赖于读者和文化环境的推力,它不断地回到这种推力,也在要求这种推力。虽然诗歌的创作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但它在根本上仍受制于这种和它构成互动关系的读者和文明的作用力。
这里,存在着一只比诗人的手更有力的“看不见的手”。我曾在欧洲快车上遇到一位埋头阅读尼采、知道我是中国人后又兴奋地用英文背诵孔子语录的女士,我以为她是什么文化人,后来才了解她原是瑞士的一位理发师。
我还在德国认识一位“杜甫迷”,他不仅热爱杜甫的诗,还曾为此前往中国数次,带着一本中国历史地图册,遍寻杜甫当年的足迹;然而这并不是一位“汉学家”,他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学化学老师!
所以,我理解了在欧洲何以会产生像叶芝、里尔克、普鲁斯特这样的作家和诗人,因为它的文明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当然,欧洲早已不是什么“高雅”或“精英”的一统天下,然而,无论受到怎样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冲击,它也不会愚蠢到仅仅以“市场”来作价值判断的标准,更不会出现像目下中国文坛上这样无聊、恶俗的炒作。因为就整体而言,那里的“人民”仍处在良好的文化修养的引导下。
我讲出这些,其意正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对文学启蒙的注意,提醒一种诗歌与文明、与国民素质的互动关系。为什么这些年一再出现“看不懂”的责难?为什么诗歌和其它严肃文学会如此轻易地被逐出市场经济的“理想国”?为什么那些坚持把诗歌作为一种对语言和文化的提升的诗人在今天又被扣上了“脱离读者”的帽子?这一切说明了文学的启蒙在我们这里仍得从头做起,说明了文学的发展不能总是与教育脱节。
的确,很难设想在一种贫乏的、发育不良的文化环境中会奇迹般地出现一种心智成熟的诗歌,即使有,它的命运也会不妙,它也难乎为继,因为它缺乏来自自身文化环境的支持和推力。
好在教育界“素质教育”已被提到议程上来,虽然有些人对“素质”的理解仍让人啼笑皆非。在这种情形下,林老师没有选择电脑而是选择诗歌作为素质教育的突破口,这无疑体现了一种洞察力。因为诗歌才是对心灵的开启,是对人的内在素质的提升,因为人的自我意识、想象力和创造力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至于林老师为什么会选择一位美国十九世纪女诗人,首先出自她的热爱。在几年前林老师曾选修过我的比较文学课,她交上来的作业是狄金森与李清照的比较,当时我还没有怎么在意,现在我才意识到:多年来狄金森的诗一直在对她的生命讲话,这使她安于教师的职业,并从中感到活的意义。
她不是诗人,也从不写诗,但是,当她带我穿过北大附中校园去见她的“孩子们”时,一瞬间我感到在她身上似乎就活着狄金森的诗魂!
我不得不惊讶于诗歌那种超越生死、穿透时空的力量。现在,她要她的孩子们和她一起来分享这种秘密的爱。她对他们说:读狄金森你会感到“思想着的独立的人的可贵”,她还说:“阅读她就是在青铜的历史上的漫步”。孩子们半信半疑地听了,直到他们在这种诗歌漫步中惊讶地发现了他们自己。
的确,林老师的选择再好不过,如果我们了解狄金森的诗歌的话。对于这位优异的女诗人,虽然有人说现在美国的男女老少都读她的诗,但也有人说很难懂,林老师却认定“诗中充满智慧和性灵的东西正是年轻的时候可以理解的”。
她相信在诗人的语言跳跃中有一种直接进入心灵的力量。她相信这些看似简洁却又“晦涩”的诗中蕴涵了人性中最深邃、内在、高尚的东西,它们不仅会开启孩子们的心灵,还会为它定位、导航。她为她的课做了大量工作。她终于喜悦地看到对狄金森的诗歌一无所知的孩子们产生了热爱,在一次次讨论中她发现“我们心中总有火花闪耀”,“只要我们心中水草丰美,尘俗中人依然可以诗意地栖居”。
结果是,孩子们不仅喜欢上了狄金森的诗,而且纷纷以自创诗歌的形式,表达他们的这种热爱和他们内心中诗的觉醒。
邓倩文同学的诗是《堕落的天使之翼》:“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延续生命/ 除了此刻奔涌的液体/ 那是燃料/ 直到我看见白色的玫瑰/ 长出刺来/ 也无法使它冰冷”。
林老师记下了邓倩文自己的解释:因为狄金森喜欢穿白色衣服,所以这首诗中出现了“白色的玫瑰”;她还说生命是有限的,终会死亡,奔涌的液体指血,也可以是激情。林老师很喜欢这首诗,并认为“堕落的天使之翼”这一题目耐人寻味。
还有一位刘昂同学,本来就有“艺术细胞”,在林老师的鼓励下,小本子上已写满诗了!他有这样一首《头发》:“梳子来了 头发倒在了一起 有几根头发 直挺挺的 岿然不动/ 风吹来了 头发倒在了一起 那几根头发 依旧 立在那里 岿然不动/ 终于 剪子来了 那几根头发 牺牲了。
”如此可爱!林老师的评语是:“就像狄金森的自然诗,幽默而有情趣”。正是在这样的理解和引导下,孩子们的热情更大了。
今年二月,刘昂随校乐团访美,当他谈起狄金森时,房东马上拿出一本狄金森诗歌全集送他。刘昂返校后找到林老师,一起来分享这喜悦。的确,孩子们听到了诗歌对他们的呼唤,或者说,诗歌已来到这些孩子们中间,寻找它未来的骑手。
一切刚刚开始。下一步,林老师将通过原文与译文的对照,将孩子们更深地引向对诗的自觉,去体会“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的确,这句话不错,诗歌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
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诗”也是一种在僵化的教育中失去的东西。因此,林老师所做的一切,与其说是施予,不如说是“恢复”,是拂去蒙在心灵上的积尘,让它向着诗歌敞开。“教育不在于给予什么,在于打开,就像诗,给我们第三只眼”,这是林老师的话,在我看来,也是对素质教育、对文学启蒙最好的理解。
孩子们没有辜负林老师的心血,在诗歌的引导下,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心灵,也重获了自己的语言。他们的诗包含了真正的诗的幼芽,或者说,迸发出了那些“教育家”们意料不到、也难以想象的东西。而这正是希望所在,因为只有这样的诗歌才指向未来,也通向未来。
上个学期放寒假时,林老师说她和她的孩子们用狄金森的一首诗互说再见。现在,林老师给我找出了这首诗:
殉理想的诗人,不曾说话——
把精神的剧痛在音节中浇铸——
当他们人间的姓名已僵化——
他们在人间的命运会给某些人以鼓舞——
殉理想的画家,从不开口——
把遗嘱,交付给画幅——
当他们有思想的手指休止后——
有人会从艺术中找到,安宁的艺术——
我非常感动。一种在这个时代甚至在所谓“诗坛”早已失落的诗歌精神,在一个不为人知的中学老师和她的孩子们中间重又被点燃起来,这使我没有理由为诗歌悲观,也没有理由为汉语的未来悲观。我想,我们同样可以用这样的诗同那些为我们的内心所不能接受的一切说“再见”了,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所要从事的工作,已被一种不死的精神所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