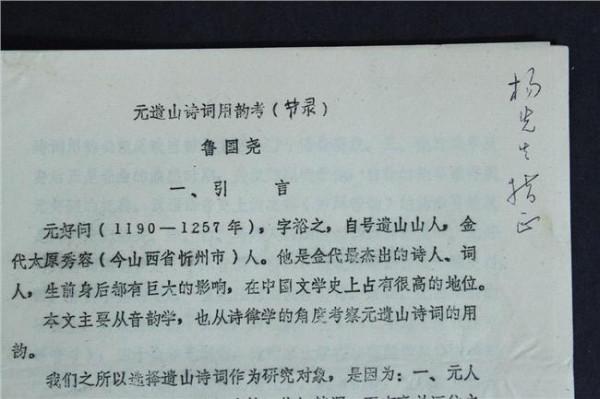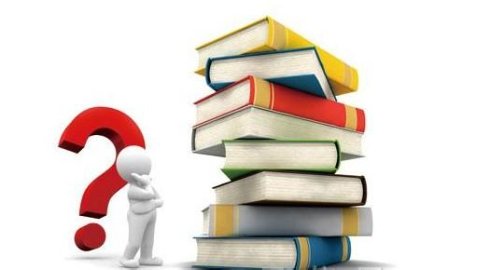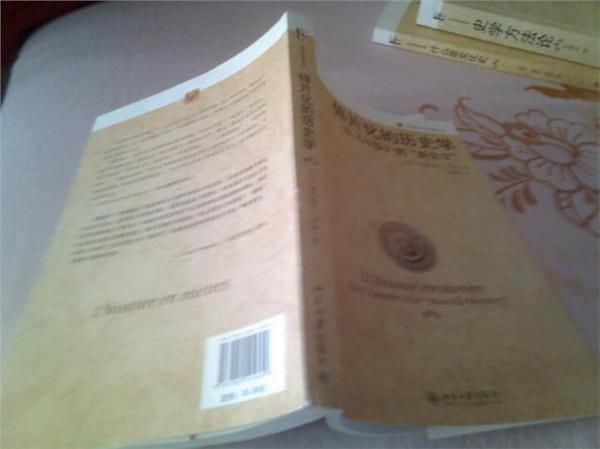旅行者王家新 语言学转向下诗歌的另外可能兼论王家新《旅行者》
优秀的诗歌总是自足的,无需赘言的。它告诉自己,它就在那儿,它澄明,映照出人类最基本的经验,他拒绝了作为一个诗人的冒犯。而这种冒犯,将语言置于一个尴尬境地,似乎诗歌不需要情感的滋养的观念。
在低劣的诗人那里,这往往被奉之为瑰宝,以此开始他们乐此不疲的追逐。而在优秀而自足的诗歌面前,批评者所作的,往往只能是指示,是彰显,而不是将自己所谓的“高见”强加于上。
现代诗歌的语言学转向,将诗歌语言提高到本体的高度,将语言视为一套自足的系统,语言总是充满了歧义,其自身是模糊的、不透明的,自我衍生的,这无疑是了不起的洞见。但正是在整个诗歌界出现语言学转向后,现代诗歌无可辩驳的衰落了。
诗人们在语言面前退让了,在诗歌中试图让语言自身说话了,他们玩起了语言试验,在语言的自我嬉戏中消费着廉价而且可怜的快感。而且一再将诗歌语言与日常话语划清了界线,似乎诗歌摆脱了交流的目的性意义,陷入了一场集体洪大的“自说自话”的狂欢。
诗人们在语言中迷失了方向,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在语言的律动中生发出某些诗意,写诗成了一场被动的心理追逐。语言学转向陷入了语言的迷途,这无疑是现代诗歌堕落的开始。
而真正的强者,是在这场迷途中有所反省,而实现飞越的人。诗歌总体说来,是一项均衡的艺术,它不限于某种单一的诗歌理论。诗歌理论对于诗人来说,只具有指向性的意义,别无其他。如何我们愿意深究,在于我们完全忽略了语言学转向的另外一种可能:既然语言充满了歧义,其自身是模糊的、不透明的,自我衍生的,那么诗人要做的,恰恰是在言语中,寻找其明晰的部分,而不是盲目的服从,甚至人为的“增魅”。
究其原因来说,语言本质就是一种功利性的语言,如果失去了语言的“吁请”—“接受”的交流性功能,失去了指涉,语言将不复存在。
因此诗歌必须是明晰的,而不是含混的,需要重视的是其可解的部分,而不是未知的部分。应该认识到诗歌语言与实用语言在此意义上来说,是并行不悖的。
差别在于,实用语言在于理性的辨析,而诗歌语言在于情感的凝粹。诗歌的明晰性在于情感的可转移性,失去了情感的支撑,诗歌不会获得任何的生命力,就像现在很多诗歌所实践的那样。
对于现代语言学转向的拨乱反正,将是一场诗歌界的一场“哥白尼”式革命。 让我们看看王家新的《旅行者》。
这首诗不长,它所有的句子,几乎都是明晰的,都有着明确指涉的,即便是在想象中,这种想象仍然是基于现实的(想象其实也就是一种现实),基于整体的情境。它拒绝了所有的隐喻和换喻。也就是说,语言在这里所要做到的,只是如何更好的表现作者的意图,恢复当时的情境。
在这里,我并不否认词语和诗人的角力,但很明显,在这其中,诗人是强有力的,是主导者。在这里,诗人的想象也不是无止境的,而是服从于情感的需要。这是一项综合性的劳作,均衡才是其最终归属。
旅行者 作者:王家新 他在生与死的风景中旅行, 在众人之中你认不出他;( 有时在火车上,当风起云涌,我想 他会掏出一个本子;或是 在一个烛火之夜,他的影子 会投在女修道院雪白的墙壁上。
蚂蚁会爬上他的脸,当他的 额头光洁如沙。 他在这个世界上旅行,旅行,或许 还在西单闹市的人流中系过鞋带; 而当他在天空中醒来时, 我却在某个地下餐厅喝多了啤酒。
七年了,没有一个字来, 他只是远离我们,旅行,旅行; 或许他已回到但丁那个时代, 流亡在家乡的天空下;或许突然间 他出现在一个豁然开阔的谷口—— 当大海闪光,白帆点点在望, 他来到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
七年了,我的窗户一再蒙上白霜, 我们的炉火也换成了暖气——为了 不在怀念中生活?而我一如既往, 上班、写作、与朋友聚会…… 只是孤身一人时我总有些害怕; 我怕一个我不再认识的人突然敲门 诗歌的情境很简单,无需作出任何的过度阐释:一个朋友七年没有见面,在世界各地旅行,七年间我的生活中有变化也无变化,因为我的这些变化和无变化,使我想起如果七年前的朋友造访,我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而无可否认的是,我和他同样面对着死亡。
这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情感。这种情感整体传达到读者那里,诗歌的使命已经完成。至于我们可以将他引申开去,比如这个朋友就是诗人自己,这种旅程(那么就成了两个)就是生命旅程的两种体现等等,也未尝不可,但要清楚的是,这种内生的机制,是来自这种普遍情感本身。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他在生与死的风景中旅行”似乎有隐喻的成分,其实我们将其摒弃,效果更佳,比如我们改成: 他将慢慢死去, 在人群中,你很难发现他。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