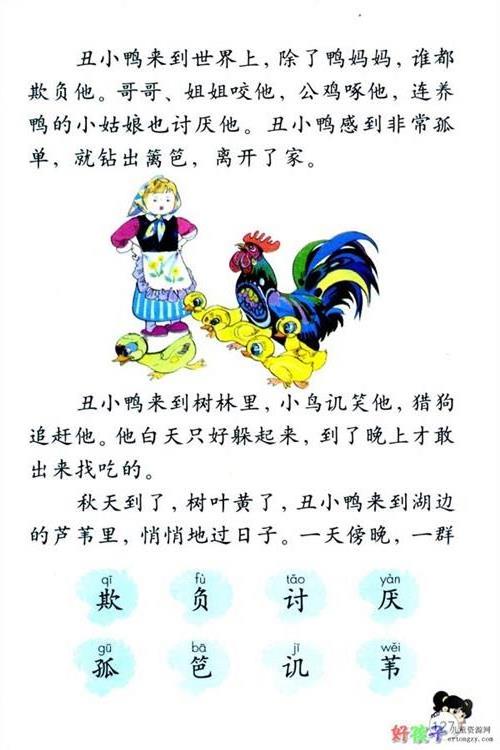陆扬圣经 陆扬:论《圣经》的崇高美学特征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上帝创世、约伯记和耶稣殉道三个片断,阐证《圣经》的崇高美学特征相吻于崇高作为美学范畴的一般特征即超越。它分别表现为上帝全能全在、超越了一切世俗知识形式的绝对;表现为神性和人性不能相提,然最终嘉许人类苦难中的悲声的神的公正、;以及表现为挣扎和极度的痛苦中精神对于肉体的最终超越。
其间崇高范式可见出的从神秘向人文过渡的倾向,正不妨视为《圣经》从犹太教到基督教经典确立过程中可予探考的美学意蕴走向。
关键词:上帝、创世、约伯、耶稣
《圣经》作为西方文明的两个渊源,人所公推的美学特征是崇高。《圣经》中的上帝不苟言笑,威严深邃莫测,而且三令五申严禁形象崇拜,与希腊神话中宙斯与人大体同形同性的君王模样,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而希伯莱民族的历史出演在巴勒斯坦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始终是在战乱频仍、刀光剑影中辗转迁徙,艰难求生存,这与希腊得天独厚的地中海蓝色文明比较,可以孕育出怎样内省孤僻的民族性格,也为显见。
假如认可康德的释义,以崇高是为主体为外部的险恶危殆所压倒,然内在的精神奋起反抗,终而在气势上胜出,"所以崇高不存在于自然界的任何物内,而是内在于我们的心里",那么称《圣经》足以给我们提供崇高美学的典范,应当说不是夸张。
但通览迄至近日国内的《圣经》研究,谈论《圣经》文学的为多,探讨《圣经》美学的为少。而在原属希寥的《圣经》美学著论中,述及《圣经》美学崇高特征的,更见其微。这个缺憾相信随着有关研究的深入,可望有丰盈的补充。本文且抛石问路,拟就上帝创世、约伯记和耶稣殉道这三个恐怕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片断,来探讨《圣经》的崇高美学特征。
上帝六日创世体现出的崇高意味,很显然并不限于神学的意义。黑格尔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黑格尔的崇高论强调的也是精神。他说,"崇高把绝对提升到一切直接存在的事物之上,因而带来精神的初步的抽象的解放,这种解放至少是精神的东西的基础。
因为这样崇高化的意义虽然还没有作为具体的精神性来理解,却已被看作独立自在的内在的东西,按其本性,就不能在有限现象中找到真正表达它的形象。"这一致力于从精神方面来阐释崇高的美学思想,与康德崇高不在自然界,而在我们心里的著名论断,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黑格尔称上帝创造宇宙是崇高本身最纯粹的表现,复引《创世记》中"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1:3)作为崇高最突出的典范。这当然不是黑格尔一个人的感受,上帝造光最为崇高的说法,本身就是来自朗吉弩斯的《论崇高》。设想太初上帝在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中创造天地,光明顿出的这一瞬间,其辉煌灿烂给予我们的震撼,肯定绝不仅仅是视觉上的愉悦。
《创世记》交代上帝创造了光,没有交代上帝创造黑暗。光明是上帝创造,黑暗是不是上帝创造?《创世记》似语焉不详。"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1:1-2)给人的印象更像是黑暗本是上帝创世之前,或者说宇宙诞生之前即已存在的原始样貌,它们正在等待上帝创造光明和秩序,降临于上。但是《以赛亚书》中我们读到了这一段话: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45:6-7)
这段话意味深长,它意味不仅光是上帝所造,黑暗同样是为上帝所创。《以赛亚》书的作者这里明显是想强调上帝创造了光明也创造了黑暗,创造了善也创造了恶。仅此一端,上帝耶和华就大不同于是时或亦在成形之中的琐罗亚斯德教的善恶两元神。
上帝是至善的,但是他并不是与恶对峙的那一种原始力量。反之善和恶、光明和黑暗一并收入他的麾下。故此,《出埃及记》里我们看到上帝调遣黑暗,降灾于埃及人:"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
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10:22)这三天里,惟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这令我们想起《诗篇》:"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上帝必照明我的黑暗。"(18:28)这可见上帝的至高无上,非"至善"一语足以形容。
希伯莱一神教的崇高范式,由是观之,当是朝向无限的一种名可名,非常名的延伸。或如黑格尔紧接上面引文所言,它虽然被表达出来了,却仍然高高居于个别现象乃至个别现象的总和之上。
实际上上帝的名谓高深莫测。约定俗成的耶和华人已皆知实是亚卫(Yahweh)的误译。而亚卫在最早的希伯莱经文中并没有赖以拼读的元音,是为YHWH,可写而不可言。这是真正的大音希声。上帝的神圣和崇高在这里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语言能力。
《创世记》有"耶和华上帝造天地的日子"(2:4)语,耶和华与上帝两名并用。"耶和华"即是Yahweh,是为上帝约定的名谓,第三人称,意谓"他是"或"他将是",耶和华不是别的,他就是以色列人的救世主,他们约定的上帝,他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
故亚卫的第一人称,即当上帝称呼自己的时候,理所当然便是"我是"或"我将是"。是以《出埃及记》里摩西问上帝,假如我去以色列人那里,告诉他们是你们父辈的上帝派我来的,假如他们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该如何作答?上帝当时就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
"(2:14)这是官话和合本的翻译。此句的英文是I AM WHO I AM,我是我所是。这便是Yahweh一名的所指。
"上帝"(Lord)一语则是神的泛称,译自希伯莱语Elohim,强调的是神的绝对的至高无上。两个名称在《旧约》中交替出现,不下数千次,这里予以并提,显然是在表明它们指的是同一个独一无二的至高上帝。
上帝有时也称自己是全能的上帝。如《创世记》亚伯兰99岁,上帝向他显现时,就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17:1)"全能的上帝"(God Almighty)系出希伯莱文El-Shaddai,又是一个崇高意味非常的称谓。
Shaddai一语有巍巍如山之意,在《约伯记》里出现达31次,而在其余各篇出现不过17次。这正可印证上帝广垠无限的伟力,终也叫心有不甘的约伯哑口无言,承认上帝天机莫测,自己是何等渺小。盖言之,上帝是专门庇护以色列人的神,他就是绝对。
《创世记》写上帝六日创世,大功告成后,"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1:31)公元前三世纪完成的七十子希腊译本(Septuagint)中,上文的"好"一语用的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希腊词kalos。
虽然,公元5世纪圣哲罗姆的拉丁通俗译本(Vulgate)将kalos译作bonum(好、善)而不是pulchrum(美),但kalos一语美善相间的本义,正可表出七十子文本的译者们有心移花接木,从希腊文化中传承过来的创造为美的用意。
上帝就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当他以无上的伟力无中生有,创造出欣欣向荣的大千世界时,那一种在对象中观照自身而感受到的由衷喜悦,无论将之命名为好抑或是美,没有疑问都是创造的至乐。
事实上即便是历代神学家,也乐此不彼在艺术和上帝创世之间来探隐发微。圣奥古斯丁曾以艺术喻上帝创世的神功。托马斯?阿奎那《论真理》卷三第1章引奥古斯丁的话说:一切生物皆在那神圣的心灵之中,诚如一件家具是存在于其制作者的心中。阿奎那这里无疑是意在说明,艺术家未及制作先已成竹在胸,这正相仿上帝创世之初,便有理念内在于心了。
上帝的创造体现崇高,与以美为奎臬的人类的创造不可同日而语。中世纪流行的是艺术作为技艺、作为制作的观念,反之如奥古斯丁《忏悔录》所示,戏剧、绘画等等"美的艺术",则给驳斥得体无完肤。这可见中世纪神学以艺术喻上帝的创造是在制造的层面上而不是审美的层面之上。
事实上《圣经》中凡言"制造",必指神圣,而概不涉及人为。换言之它是专指上帝的创造而不指任何人的创造乃至制造活动。如《创世记》:"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1:27)又《诗篇》:"南北为你所创造。"(89:12)而《罗马书》:"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众子显出来。"(8:19)凡此种种,可见《圣经》中的创造的快感,无不带有高不可测的崇高的意味,这与希腊的惟美传统,是大有不同的。
《约伯记》大凡从文学视野来加阐释,几乎无一例外被旁比作希腊的悲剧。悲剧的灵魂是崇高,《约伯记》无论像或不像希腊的悲剧,或者说是不是适宜被纳入希腊美学的悲剧范畴,它的崇高则毫无疑问是《圣经》里最是惊心动魄的一道电光。马丁?路德就说过《约伯记》的崇高《圣经》之中无出其右。但是,问题在于,《约伯记》的崇高美学特征是在于约伯绝对的信仰、绝对的忍耐?还是在于约伯在生不如死的苦痛中忍无可忍的悲声?
约伯的名字本身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好耐心的同义词。这在《圣经》里就有本可依。《雅各书》中,我们读到雅各布道有这样的话:"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5:11)可见约伯之成为逆来顺受的典型,由来已久。
约伯在极大的苦痛中苟延残喘,他诅咒自己的出生之日,自认为忍受的愁苦比海滩上的沙还要沉重。然约伯被认为是虔诚如旧,对上帝一如既往忠心耿耿,终而约伯苦尽甘来,身体康复如初,同时膝下更复添七子三女,由此无端受难的好人在一种更为抽象的赎罪中新生,而使着目于超越苦难的希伯莱文化,由此最为典型地表出一个忍辱负重的崇高范式。
但是我们细读《约伯记》,可以发现约伯其实终而失去了矢志不移的好耐心。从结构上看,《约伯记》全卷四十二章文字中,第1、2章全篇的序幕系散文写成,第3至37章是诗体的大辩论,有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交锋,更有以利户出来将约伯和他的朋友一并训斥。
第38章至42章第6节,除了约伯两段简厄应答,悉尽是上帝之言。最后第42章第7节以下,复以散文形式敷成,是为尾声。统览全卷书,约伯罕见其匹的忍耐仅见于散文体的一头一尾,而诗体部分则充斥了约伯的悲愤控诉:
我因愁苦而惧怕,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我必被你定为有罪。我何必徒然劳苦呢。我若用雪水洗身,用碱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我们中间没有听诉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印。(9:28-35)
约伯胆大妄为无以复加,竟至于设想同上帝来互按手印,诉讼高下,期望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在他和上帝之间作一仲裁。这又岂止是亵渎神圣!令人震惊的,是约伯称错不在他,而在上帝,对上帝的大不敬之言几乎就是没遮没拦。
第7章里约伯将自己比作神话中的海中大鱼:"我对上帝说,我岂是海洋,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7:12)这使人想起弥尔顿《失乐园》中的撒旦,后者正是张开巨大的翅膀,拽着熊熊火焰,从海面上冲天而起,直奔伊甸园颠覆了上帝的杰作。
第9章里约伯说,要论力量,上帝是无所不能,要论公正,谁又能审判他?这是将上帝述成暴君形象。第16章里约伯更诅咒上帝是呲牙裂嘴,把他撕成碎片:"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16:9)上帝这里几成凶神恶煞。这里约伯绝然不复是那个饮恨吞声的好耐心典范,而具有一种巨人式的气魄。至此约伯作为一个悲剧人物的崇高范式,可以说被充分确立了起来。
上帝最终在旋风中开言。上帝没有理会自以为是的以利户,上帝最终嘉奖约伯,而对他满口忠信的三个朋友嗤之以鼻。上帝对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42:7)又说,"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
"(42:8)这个结果叫人大吃一惊,上帝的公正看来真是莫测高深。它对约伯的忍耐压根就是无动于衷,然而终于是答复了约伯的悲声。我们看到上帝这样责问约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
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罢。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在何处?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38:2-11)
上帝进而责备约伯,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指引北斗和随他的七星吗?你能把智慧赐与众生吗?强辩的约伯,与神辩论的约伯,你能回答吗?约伯如梦初醒。造物主镂云裁月,吞吐江海的神功鬼斧,其深意非人类智能可以企达。这是上帝传达给约伯的智慧。
我们不难发现,上帝没有解答约伯无辜受难的怨愤,反之排山倒海提出一系列问题,证明自己的神性,叫约伯的问题变得毫不相干。上帝提醒约伯的是作为造物约伯没有权力来质问造物主。他要约伯明白神性和人性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东西。约伯终而知道天机玄奥,深不可测。我们看到约伯最终向上帝忏悔:"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42:5-6)。
上帝的崇高再一次展示出它威严莫测的神秘特点。此外,还将我们引向一个更深入的问题。这就是人类与上帝的关系。如果说,《约伯记》最终并没有解决人类苦难的问题,上帝是答非所问,南辕北辙,那么通过约伯的悔过,人类当可从自我中心的骄矜,终而来意识到他是神圣秩序的被造物而不是造物主。
上帝并非不知道约伯对他出言不恭,如其所言,"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示自己为义么?"(40:8)但发人深思的是,上帝看中了约伯不屈不挠的自由意志,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上帝最后给约伯的嘉奖或不足道。牛羊骆驼数量翻番和新得子女的快慰,未见得足以消弥先时丧子失女的惨痛。但是约伯心满意足。他终于得到了说法。上帝没有明示约伯好人受难的原委,他其实是回答了一个约伯和他的朋友们都没有想到的问题:人类无所不知吗?人类有权利来评判上帝吗?
《约伯记》的崇高特征由是观之,是典型展示了希伯莱神秘主义的美学特征。即它并不仅仅是表征人的自由意志和乖戾命运的不屈抗争,诚如我们在约伯身上读到的悲愤,而是惊心动魄叙写出了类似黑格尔所说的两种必然伦理力量的必然冲突。
作为冲突另一面的上帝,同样是表征出了一种更高的、更为深不可测的神圣意志。上帝没有嘉许人类苦难中的忍耐,上帝最终嘉许的是人类苦难中的悲声。因此毋庸置疑,他就是降临于约伯的乖戾命运背后的那个莫测高深的至善。
《约伯记》给予我们的这一点启示,对于认识希伯莱信仰的崇高特点,当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约伯,我们最终发现,不是因为他的忍耐,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忍无可忍之中发出的悲声,使他足以比肩反抗宙斯的普罗米修斯和反抗神谕的俄狄浦斯。
耶稣的身世似乎是个不解的谜。在犹太人看来,他是上帝派遣来复兴犹太国的弥赛亚,在基督徒看来,他是上帝道成肉身来拯救人类的救世主。而除了更像文学,不像历史的四篇福音书的记载,有关耶稣生平基本上没有一页档案留世。
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编年史》中有一处提到"基督",称以此得名的教派是一个讨厌的教派,发源于犹大省,又传入包纳了一切污垢的罗马。但也仅此而已。但是《约翰福音》显示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反之耶稣出身的崇高,足以同上帝比肩。
由此我们看到了气势恢宏的另一种创世模式:"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1:1-4)
上文道(Word)一语在希腊文是"逻各斯"(logos),逻各斯最早由赫拉克里特引入哲学,是为宇宙的根本大法。但诚如"理式"(eidos)的本义是形相,即便它是在心而不在目,逻各斯同样有一个感性的最初涵义即言说。
德里达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柏拉图以降西方理性中心主义的别称,着眼点即是他所谓的以言说压制文字的西方全部语言乃至文化的历史。道可道,非常道,逻各斯是上帝之言,它不但包括说出的话,而且包括未有说出的话,这就是理性。
此外逻各斯固然不能说是有人格的,可是也很难说是没有人格的,这就为基督教三位一体理论提供了灵感。"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1:14)逻各斯道成肉身即是耶稣基督。"道与上帝同在",意味耶稣有区别与上帝。"道就是上帝",意味耶稣在最充分、最完全的意义上,就是上帝本人。这如《罗马书》所言:"他(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上帝。"(9:5)
可以说,《约翰福音》以上创世描述或者说耶稣降生图式,是在很大程度上将希腊的理性传统和希伯莱的神秘传统合而为一了。耶稣的崇高因此在这里更为清晰地显现出精神的必然性和超越性。值得注意的是"生命"一语在《约翰福音》中出现频频达三十六次,而在《新约》其他篇章中最多不超过十七次。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意味耶稣就是生命,就是光,他同时具有一切人的品质和神的品质。同卷书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8:12)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14:6)这一舍我其谁的气概虽然并不多见于平日里更多谦卑和忍让的耶稣,但由此我们读出了耶稣藉光照亮世界的那一种神秘的崇高。那正是上帝君临天下的风范。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通览《圣经》,这无疑应是基督教苦难意识中最典型的崇高范式。事实上耶稣个性中有刚愎的一面。他曾经用鞭子清洁圣典,《马太福音》中他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我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10:33-34)这极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气概。但是耶稣最终用他的鲜血清洗了他多少显得有些喜怒无常的性格,在殉道中显现出精神超越的崇高。
耶稣死得极其痛苦,绝然没有苏格拉底之死的安祥和宁静。除《约翰福音》,被称作《同观福音》的其他三篇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最后泣血的生命之声:"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8:46)耶稣的悲声在这里使我们再一次想起约伯的悲声,神秘信仰这一耶稣在屈辱和苦难中的唯一支柱,是开始动摇了吗?
比较《旧约》中的圣父,我们发现耶稣身上发散出更多的人文精神,上帝耶和华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至高无上神,人类天机莫测,只能诚惶诚恐。耶稣虽然也从他父亲身上继承下刚烈的血统,表现为现存制度的一个不屈的叛逆者,但是他慈祥、温和、宽容、富有同情心。
他仿佛遥在天边,又似乎近在眼前,而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耶稣的崇高,表现在对苦难人生的一种坚定的超越信念。正是在他毫无尊严的极度痛苦的死亡之中,耶稣表征了崇高在其普遍意义上的畏惧和超越的典型特征。
它不同于希腊美学中的崇高范式。这一点黑格尔看得清楚。据他的解释,耶稣之死表明一方面世俗的躯体和脆弱的人性由于显示了神自身而得彰显且受到尊崇,但是另一方面,此种躯体和人性是在作为否定面且在痛苦之中而得显现,这就和古典理想中肉体和精神两相和谐的审美理念见出了区别。
故而,"基督受嗤笑,戴荆棘冠,背十字架到刑场,忍受殉道者的苦刑和拖得很久的死,这一切都不能用希腊美的形式去表现。
在这种情境里伟大崇高的是神性本身,是深刻的内心生活,是精神中永恒的无限的苦痛,是坚忍和神的宁静。"黑格尔没有说错,耶稣的悲声由是观之,毋宁说是以耶稣肉体形式的痛苦否定,警示了人类可以怎样使他与生俱来却容易被忘却的苦难意识见出神性。在这一神圣和世俗的剧烈冲突中,脆弱的肉体和人性虽归消亡,但是它可以揭示,人类亦将经历一个痛苦的否定过程,而最终有可能实现精神的自由。
综上所言,《圣经》的崇高美学特征相吻于崇高作为美学范畴的一般特征即超越。它分别表现为上帝全能全在、超越了一切世俗知识形式的绝对;表现为神性和人性不能相提的神的公正,以及人类苦难中的悲声和这悲声终而得到神的嘉许;并且,表现为挣扎和极度的痛苦中精神对于肉体的最终超越。
从上帝创世到约伯故事到耶稣殉道,其间崇高的范式可见出从神秘向人文过渡的倾向,而这一倾向,正不妨视为《圣经》从犹太教到基督教经典确立过程中可予探考的美学意蕴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