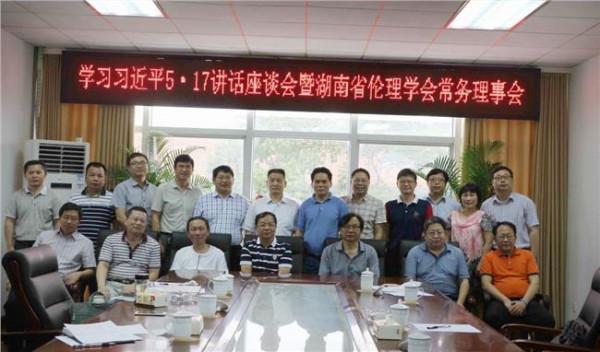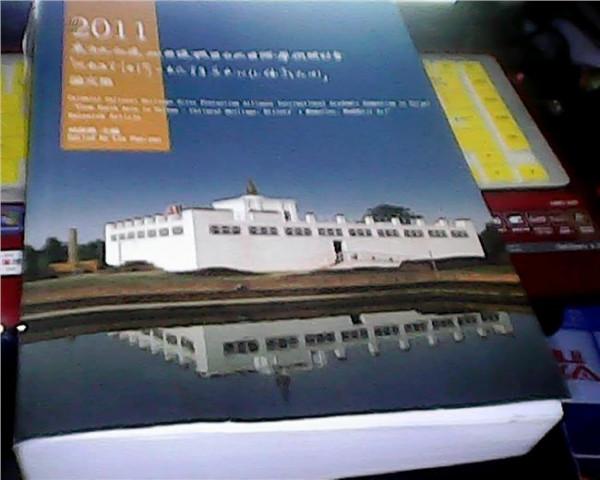北京大学陆扬的妻子 王汎森北大演讲:人的消失?!二十世纪史学的一种反思
3月14日下午,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先生发表了他做客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计划系列演讲的第三讲:人的消失?!——二十世纪史学的一种反思。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陆扬教授主持演讲,演讲结束以后,王汎森先生还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罗志田教授展开对谈,并接受了在场听众的提问。
王汎森先生提出,这一讲的题目是他个人非常关心的问题。他认为,历史很重要的任务在于记录这样的过程: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即使在结构性的力量强大到使人以为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还是有人相信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将局面扭转过来,并且从中得到勇气和智慧。
王先生认为,这既是史学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促使他思考这一讲的主题的来由。哈佛大学一位新近故去的著名中国史家曾经向他提出,写历史提到人名应该越少越好,只有人名少了历史才是硬的,如果人名多了历史就是软的,对此他完全不能认同。
在题目中,王先生用了一个问号和一个叹号,意在表示这里并不是要对“人的消失”表示认同,而是想要强调史学中言说这一问题的脉络。这一脉络逐渐形成一种期待,使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多人都相信好的史学就应该是这样的。
这一讲主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在20世纪史学一波一波的革命中,对于非个人性、非人格性力量(Impersonal Force)的发现,包括结构的发现、语言学转向等等,包括国内的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是强调团体、社会,认为在历史中并不是一两个人在发挥作用。
第二个部分则是要介绍1960年代以后产生的“人的消失”或者“人的死亡”的呼声,包括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宣称人的死亡,布罗代尔宣称“人只是历史的泡沫”等等。
一、传统史学中“人”的角色与分量
王先生首先从传统中国史学讲起。按照梁启超的讲法,传统史学就是“人的史学”,钱穆也反复这样强调。王先生提出,从《尚书》到《左传》,其实就是一个由记事为主转到以写人为主的过程。他随后介绍了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观察。
普实克认为中国史学从《史记》以后都像是一个一个盒子一样,如《史记》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裁,就是把材料储存在不同的盒子里。而西方自希腊罗马以来的史学却是像河流一样,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从古至今写下去。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王先生随即指出,中国史学自《史记》以来渐渐以人物为主体,以至于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唐代李延寿写《南史》、《北史》,主要的部分就是传,他可以牺牲掉别的盒子。人们在评论历史的时候,也都是要以评论人物为主,远如宋代叶适的《习学记言》,近如已经进入二十世纪的蒋百里,都是如此。
二、梁启超的观点及变化
王先生提出,史学中特别看重“人”的情况从梁启超开始有了变化。在1901年到1902年间梁启超写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这两篇文章的时候,他很关键的看法是认为《二十四史》都是写相互砍杀的“相斫书”,认为只有写团体、写社会才有历史性,写个人则没有特别的意义。这其实正是间接提出对以人物为主的史学传统的批评。
到了1920年代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时候,梁启超的看法已有所改变,他对于自己早期的很多史学观点都加以修正。早期他认为历史书写一定要符合所谓“公理”和“公例”,此时则注意到历史上还有“首出的人格者”,也就是重视个人的作用。
以明代思想为例,梁启超认为王阳明的出现就足以概括他之前的时代是滞后的。在他看来,首出的人格者在历史上有百人以上,所以写百人就足以把历史上的若干问题讲清楚了。所以可以说,虽然是从梁启超开始否定个人的作用,但是也是他本人在后来有了很大变化,沿着新的意见做了很多工作。
王汎森先生介绍说,梁启超所谓“首出的人格者”,是说其言行要形成史迹,也就是要改变社会。这个人和他所掀起的一阵风,要对于社会有直接的作用。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历史中的人物,不然还是不值得写。在梁启超看来,历史界和天然界有着截然的分别,历史里含有意志,是会改变的,天然则是始终不变的。
王先生引歌德的名言来形容梁启超所谓的天然界是“西沉的永远是同一个太阳”,提出虽然在当代史学家看来,因为生态的破坏,似乎天然界也有它的历史了,但是在梁启超那里有很清楚的界定。
三、新史学
王汎森先生认为,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近代中国史学的主体是以历史考证和客观性重建为目标的新史学。新史学的领导者是北大派,包括在北大任教的胡适,以及北大毕业后来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等人。
他们一派所倡导的新史学,基本上是以问题为本位的史学。新史学还有另外以何炳松为代表的一派,是以事情为主的史学。何炳松在很多地方都讲到,中国史学只有纪事本末一种体裁符合西方近代的史体,就是因为纪事本末是以事情为主。所以像清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因为是以事情而非以人为主,能够与西方呼应,在近代也就提高到相当的位置上来。
回到胡适、傅斯年这一脉络,他们曾经反复讲史学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王先生这里举辽金史专家陈述给傅斯年的信来说明新旧史学观念的差异。陈述对傅斯年讲,他在进入史语所以后才发现以前老先生们是以一本一本书为主体的历史,史语所则是以问题为本位的历史,写文章都是为了解决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
傅斯年自己的说法则可以看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最后的三句口号,第一句是“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王先生认为,这里面就有非个人性的味道,傅斯年并没有反对传统史学,但是从他几篇重要的文章来看,他认为传统史学都只是材料,真正要书写史学,还是要写以问题为本位的史学。
王先生还提到,他的著作《傅斯年》最早以英文出版的时候,有评论将傅斯年与1940-50年代英国的史学大师路易斯·纳米尔(Lewis Bernstein Namier)相提并论。纳米尔提倡群体学研究(Prosopographical Study),提出要把心性从历史中拿走(Taking Mind Out of History)。傅斯年没有纳米尔那么极端,但是从这种意见也可以看出傅斯年在史学上的偏向。
胡适在《胡适文选》自序里面曾经写道,有人认为他不重视个人,这一点他不能承认,他认为自己其实是非常重视个人的。王汎森先生指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批评,就是因为当时持传统史学观点的学者不适应新史学以问题为本位的观念。可是后来翦伯赞又借这一段话来批评胡适太重视个人,不讲群众的力量,王先生认为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史学观念的更迭。
四、左翼史学
王汎森先生认为,左翼史学在讨论个人和历史关系的问题上,最具启发性的著作当属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普列汉诺夫提出,要把个人和历史规律结合起来看待。他不同意一般认为个人就代表着偶然性的观念,而是相信在历史有其必然规律的同时,个人也可以在这个规律里面尽情跳舞,发挥他的作用。
如果不是二者刚好洽和,历史就不会以实际发生那样的方式呈现出来。王汎森先生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讲法非常细致,而且很有分寸感。
讲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王汎森先生认为其中最有贡献者之一是李大钊。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思想的变动要从社会经济的基础来看,这与胡适他们有着很大区别。但是李大钊也注意到这一股史学潮流太过轻视历史中重要的个人。
他批评当时一些历史课本和通俗读物为了追求历史的客观性,讲汉武帝的时候不讲汉武帝要讲汉初时期,讲商鞅变法要改叫秦代变法,讲亚历山大大帝不提他的名字而讲成马其顿如何如何。他不赞成这样的办法,所以一方面介绍社会经济史,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一方面也反对过度抹杀个人。
王先生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最具代表性的例证当属柳亚子与早期共产党领导人恽代英的对话。北伐期间柳亚子因为太痛恨蒋介石,曾经向恽代英提议把蒋介石刺杀掉,恽代英却回答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相信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杀他没有用处。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只是当时社会关系下的产物,换成另一个人也是一样,只有契合历史发展的实际规律,才能有所成就。王先生认为,历史的实际走向也许并不如此绝对。
五、钱穆等人的驳议
王汎森先生随后介绍了钱穆对于史学中人的问题的意见。在钱穆看来,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等新的史学观念通通都不对。王先生指出,钱穆并没有专门讨论过史学中人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会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反复出现。钱穆不太批评梁启超,也许是因为他本人受梁启超影响较多。
比如他也同样会强调历史人和自然人的区分,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在历史上发挥作用就是自然人,如果发挥了作用就是历史人。但是对于发挥作用的界定,钱穆有很有意思的看法。
王先生提出,章太炎曾经批评纪事本末体只写大人物的历史,忽略小人物的作用,认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很多事情其实是小人物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钱穆没有受到章太炎的影响,但是他们有近似的观念。钱穆说历史上有一些人,虽然没有经历过可以写在纪事本末里的大事,却对历史有很大的影响。
王先生将钱穆所指的这种影响概括为“历史的潜势力”。比如说孔子在《左传》里不过只有几句话的记载,颜渊就根本没有出现,可是孔子和颜渊对于历史却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反而是《左传》里着意描摹的许多人在此后却没有影响了。
再比如三国时期的隐士管宁,王先生笑称他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逃跑和躲起来,可是管宁对于后来人同样有很大的影响。还有时失败者会比成功者更有影响,比如文天祥就并没有做到他想要做到的事情。如果以事情作为历史的单位,那么他们就不重要,但是他们在历史上却形成了一种潜势力,在事情的舞台后面的台子上施加他们的影响力。
王先生提出,钱穆这种关于历史中人的问题的意见,往往是针对胡适、傅斯年、左翼史学等而来的,认为他们都是重物而不重人。而在钱穆看来,对于人的重视是传统史学里最重要的部分,甚至史学的本来使命就应该是要写人。他总结希腊罗马灭亡的原因,就认为应该归咎于他们的史学不重视人,所以在没落以后没有可资借鉴的办法来挽救。
王先生发挥他对于钱穆的理解,认为钱穆应该会觉得,近代的史学像是一场足球赛,没有人在踢球,只看到球在跑来跑去。在钱穆看来,太谈社会经济、结构、地下史料等物的层面,都会破坏他理想中的史学。王汎森先生提出,他赞成钱穆对于人的重视,可是不能够赞成他这种“以上皆非”的态度。
六、1950年代以后世界(史学)思潮中“人”的问题,以及它们对华人史学界的影响
对于这一问题,王汎森先生认为应该另外做专门的讨论,这里只介绍一点基本情况。他认为,西方史学本来就有重视事情的传统,尤其在19世纪以后,往往相信历史发展自然有其模式与规律,因此并不重视人的层面。可是在1950年代以后,几种大的史学思潮都跟人的逐渐消失有关,甚至主动提出要把人取消掉,这就更是一种新的发展。
王先生认为,1950年代以后与 “人的消失”相关的西方史学思潮主要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新归来;二是社会经济史的过度强调;三是由下而上的历史的兴起。
二战以后,很多历史学家回到左派史学的立场中来,将人看作复数的人、集体的人。王先生举邓之诚的经历来说明。邓之诚1956年的日记里曾经写到,他读报看到俄国《真理报》提出崇拜个人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行为。这使他非常惊讶,因为他是属于传统史学的观念,认为人非常重要,而在当时,重视人却已经成了反马列的行为。
在上述三个方面以外,王先生认为对于“人的消失”更为重要的,是后面他将要论述的三种思潮:一是结构主义史学;二是年鉴学派;三是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的史学思潮。
七、结构主义
王汎森先生提出,结构主义反对人文主义,认为结构先于个人存在,结构里面所有的意图、心智、规划、行动都只是结构中的关系项而已,都要受到深层规律的制约。这就带有很强的反历史主义的倾向。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列维·施特劳斯
(Claude Levi-Strauss)就认为,历时性的探索本身没有太大意义,应该更注意从共时性的结构中发现规律。这种影响反映在史学里面就是人的去中心化,包括年鉴学派在内的很多史学家都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
八、年鉴学派:人是历史的“泡沫”
王先生认为,年鉴学派深受涂尔干的影响。涂尔干强调集体的再现,关注社会事实,影响到年鉴学派的很多方面,其中就有王先生在第一讲曾经介绍过的心态史的研究。王先生举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著作《国王的触摸》(The Royal Touch)为例,认为这本书讲一种集体的心态反映在相信国王可以通过触摸患者的头来治病的史实之中,这是受到涂尔干的影响才会有的思考。
年鉴学派常常回溯他们所受到的涂尔干的影响,但是在王先生看来,他们的史学观念至少还要受到另外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结构主义,二是他们反对当时法国主流的受兰克史学影响的政治史研究。
当时的主流史学往往认为重要的政治人物是历史中最重要的力量,这遭到了还居于学界边缘的布罗代尔等人的强烈反对。
从以上三方面的影响出发,布罗代尔在他的著作中往往否定个人的重要性。譬如《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全书有两千页,可是真正和其中受世人瞩目的战争相关的内容只有七八十页。布罗代尔认为气候、地理,包括次一级的经济,都要比事件更有力量,事件和人都不过是历史的泡沫。
在《论历史》一书中,他提出人是历史的囚徒,只有长期不变的东西才是真正关键的,它们透过限制来影响历史的发展。布罗代尔说他在巴西的一个晚上看烟火,烟火放上去天空大亮,可是烟火掉下来黑暗马上又攻占了所有,他认为这些烟火就好像是事件,好像是人,不能穿透这深沉的黑夜。所以他认为人是历史的囚徒,是泡沫,强大的都是长时段的因素。
九、福柯“人的死亡”
王先生随后介绍了福柯“人的死亡”的讨论。福柯认为,“人”是很晚才发现的观念,是18世纪以来的建构。而且,他对于现代的人文学科系谱有很大的批判,认为几个世纪以来产生的人文学科都没有办法真正了解人,人的意义反而被人文学科联合埋葬了。此外,在《词与物》第九章“人及其复本”中,他又提出人既是被认识的对象,也是认识的主体,这是矛盾的。王先生认为,福柯喊出这样的口号,对于近代西方史学就产生了暗示性。
十、后现代主义
王汎森先生认为,后现代主义同样对史学中人的问题有很大影响。1967年,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编了一本《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使得“语言学转向”受到广泛关注。
后来证明语言学转向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事情,并且在80-90年代给史学以显著的影响。王先生提出,后现代主义认为语言先于人的意图而存在,自有其规律性,所以人是不重要的。受到语言学转向影响的历史著作,往往对于人的主体作用感到怀疑,甚至有世界知名的史学家,在提到人的时候都要扭扭捏捏。
不过,后来西方重要的史学杂志《历史与理论》(History of Theory),曾经有一期在几篇文章里提到新文化史似乎有一点使得人的地位重新得到肯定。王先生指出,新文化史认为,世界上有很多结构一样的网格(grid),是没办法改变的,但是人作为一个主体还是可以透过它们去完成一些事情。这的确是承认人还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主动性。
十一、其他的观点(如“小历史”)
王汎森先生提出,对于他上面讲到的“人的死亡”、“人是历史的泡沫”一类的看法,很多西方史学家也不能够认同,这其中就包括一些意大利史学家发起的“小历史”(Microhistory)。这不仅是针对年鉴学派,也是针对当时社会科学影响下的历史研究,认为他们都只顾从大的局面着眼。
小历史强调个人非常重要,代表人物有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等人。王先生提及他曾经请教金兹伯格对于布罗代尔的看法,金兹伯格就表示乔万尼·列维曾经提出,布罗代尔的书虽然好,但是里面没有人。这代表了一派史学家对于人的问题的反省。
十二、“人”的复返,以什么方式复返?我们能假装近百年的新历史思潮都没发生吗?
王汎森先生认为,20世纪了不起的史学著作大多表现出没有人的特色。像埃里克·沃尔夫(Eric R.Wolf)的名作《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里面讲到一些很小的人,可是当时欧洲对这些人产生最大关系的重要人物却不出现在他的书里。
所以有书评以为,书名是“没有历史的人”(People Without History),作者实际上写的却是“没有人的历史”(History Without People)。
王先生提出,年鉴学派到了第三代,其实也开始越来越重视人的作用。按照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法国史学革命》(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里的介绍,年鉴学派的发展是“从地窖到阁楼”。
原来在地窖时否定人的作用,后来到了阁楼则发现人的重要性。于是在1990年代前后,年鉴学派也开始写人物的传记,包括勒高夫写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传记《圣路易》(Saint Louis)。可见即使在西方思想最否定人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不以为然,提出反对的意见。
王先生郑重提出,史学很重要的任务是还要有历史的教训,对于历史人物要有道德的苛责。如果人在历史中没有作用,希特勒也只是德国景气循环的产物,那么德国大部分人都要负有历史的责任。可是如果承认希特勒的作用,那么就是希特勒和他的群体要负很大的责任。现代史学不再重视历史的苛责,不再重视历史的教训。但是这毕竟是史学重要的原始的目的,是史学应负的责任,应该在史学家的考量之中。
最后,王先生提出,我们不能对20世纪史学里面对非个人性、非人格性力量的看重视而不见,就像讨论今天的文化,不能假装五四运动没有发生过。但是即使是有大的结构性的力量,如果不考虑孔子、朱子、王阳明这些思想家的作用,也就没有办法讲思想史的问题。
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既看到结构的阻力,也看到个人的努力。关注个人与结构、与长时段之间的关系,在对结构有充分体认以后,重新把人考虑进去。这是他个人对于这一百年来史学发展的反思和想法。
陆扬教授总结他聆听这三场演讲以来的感受,认为如果只将王汎森先生看成是一位专注于思想史的学者,那无疑是非常狭隘的,因为他关注的其实是思想的力量在历史中如何发生作用的问题,这是所有历史研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
陆扬教授认为这三讲有一个内在的脉络,就是重视思想的潜流和潜力,以及思想的层次,而且这也不是以往的只以重要思想人物为对象的思想史,研究中并不先行规定哪种思想资料更有优先性,而是更全面地分析思想渗透的途径。
陆扬说王汎森先生善于运用比喻来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的能力,也给他以很深刻的印象。他还认为,20世纪专业史学中人的消失,除了意识形态等原因外,史学的职业化本身也是重要的推助力。如德赛图(De Ceateau)强调的,过去的历史观是连续的,今天则是中断的,史学的职业化是以过去的纯然客体化为前提。
现代史学发展出来的种种手段几乎都是为结构性和群体性分析服务的,各类专业工具越来越不适用于分析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或对历史产生的作用。
传统史学中那些描述个人影响的语言大都被当作过于主观或文学性而遭到排斥。同时正如科塞雷克(Koselleck) 所言,史学中过度夸大历时性也必将导致人的能动而积极的存在失去了行动的空间和余地。但这也造成在流行的大众史学著作与专业史学之间产生巨大的鸿沟,因为前者仍以历史人物的叙事作为骨干,这种差异事实上造成了专业史学的边缘化。
要想突破这一困境,使得史学重新拥有它19世纪末以前的功能,王汎森等学者采用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也许是一个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