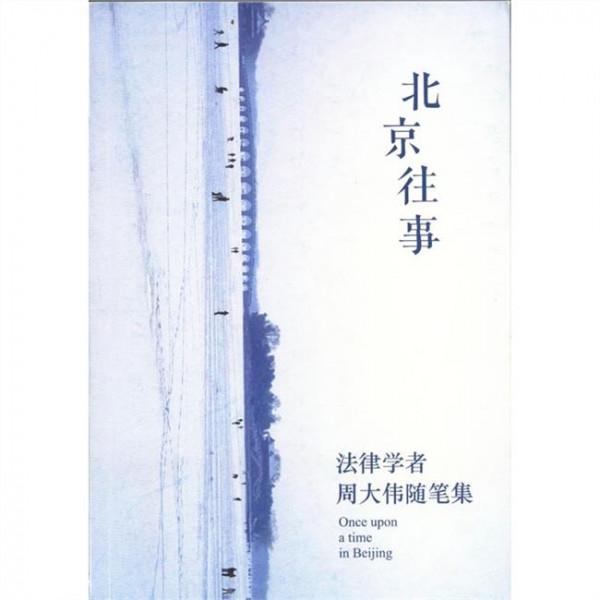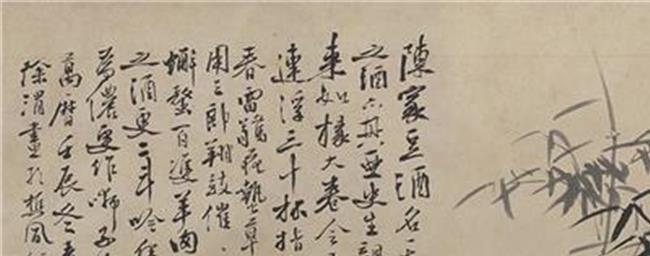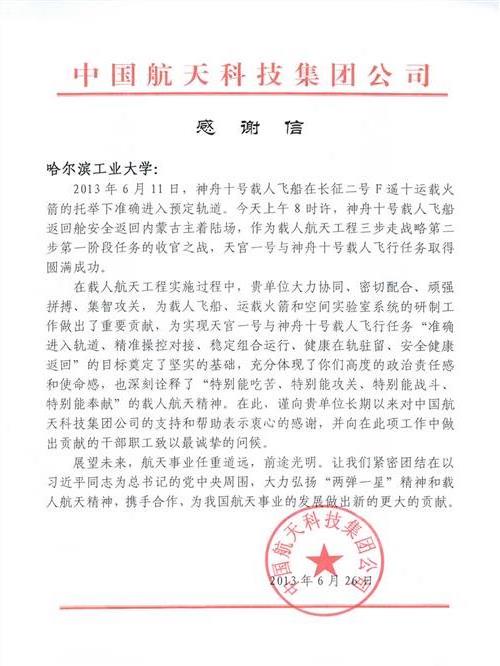周大伟衡阳人 周大伟:一个中国法律人的希望和困惑
2012年11月19日上午10点05分,我在书房里校阅完《法治的细节》样稿的最后一页,把样稿交给已经在楼下等候的快递公司员工。随后,我拖着旅行箱乘车前往飞机场。一个小时后,我将在那里和北大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回合。
今天,我们一起结伴飞往的目的地是:江苏无锡。在风景绮丽的太湖岸边,有些朋友在等候我们来参加一个聚会。 邀请我们前来无锡的朋友中,有些是资深的律师,有些是当地普通的政府公务员,还有些是年轻的公司白领和退伍军人。
其中的大多数人,我们还都是第一次相识。只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直接或间接地聆听或贺教授的精彩演讲,也有人阅读过我的那本不太畅销的法学随笔集 —— 《北京往事》,这算是为我们的“一见如故”投下了有趣的注脚。
听他们在席间的谈吐,大多怀揣卓见。在这个历来不那么太关心“国家大事”的富庶江南城市里,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此地竟然“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思想的交流未必需要某种通常意义上的形式。思想难以被遮蔽,它像眼前的浩瀚太湖水一样,只要有机会,就会悄悄地找到自己的去处,流向大河小渠,义无反顾地完成表面上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沟通。
社会在转型,人心在思变。无论走到哪里,不难看到众多朋友们都拥有非常相似的价值观。
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尽管大家都带着各自的希望和困惑,但是人们在一个终极目标上正在达成共识 —— 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其实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只有用法治而不是人治的方式,才能最终降伏这个千百年来充满悲剧宿命的庞大国家。
司法是一种相对保守的力量,具有天然的渐进特点。从国家平稳转型的意义上看,司法改革可能是目前风险最小、成本最低的途径。只有法治思想在中国普及,才能让中国人继续坦坦荡荡地活下去,中国才有国泰民安的可能。
其他的“老路”或“邪路”,不是历史的误区,就是资源的浪费。 对于中国法律人来说,如何为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贡献一份力量,如何让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少出现流血和暴力,如何达成不同阶层、阶级、民族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和解,这很可能是一条“吃力不讨好”的道路。
我们很可能像是中国象棋中的过河卒子一样,只能“勇往直前”,除了“东躲西闪”,没有了退路。这种类似每天都在用水滴石穿的方式推动社会的进步的情形,相对于近一百年来中国人“比赛谁更激进”的图景,太容易使人失去应有的耐心。
法治社会的构建是个艰苦和漫长的过程,需要严密的制度设计、繁琐的运行程序和高昂的维护成本。我曾遇到过一些法律职业同行,他们或曾大声呐喊,或曾奋笔疾书,或曾行走南书房给高层领导授课。
使他们常常感到沮丧的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自认为绝妙的治国建言往往被束之高阁。他们的热情很快降温,他们或者开始捧读起易经和老庄,或者打算在大城市的郊区找一块农田,春耕秋收,自得其乐、与世无争。
中国改革和开放的大业,最开始几乎是从台湾邓丽君小姐的歌声中获得人性启蒙的,可见起点之低,同时也不乏预示着一路行来注定要经历的艰辛和坎坷。
对于中国法律职业人而言,我们不得不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艰难地去体验西方国家数百年来在法治文明中创造的所有关键词。时代实在太匆忙了,不容我们去潜心实验,必须在启蒙之初就做出选择。老一代人历尽沧桑,此刻已经力不从心;年轻的一代先天不足,步入成年时才开始理解常识。
这意味着,启蒙的意义固然庄严和深远,启蒙的过程却过于粗糙和机械,由此导致了思想的苍白和缺席。 然而,法治启蒙运动在中国如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难以阻挡。
用前不久辞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的一番话来说:“启蒙运动的价值,也即伏尔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孔多塞这些人提倡的东西深深感动了我。他们也许太褊狭,对人类的经验事实往往也会判断失误,但是他们是伟大的解放者。
他们将普罗大众从恐怖主义、蒙昧主义、狂热盲目以及其他荒谬绝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们反残忍、反压迫。他们跟迷信无知以及许许多多败坏人们生活的勾当进行了一场胜利的战斗,因此,我站在他们一边。
” 在中国,这场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并由体制内和外共同发起的法治启蒙运动,一路遭遇坎坷。被呼唤的法治时代并没有如所预期地那样顺利分娩和繁荣,它的出现一再被延宕,甚至倒退。诚然,中国的社会环境较之二十年前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打破专制主义出发而建立的理想,在今天又碰到了理想主义最大的敌人:物质消费主义。
当年那种由于被压抑而激发出的理想主义的激情,在重商时代可能会变得迷茫和扭曲,对于中国法律职业人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然而,近百年来,绵延不绝的思想脉流从来没有中断,即使在极为严酷的年代,也有人不顾危难做着他们认为应当做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都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人的名字,他们选择了另外一种生命形式。
我有时在想,如果今天的中国的法律界没有江平没有张思之没有贺卫方,大家的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不必讳言,那一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景。 在中国,有很多并不尊重法律的人在大谈所谓“有特色”的法律思想,这些“法律思想”的共同特点就是基本上与真正的法律无关,它们仅仅是一种把法律作为工具并进行意识形态图解的说辞。
同时,我们也奇怪地发现,周围的一些年轻人,对数百年前的“明朝那些事儿”或“唐朝那些事儿”,乃至皇帝后宫的那些事儿,说起来津津乐道,了如指掌。
但对100多年前、50多年前乃至20多年前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很多事情,则知之甚少。澄清这一切,或许还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历史不容纳杂质,所有需要被荡涤的杂质最终都将被荡涤干净。
或许是性格过于温和,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成为一名斗士。在这方面,我发自内心地敬佩贺卫方教授在公共领域内一如既往的坦然和敢言。生活在这个现实环境中,我们都感到深深的压抑和不安。
到底是应该不断地大声表达抗议,还是暗喻及婉转地去耐心建构,没有人说得清哪种方式更重要或是更有效。目前而言,它更像是由于不同性格所带来的个人选择。 中国法律职业人面对的现实显然并不完美,但却依旧值得我们留恋,我们总觉得还值得为它继续努力,因为我们除了怀有几分天真和执着外,还能得到这个世界不算太吝啬的惠顾,就像是人们在饥渴的时候总是能遇到甘霖,现在总算是有了一个让那些人敬畏的东西 —— 互联网了,人们开始从中看到法治的巨石在被缓缓地向前推动;还有,有些无视法治、居心叵测的大人物总是在即将得逞之前戏剧性地跌落下来。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无锡这座城市。记得年幼时光,我和祖母曾在这个江南名城里生活过几年。
如今,早年无锡城里那些漂泊着大大小小木船的河道已经被填埋,城区里那些曾经被磨出光泽的石板路也已改造成了柏油路,还有,每天早晨在街角拐弯处卖大饼油条的那个苏北师傅也早已不见踪影。整个无锡太湖沿岸,早已经不再是只有鼋头渚和蠡园的时代,如今已经规划为一个庞大辽阔的风景区。
到处是豪华的酒店和私家别墅。在我们下榻的酒店不远处,数年前,当地政府和商人们不惜重金,用最奢侈的材料和最现代的声光电科技手段打造出一个名扬海内外的佛教圣地。
每当夜幕降临,这里和中国大多数城市里的景象一样,大大小小的酒楼里都人声鼎沸,歌舞升平。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成功和富有的人们,似乎预见到这个国家总是坎坷踉跄的运行轨迹,他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移民海外,在获得某种“保险”后,又开始像候鸟一样往返于辽阔的太平洋两岸。
周围的人们都在不停地指责并赌咒着这个时代的荒诞和制度的缺憾?人们并不愿意多想,假如,一个社会的法治防火墙尚未建成之时,即便这个制度有一天轰然崩塌,是否就意味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的到来?眼前这些正在餐厅里享用美餐的人们,是否仍然可以继续保持今天的生活质量或体验到更安详的生活? 此刻的中国,像是个硬币的正反两面:既有物质的丰富和诱惑,又有思想的苦闷与压抑。
我们既不能责备其中的虚浮和荒诞,也不能责备其中的懦弱和逃避,因为它们同样真实。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都是传统和现代交汇而成的千万条溪流中的水滴,大家同在路上,同在一个社会环境中,命运把大家牵了在一起。
此刻的街道上,正到处张贴着冯小刚执导的《一九四二》的电影海报,战争和饥荒的年代似乎早已离我们远去。21世纪对中国而言,到底是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纪还是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纪,人们还在争论不休。
不过,我们乐观地注意到,每天中国人都在面临着一波又一波汹涌而来的新问题,而且人们又愿意竭尽力量,用文明的方式而不是用野蛮的方式,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这就说明我们今天还算生活在一个前途光明的时代。
带着各自的希望与困惑,朋友们在深夜的街头分手告别。一年的尾声即将来临,这些希望和困惑还将伴随着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我们相约在明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再次来到这里相聚一堂。
这本书中所收集的文字,主要是我在最近三年里为“两报一刊”(《中国新闻周刊》、《法制日报-法治周末》、《南方周末》)撰写的专栏作品。不知不觉,竟积累成了一本20多万字的文集。这些年里,自己从未奢望通过这些随笔文字去“改造我们的文化”,唯一的心愿是将自己对法治的细节思考,以一己的点滴努力融入众多法学界同仁的合力之中,从而逐步营造一个正常的法律文化氛围。
在坚持写作过程中,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雷莎修女的几句话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你多年来营造的东西,有人会一夜之间把它摧毁,但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去营造。
(What you spend years buildings, someone could destroy overnight; Build anyway.
);你今天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但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做善事。(The good you do today, people will often forget tomorrow; Be good anyway.) 【注:本文为《法治的细节》一书的作者后记。】 2012年12月6日 写于美国加州Burling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