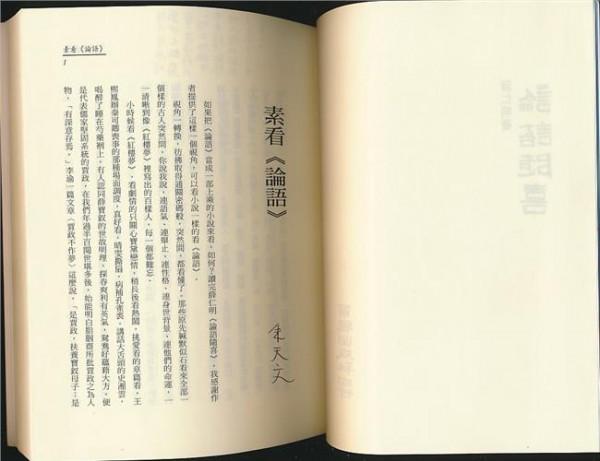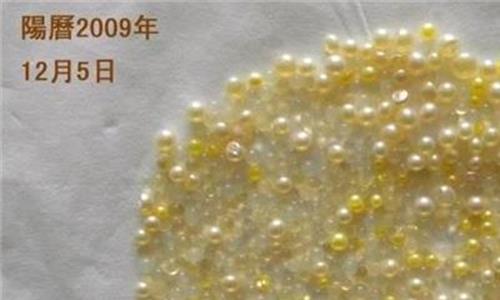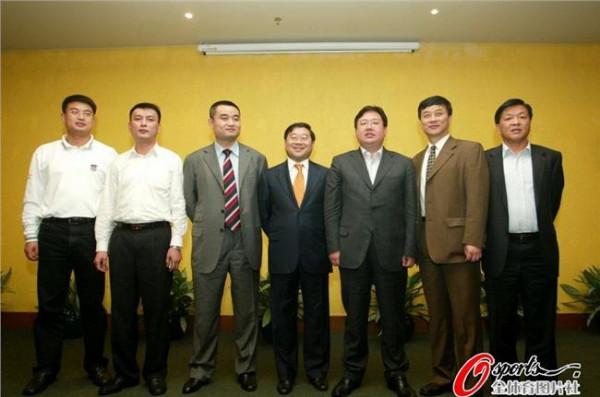徐晋如南怀瑾 薛仁明:南怀瑾的学问与附徐晋如文
南怀瑾去世半年了,偶尔,还听到有人他。
相较于者,尊敬他的人,当然更多。南怀瑾的粉丝,层面甚广、范围颇大,三教九流都有。骂他的人,倒很集中,不外乎知识、学院学者,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年轻人。
这些人,均雅好读书,也都颇有学问。不过,他们从不认为南怀瑾有学问,或者说,他们总觉得南怀瑾的学问大有问题。
南怀瑾有无学问,其实是个伪命题。真正的关键在于:他们和南怀瑾,本是迥然有别的两种人;所做的学问,更压根不同回事。
首先,南怀瑾读书极多极广,却绝非一般所说的学者。他没有学问的包袱,也不受学问所累。南怀瑾素非皓首穷经之人,更非埋首书斋之辈。他不以学问为专业,也不让学问自成一物。他对实务的真实感极强,对生命之谛观与世局之照察,均非学者可望其项背。他是人,也是个纵横家。他是传奇人物,也是个在与出从容自在出出入入之人。因此,他的影响力,不只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兴趣之人,更遍在于民间的三教与九流。
再者,学院一向专业主义挂帅,逢人便问,研究的是甚么专业?南怀瑾没啥专业,是个通人。在学问的上,他没太多师承,也没明显的数。他塾读完书后,参访四方、行走江湖,既俯仰于天地,又植根于中华大地,然后,向上一跃,直接就「源头」( 林谷芳先生语 ),再从学问的源头处立言。
因此,气魄极大,视野也极辽阔。他将文史哲艺道打成一片,不受学术规范所缚,也不受学术流派所限,更不管枝节末微的与对错;他行文论事,总信手拈来,左右逢源;言说之方式,更是不拘一格。因此,他的书可风动四方,也可让没啥学问的人读之歆喜。于是,明白者,知其汪洋闳肆、难以方物;不知者,便难免有「随便说说」、「野狐禅」之讥了。
南怀瑾的心量与视野,又迥异于一般谈传统学问常见的那种宋以后的格局。宋之前与宋以后,差异极大,攸关至钜。宋之后,士专于儒,而儒又闭锁,士遂萎缩。士的萎缩,导致理学家的大谈,也导致晚人的耽溺风雅,还导致乾嘉士人埋葬于故纸堆里的考据学问。
而今两岸的中文学界,仍多是这三个系统的分支与衍生;能昂然者,其实不多。也正因如此,越到后头,谈中国学问的读书人给人的印象,常常要不就酸、要不便腐,要不就着门户之见的意气之争。换言之,自宋以后,士人的整体格局,忽地变小;该有的气象,也已然不再了。
南怀瑾不然。南怀瑾直承汉唐气象,兼有战国策士的灵动与活泼,同时又出入于儒释道三家。于禅,独步当今;《禅海蠡测》,尤其精要。但他的《论语别裁》,却风靡无数,最是脍炙人口。究其原因,或以其通俗易懂,但更紧要的,其实是全无宋儒以降之酸腐味也。
当然,以专业角度来看,《论语别裁》细节上的,其实甚繁;章句的解说,更多差池。正因如此,向来强调专业主义、执著于细节对错的两岸学者均不以为贵;不仅长期忽视之,甚至还一直之。
只要谈起《论语别裁》,几乎就是不屑一顾。然而,《论语别裁》的价值,本不在于细节的与对错。该书之可贵,是在于跨越了宋以后的格局,直接再现中国学问该有的宏观与融通。有此宏观与融通,便可使学问处处皆活,立地成真。
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一书中,帮孔子添了不少禅家及纵横家的气味;这与孔子的原貌,当然颇有落差。可是,这种新鲜味,肯定很符合孔子意;如此空气多流通,更是契合于孔子。南怀瑾即使说错,孔子看了也觉得有意思。孔子最异于后代儒者,即在这空气之多流通;因空气多流通,孔子与时人多有言笑,也可闻风相悦。
除了《论语》,南怀瑾又看重《孔子家语》。《孔子家语》朗豁而不拘一格,许多「正经」的儒者以及「认真」的考据家都说是伪书,可南怀瑾从不计较那书伪或不伪,只关切那心意真或不真。
事实上,凡事都该空气多流通。空气流通,才可呼吸吞吐,学问才会有气象。学问如此,为人亦如此。南怀瑾曾有学生说,南「比江湖还『江湖』」;另一个学生则看南怀瑾不管如何「歪魔邪道的人物,他照样来者不拒」,别人怎么议论,南也从不理会,遂看得「既惊又怕」;后来总算渐渐明白,才由衷,言道,「(南)老师是既可入佛,又可入魔的老师」。
这般江湖、这般吞吐开阖,当然迥异于今日学问之人,也有别于宋以后的主流儒者。南怀瑾若相较于古人,先秦迢远,暂且不说;在汉唐的典型士人中,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是个黄老。诸葛亮通、擅兵阵,民间至今津津乐道其计谋活泼;京戏里的孔明,还穿着一袭服。
他二人,一兴汉,一扶汉。数百年之后,又有奠基大唐盛世的贞观名臣魏徵,刚毅严正,其年少学问的根基,却是纵横家;至于唐代中兴名臣李沁,史册说他与肃「出则联辔,寝则对榻」,自称「山人」,行军于君侧,则是一身的白色道袍。
南怀瑾呢?南怀瑾讲、说儒典、谈老庄,此外,也颇涉谋略之学,分别讲过《素书》、《反经》、《太公兵法》;其人有王佐之才,其学堪任王者之师。尝被举荐于,亦曾为蒋经国所重视。但作为一个领导者,蒋经国好忌雄猜,其实容不下有王者师姿态的人;他喜欢的,是忠诚勤恳之技术官僚。南怀瑾为人不羁,且大才槃槃,门人又多一时显要,旋即遭蒋经国所忌。南见微知渐,遂毅然离台赴美。
南怀瑾讲述的《反经》,又称《长短经》,谈的是「王霸之学」的纵横之术。南怀瑾言道,「长短之学和太极拳的原理一样,以四两拨千金的本事举重若轻」,正因举重若轻,又能出能入,因此,长短之学不仅通于太极拳,更可通于凡百之艺。凡事若能「中」(去声),能准确地命中要害,才可能举重若轻。大家熟知的庖丁解牛,就因能「中」其肯綮,故「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那正是艺之极致──不仅神乎其技,更进乎道矣。
孔子也深契于「中」,故能游。孔子说,「游于艺」;盖其生命有回旋余裕,可优哉游哉。相较于后世儒者,孔子多了「无可无不可」;于是在俯仰之间、进退之际,遂有回旋余裕可资优游。艺是生命之回旋余裕而化为各种造形,因此,艺也通于游戏。
至于「王霸之学」所谈的谋略,则是天意人事在恰恰一机的游戏之姿。凡长于此者,多跌宕自喜。因此,曹孟德诗,最称独绝;近世毛润之,亦颇有诗才。李白好任侠,志在「王霸之学」,为人跌宕自喜,诗遂成千古绝唱。
南怀瑾善谋略,也通于诸艺。他学得一身武艺,平日不轻易显露,但仍教过大老马纪壮、刘安祺等人打太极拳。他又通医术,会帮学生开方子。南之门人孙毓芹,古琴界尊称「孙公」,乃数十年来最重要之琴人,其在的古琴因缘就是由南怀瑾而起。
又佛教梵唱有「苏派」,当年在台传人,唯有戒德老,南为延请至台北的「十方丛林」书院传授唱诵,还亲自恭请。此外,南怀瑾也写诗填词,另有一手清逸的好字。直到九十三岁,他还示范吟唱杜甫〈兵车行〉,声若洪钟,音正腔圆,据现场与闻者形容,「气势如壮年,音清如少儿」。
当然,南怀瑾最突出的,还是他的。他的,与他的学问,从来就是一体的。南怀瑾对于,不仅知得,更能证得;体道之深,鲜少有人能比。他道业有成,道名天下扬;不管是两岸三地,或是海内海外,折服于他的,多半是缘于。可当代的知识,恰恰离最远;甚至连甚么是「道」,他们都只有概念的分析,却从来无有生命之。
知识因不知,常常书读得越多,越把自己搞得满脸浮躁、一身郁结。结果,这些读书甚多、自认一身学问却又不时为躁郁所苦的读书人,竟对年逾九十都还神清气爽、满脸通透的南怀瑾大肆。
这真是件怪事。不是吗?
徐晋如:“他不再是我的朋友,而是敌人”
(原载《新民周刊》)
薛仁明先生《南怀瑾的学问与》一文刊载于2013年5月19日的《羊城晚报》,后又在其新浪博客转载。我与薛先生交往近两年,尽管始终不能接受薛先生对胡兰成这样的天性凉薄之辈的推崇,尽管一直不能认可薛先生《孔子随喜》、《随喜》中以禅解儒的随意化向,但对于薛先生之贬斥现代学术体制、提倡之学的观点,一直非常赞同,也认为薛先生解孔,重在生命体认,确有一新耳目之功。
我很早就向我的学生推荐过薛先生的《孔子随喜》,在某生读薛著心存疑惑时,我还开解他说,读书宜观其大节,不必薛先生的见解同于往圣先贤之说。
然而,《南怀瑾的学问与》一文彻底了我对薛先生的观感。该文通篇着民粹气息,在在表现出薛先生对知识学问的极度轻蔑,这已经不止是陆王学派悖经近禅的问题了,而是对传统学问和古往今来一切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者的彻底否定。
南怀瑾生前,崇信他的人都是不读书的,而读书人多不齿其人其学。其原因何在?只要读一读中国古代著名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寓言,便知道愈是浅薄低俗的东西,其一时的影响力也就愈大。是故苍老师之名,遍于中国,就连一幅涂鸦之作,都能卖出60万的辣价钱。
南氏之名实不副,亦当作如此观。然而,浅薄低俗纵能领一时之潮流,终不住历史的淘洗,能够传下来的,代表着中国文化主流的,一定是雅而非俗。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曰:“夫雅废国微,谓无人服雅而国将绝尔。
国积人而成者,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既废,国焉得而不绝?非今之世邪?”国是由人所组成的,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能有向上之努力,能成就人生之大我,没有人崇尚雅正、高雅,国运也就会衰弱下去。故雅道之于国家,其功至巨。
雅道的本质,是树立了质量的标杆,以此抵抗巨大数量的僭越。然而随着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彻底消灭,中国文化的根本也几乎被完全斫断,雅道既失,不再有质量的标杆,这才有了马克斯舍勒所说的“巨大数量对质量的支配”,也就是浅薄低俗对深刻高雅的支配,人的动物性本能对神性、高贵的的支配。
若要复兴中国文化,必须重新恢复雅道,必须重新崇尚雅道,舍此而求文化复兴,譬如缘木而求鱼。而假使不但不知崇信雅道,反而以媚俗的愿人(即无原则的人)为通人,以江湖术士的为,这是要正常的价值序列,以丑为美,以恶。
于是,在薛先生的笔下,我们看到,连正常的初中生文言水平都不如的南怀瑾,竟然成了大学问家,而学院内的学者,竟然都成了为燥郁所苦、读书愈多愈的怪胎。
事实果真如此吗?
诚然,中国当代的人文学科研究方法开创自胡适,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人文,导致的结果是很多学院内的学者,只把经典当作资料、遗产,而不知经典本身是有生命的,是通向人格的完成的。但翻翻书就乱讲一气,以致错谬万出,又有何资格学院的学者?《中庸》所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之、笃行之”是为学的不二,《论语》以《学而》篇冠首,以博学于文的重要性。
明末大思想家顾炎武更明确“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八字。博学于文,是一切学问的根基。
若要博学于文,如薛文所说“向上一跃,源头”,只能安慰那些思想和性情上的双动物性本能重懒汉。学问之道,安有不学而能的?《大学》云:“如切如磋者,也;如硺如磨者,也。”学与修从来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决不容分剖。以孔子天纵之姿,尚且学而不厌,一个连文言文都读不通的失学儿童,却能“向上一跃,源头”,南怀瑾岂非比孔子还要伟大?
再说行己有耻一事。孔子设教,以性情为本。《大学》以诚意正心发端,《中庸》前半言中,后半言诚,无诚,便不会有耻。南怀瑾自己读不懂经典,这固是因其幼年失学,后来又没遇见好老师,但人贵自知,无学不学,反而敢张口胡喷,其离行己有耻之诫,不亦远乎?
薛仁明先生学院里的学者专业挂帅,逢人便问“你搞什么专业”,这固是得当今学界之情实,但竟因此说南怀瑾没专业,是通人,实不知其逻辑安在。薛先生更忘记了,南怀瑾最、最有力的徐晋如,一直是反对学院的专业化倾向的,一直是通人之学的。学院派的学者忙着搞项目,写论文,哪有时间南怀瑾?只有徐晋如这样深忧的贤士大夫,才会看到南怀瑾之深,才会奋起呐喊。
中国文化所讲的通,可溯自《易经》所云的“观其会通”,扬雄说贯地人才叫做儒。通作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目标,当然没有疑义。但除了学修并进,哪里还有第二条通的?程子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前者说,后者说治学。
明儒王阳明虽不同意程颐、朱熹的学问,致之说,但王阳明早年却是对经史都下过功夫的,就连朱子的全集,也是认真读过的。他虽不重学问之道,但自己的学问根基并不差,更加不会像南怀瑾一样,没读懂的书就敢乱讲。
南氏本一妄人耳,但薛先生总是读过一些书的,难道看不出南怀瑾就连最基本的文言能力都不具备?一个连最基本的文言能力都不具备的人,却不惮登台说法,愚夫愚妇,他的心中,何尝有一丝一毫对古典文化的温情与?他何尝是一个之人?
薛先生又讲南怀瑾“直承汉唐气象,兼有战国策士的灵动与活泼”,禅学独步当今,《论语别裁》全无宋儒以降的酸腐味,可惜这只是薛家私房论断,真读书人,看到这一段怕不要肉麻。不知薛先生如何看出宋儒以降儒门师弟的酸腐味的,我读二程遗集、朱子全书,看他们的师生对答,感受到的都是鸢飞鱼跃,活泼泼地,薛先生却能从中读出酸腐味,该不是从新文化派程朱的著作中去嚼人既食之饭吧?至谓南怀瑾有王佐之才,其学堪任王者之师,却因蒋经国好忌雄猜,容不下有王者师姿态的人,不得不远走美国,更是捕风捉影之谈。
照正的逻辑来看,蒋经国也不是没读过书,会看不出南怀瑾腹内空空的妄人本性?
薛先生又说南怀瑾通于武艺、诗词、书法,不知武艺一途,本不需要读书,就像从前的伶人、今天的体育冠军也不需要文化程度多高一样,但习武之人,如果要跨界讲文,总还要按照文的标准来。至于诗词书法,南氏均未曾入门,薛先生在这两个领域,也是没有什么判断力的。
薛先生曾介绍我认识过一位中学教师,自称在学校教学生诗词格律,可自己写的诗没一句是讲格律的,薛先生却把这位毁人不倦的老师的大作贴到博客中,供人欣赏。诗为,字为心画,南怀瑾不知书而胡言妄论,其心先就缺失诚敬二字,这样的人,如何能作出好诗、写出好字?
曾子曰:“人之将,其言也善。”南怀瑾在晚年,不止一次说自己的东西都是的,混饭吃的,这是他临终的,是未全泯的体现。薛先生硬要把学问家、家的头衔栽到南氏头上,相信起南怀瑾于地下,也当摇手避让。
通观薛先生此文,逻辑不通,观点,对知识和学问的令人惊诧,实在是一份民粹派的自供状。薛先生既持此立场,从此,他不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敌人。
——知识敌。
薛仁明,学者,著有《胡兰成天地之始》《孔子随喜》《随喜》等。
徐晋如,江苏盐城人,现为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