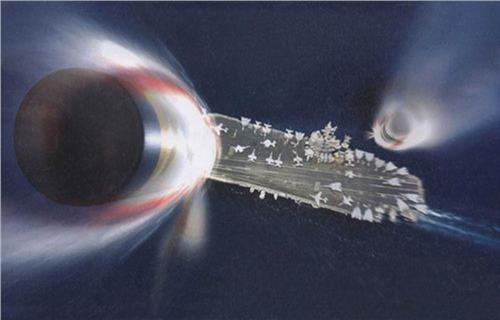他被看作是中国戏剧界的传奇 他却说“我身不在场”他被看作是中国戏剧界的传奇 他却说“我身不在场”
1993年牟森在北京。 肖全 摄
2017年在鼓楼西排练《一句顶一万句》的牟森。 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牟森说这次排《一句顶一万句》算是续借和刘震云错过的缘分。图为彩排照。 李晏 摄
1994年《零档案》彩排图。 李晏 摄
1993年牟森(右二)的《彼岸》首演后。 李晏 摄
牟森作品《与艾滋有关》。 图/视觉中国
牟森被看作是中国戏剧界的传奇,1986年他创立的“蛙实验剧团”是当代中国首个独立民间戏剧团体。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大神布朗》《彼岸》《零档案》《与艾滋有关》《红鲱鱼》等作品横空出世,他也成为欧洲主流戏剧节的常客。
不过,1997年牟森导演的《倾诉》演出后,他从戏剧创作巅峰期悄然隐退。时隔20多年后,牟森与刘震云联手拿出了话剧《一句顶一万句》,该剧将于今晚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与外界赋予的“王者归来”的氛围不同,牟森内心冷静,他觉得对中国戏剧来说,自己是一个身不在场的人。
我很固执 排《一句顶一万句》有点自找麻烦
新京报:这次是什么东西触动你,排这部《一句顶一万句》?
牟森:其实是缘分。我和鼓楼西剧场的创办人李羊朵之前就认识,一开始本来想合作《红鲱鱼》,后来因种种原因没有完成。之后,她说震云哥这部小说的改编权在她这儿,就促成了这次合作。其实,就是两个特别简单的原因,第一就是续借和震云哥错过的那个缘分,第二个就是我太喜欢这个作品了,当年我喜欢在博客写日志,翻看那些日志,还都有读后的感受记录。
新京报: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人物特别多,跨越的时代也很广阔,如何找到小说的主线,把整体结构串起来?
牟森:震云哥的这部小说结构还是很清晰的,整个故事的主线很清楚。上部《出延津记》的主人公吴摩西走出延津的步骤特别明确,比如说改名、改姓,再比如拔刀、掖刀,这几条线都是很清晰的,把它拎出来就行。下部《回延津记》又是通过另外一个人牛爱国,对应地走了一遍,这可不是重复,而是有内在的表达。
这里边有一个人物是我拎出来的,就是曹青娥。当年吴摩西因为丢了曹青娥,这给他生活带来了巨变,走出延津。那么在下部中,曹青娥的儿子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又回到延津,找到了当年出走的那个吴摩西。我等于是把这个东西拎出来,提炼出了“弥留之际”的意象——曹青娥在弥留之际,回想起了自己的前世今生,弥留之际本身也是一个醒悟之际。曹青娥是贯穿始终的一个人物,用她来支撑这个舞台,还是比较结实的。就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跨越了前世今生70年的时间。
新京报:刘震云的女儿刘雨霖曾将这部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不过只选取了小说的下半部。我看影片的时候觉得这有些可惜,你看过吗?对你排话剧有什么影响?
牟森: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到现在我还没看。电影的时间比话剧更短,它的容量更加有限,所以这部小说不管转换成什么方式,难度都是存在的。我本人其实比较固执,就一定要把这部小说的上下两部弄在一起,所以这个难度就更大了,有点自找麻烦。
列夫·朵金30多年前就排出《兄弟姐妹》 我只有佩服
新京报:在这部话剧的发布会上,你说过“要呈现出一部长篇小说应有的容量和品质”,如何去实现?
牟森:咱们拿国外的作品来说,比如俄国、苏联、德国,他们的经典文学作家特别多。我看过留比莫夫改编的《群魔》,连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作家的小说他们都能改编成话剧,而且有很多办法,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而俄罗斯也有这个(改编长篇小说的)传统,比如苏联的前辈导演托夫斯托诺戈夫,他当年就把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用两个晚上演出。我看过这个戏的资料,没有看过视频,等于是他把一部四卷本小说,改编成了两个晚上演出的舞台剧。其实,长篇小说改编成舞台剧在俄罗斯是非常常见的。几年前,莫斯科契诃夫艺术剧院来北京演出的那几个剧目,我最喜欢的一个就是根据布尔加科夫长篇小说改编的《白卫军》。
新京报:去年,俄罗斯导演列夫·朵金来天津大剧院演出了话剧《兄弟姐妹》,同样是根据长篇小说改编的作品。
牟森:那个《兄弟姐妹》我看了,原著小说《普利亚斯林一家》是我上大学的时候读的。其实,这些年我不怎么看戏,去看那个戏就是因为它是成名小说改编的作品。不知道是不是跟星座有关,我对这种结构性的东西特别有兴趣。
新京报:你觉得《兄弟姐妹》改编得怎么样?
牟森:我觉得那个也很好,但是对我来讲,这个戏六个小时的长度来展现作品的容量并不够,那本小说特别精彩。但是,人家30多年前(《兄弟姐妹》首演于1985年)就能弄成那样,我心里只有佩服啊。而且我们看的那版(2015年复排版),应该不是他最经典的一版,但那已经非常好。我非常喜欢。
我希望新作能感动观众 这是一个挺难的标准
新京报:从之前大规模地排戏,到现在再排《一句顶一万句》,大概有二三十年的跨度。你觉得,就排戏来说,你变与不变的地方是什么?
牟森:那个时候排戏很多都是下意识、本能性的东西。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会发现,我最满意的是结构。我喜欢这个东西,也一直在研究,就像我在美院(中国美术学院)开的一门课叫“叙事工程”,叙事和工程是时间、空间两个维度的东西,这也是现在我做戏的一个强大动力。在这个课程上,我都有一些口诀了,比如说命名即主题,主题即结构,结构即意义。
新京报:你觉得《一句顶一万句》大概会是什么样?或者说剧场里呈现出一种什么气质?
牟森:作为这部戏的主创,我给自己设定的这个期待值,或者说我只关注一个标准,就是我希望它能感动到观众。感动是需要指标的,比如内心的感动、眼泪的流露,这其实很难。我觉得人的身体里边,有三种液体很特别,一个是汗液,这跟体力运动有关;跟人的精神有关的有两个,一个是眼泪,一个是精液。所以那种东西,你费(精力)是因为那是通过精神和情感才能出来的。
实际上,这是我给自己设置的一个挺难的标准,我希望能够达到。我一般只要尽力去做,不太去想最后的结果。我做一件事之前跟之后,是不会改变说法的,所以这个戏如果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我不会不认账。
谈不上归来 当年消失只因觉得超越不了自己
新京报:外界都说你是“归来”,那你自己觉得,这么多年没有导戏再回来导戏,是一种什么心态?有跟原来的自己和作品照镜子的感觉吗?
牟森:没有,大家都用归来、回来,我不是回来,我也谈不上回来。换句话说,我本来就没在,怎么谈回来呢?本来我也不算一个在场的人。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那会儿,我就是一个“非正常”的案例,所以我不能说自己曾经在场,也就谈不上回来。我觉得,这次做这个戏主要是因为一个特殊的机缘。说白了,跟这个舞台没什么关系。
新京报:你说没有在场,但通过资料的记录,还有后来的报道,很多非专业人士也是知道戏剧界有“牟森”这号人物。你为什么没有一直做下去,为何就从戏剧圈几乎消失了?
牟森:特别简单,就是当时我觉得超越不了自己了,那个时候做作品,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需要对市场负责,没有销售行为。所以,那个时候做戏就要不一样,要求对自己有超越。现在来说,戏剧更像一个产品,你锁定了你的受众群以后,只要保证这个戏的品质稳定,基本没什么大的出入。但是,作品跟产品是有区别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不懂事,戏做得太多,我属于机遇比较好的,作品出来后很快就能在欧洲的这个戏剧节、那个戏剧节上演,而且很成功。也是因为各种机遇,我做的戏就太多了,我记得那两三年我差不多排了五个戏。如果放到现在,我绝不会这么去做,那是年少,很快就觉着自己超越不了自己了。
新京报:后来你也做了一些跟戏剧相关的事,比如2002年受林兆华邀请担任剧目总监,2003年在广东排了一部抗击非典的戏,这些也都是“不在场”吗?
牟森:其实可以这么说,第一,我从来没有在这个戏剧市场里边;第二,我从来没在院团里边。这两个地方我都不在,所以不能算“在场”。但是,对我自己来讲,上世纪90年代做的一些训练班、舞台剧,包《零档案》《红鲱鱼》《与艾滋有关》等,我自己都喜欢。20多年过去了,快30年了,我自己也是觉得太好了。那几个东西往那儿一放,一个比一个往前跨了一步。后来,当我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就停止了。所以,你要这么一说,还真是不算在场,就没有在场过。
先锋、实验 那都不是我做戏的出发点
新京报:提到牟森,很多人会贴上先锋戏剧、实验戏剧这样的标签,其实你自己却否认先锋、实验这样的词,为什么?
牟森:其实,我也不是否认,只是说它们不是我做戏的出发点。在咱们当下这个语境里边,先锋是一个品牌,然后这个词又具有一些别的意味。对我来说,这不是我的出发点。其实,我的每一个戏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我的戏当时不能卖票,但我大量的戏又在欧美的戏剧节上演出,所以很难去归堆儿。这些戏在小剧场演,在大剧场也演,我从来没有小剧场、大剧场的概念。特别是现在,咱们这儿的小剧场被赋予了更多别的意味,对我来讲,没有这些东西。
新京报:刚才提到《红鲱鱼》没有复演,现在会不会把原来的一些作品再重新排演?
牟森:这几年已经有人谈这个事了,也有人说把那几个戏重新演刚好是一个社会三部曲,也有人说明年是《零档案》上演25周年了。我自己也恍惚,居然25年了。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戏剧改变世界吗?》,我在那里面就说过,我做过的戏剧也好,或者说在戏剧里边发挥的作用也好,或者别的什么,我一点都不关心。我关心的是前因后果,就是如果有人帮了我,或者我伤害了谁,那个原因是什么,我对个人史更感兴趣。我经常把它作为个人史的一部分去梳理这个环节、节点,我对作品不感兴趣。
那篇文章里还提到崔健当年看完《彼岸》后写的那首歌,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当时很久没有听过那首歌了,一听眼泪就上来,泪流满面。我觉得那个戏在今天看也没有过时,当年那三个戏放在今天看都没有过时,活生生的那个力量依然还在。
曾经的我以自我为圆心以世界为半径 现在以世界为圆心以自我为半径
新京报:离开之后的这二三十年,你怎么看中国的戏剧圈,会有留恋的感觉?
牟森:没有,没有留恋。因为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方向,感兴趣的方向有很多。刚好在2000年到2003年那会儿,我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然后,各种事突然来到,我是一个特别不知道在中国实际运行什么规则的人,就是所谓的社会“潜规则”,因为这种东西在学校里没有,只能来源于单位和家庭,我的家庭没有给予我这个东西,然后我又一直没有单位。
所以,那时突然遇到了一些事情后,就非常困惑,就会去想这个人种是怎么回事?当时我也去请教各种老师,然后找到了“历史”这个兴趣,就一头转向历史,长达十年。最后,我任何的困惑都解决了,困惑的来龙去脉也都清楚了。同时也找到了自己最想做的事情,那些年我就在美院做“叙事工程”,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完成一己之愿,能做得怎么样?做多久?我都不知道,也不重要,能做到什么,就是什么。
新京报:在你40岁前后,性格变化大吗?
牟森:大,非常大,比如我不会跟媒体打交道。如果说40岁以前,我是以自我为圆心,以世界为半径画圆,那40岁之后,就变成了以世界为圆心,以自我为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