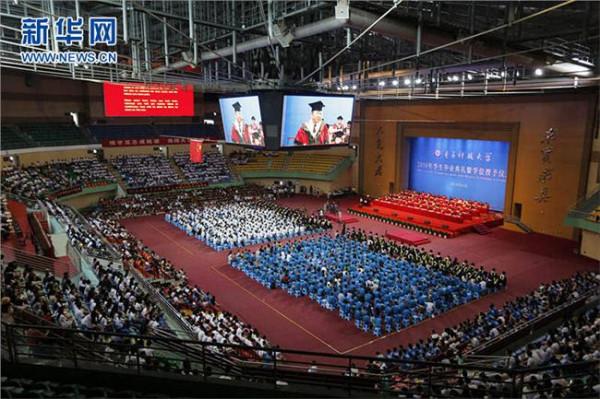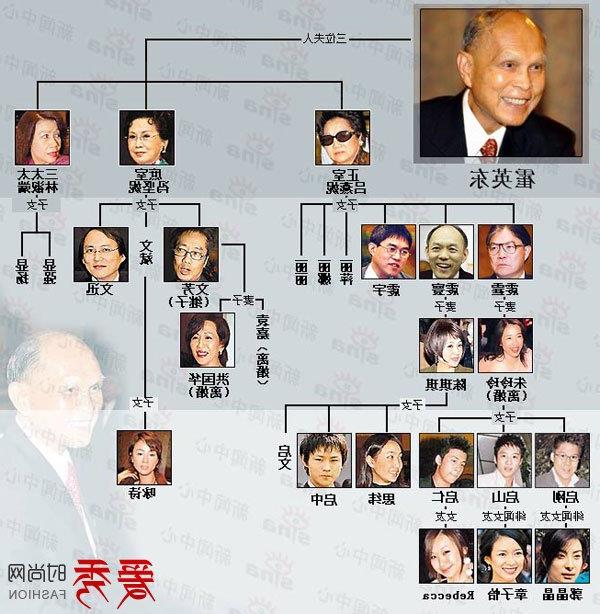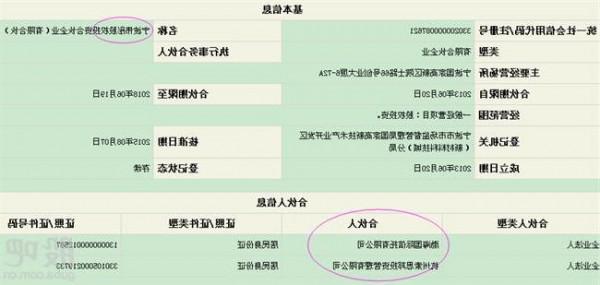荣新江莱顿 荣新江:莱顿负笈正少年(之一:欧洲学院的缩影)
2002年9月8日,当我登上飞往阿姆斯特丹的班机时,思绪就一下子回到了十八年前,回到了我初访荷兰的那段难忘岁月。那时北京还没有直飞阿姆斯特丹的班机,那次也没有像这次一样同去开会的同伴,我独自一人,先从北京飞往巴黎,再转机飞至阿姆斯特丹,对于头一回踏出国门的年轻学子来说,不免有些紧张。
1984年9月至1985年7月那段在欧洲访学的经历,在我这次从北京经阿姆斯特丹到柏林的来回旅行中不断翻滚,勾起一桩久已盘桓脑海的心愿,那就是尽早把1984年以来在海外的读书生活、访学经历记录下来,以免曾经的一切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成为过眼烟云。
我的“海外书话”,自然要从我第一次出国时留学的地方——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说起。
莱顿大学一景
我的所谓“留学”,和当时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精英们的留学不是一回事,因为我是在北大历史系攻读隋唐史专业的研究生的最后一年,由于业师张广达先生的推荐,系主任田余庆先生、书记张万仓老师的大力支持,以及一些热心人的帮助,利用北大历史系和莱顿大学汉学院交换学人的机会,得以负笈莱顿,在那里读了十个月的书。因此,我在莱顿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留学生,也可以说是访问学者。
我在那里只呆了不到一年,当然不是读上七八年书的真正意义上的留学。不过,从我自己来讲,这可真是一次难得的读书、学习的机会,更何况,我当时正在从事古代西域王国于阗的历史、唐宋时期敦煌的历史和中古时期西北地区的民族史等课题的研究,因此奢望能借此机会,不仅收集西方文献中的资料,也能拜访有关学者,调查从中国西北甘、新、蒙、藏地区流散出去的历史文献。
作者在莱顿汉学院门口
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是欧洲著名的学府,这里的汉学已有一百年以上历史,从早年的汉学讲座,到1930年以后成立的汉学研究院(Sinological Institute),我们只需看一下历任汉学讲座教授和汉学院院长的名字:施古德(GustaafSchlegel, 1840-1903)、戴闻达(Jan Julius Lodevijk Duywendak, 1889-1954)、何四维(Anthony E.
P. Hulsewé,1910-1993),就可以知道莱顿汉学在近百年的欧洲汉学史上,带给荷兰汉学的辉煌。
我为能够在这里读书而感到庆幸和骄傲。
更值得庆幸的是,负责指导我的老师是当时的汉学院院长许理和(Erik Zürcher)教授,他以两卷本《佛教征服中国》(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Leiden1972)闻名学界,那时他正研究明末以来福建地区基督教的传播史。他工作非常繁忙,平时大约一个月和我谈一次话,对我的问题略加解答,更多的时候是帮助我联络出访的事情。
许理和与《佛教征服中国》
我记得他的研究室里放着一套《大正藏》,衬托出他研究佛教的背景,虽然他的范围远不止佛教。1996年我第三次去莱顿看望早已退休的许理和教授时,也曾到他原来的研究室,拜访当时已经接替他职位的施舟人(K. Schipper)教授。施先生以研究道教著称,所以汉学院的学生们戏称:“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佛教徒了,我们现在是道教徒了。”
可以说,我在莱顿的那段日子,是我迄今为止最难忘、最美好的一段读书时光,没有应酬,没有压力,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在书的海洋中畅游,特别是可以看到那么多自己在北京找不到的图书和文章。
开始时,我主要是在汉学院的图书馆看书。
图书馆并不大,平时无人,学生要借书时,要先到图书馆办公室叫馆员去书库里找,然后填条借走,还书则是往桌上一放就行了。在这里,我和许理和教授的博士生、曾在北大留学过的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朝夕相处,成了好朋友。
书桌的背后的书架上,摆放着普通书籍,有中文线装书,也有中、日、西文平装本或精装本书。对于我们在书库里阅读的人来说,这些书取用十分方便,我们可以把许多相关的书拿到自己身边对读。书库的中间是一个“库中之库”,里面是有轨道滑轮、可以移动的密集书架,存放过期的期刊和待处理的副本书。
旁边是一间平日上锁的小房间,里面是一些属于善本的线装书和地图、绘卷等,主要是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 van Gulik, 1891-1980)生前收集的书,这些书和北大图书馆的马廉藏书一样,在研究明清小说的圈子里很有名,而高氏所藏不仅仅是小说。
莱顿汉学院内景
汉学院图书馆的中文书当然没法与北大图书馆相比,但是,在北大图书馆不方便阅览的港台杂志,这里却可以随意翻阅,我曾用极快的速度翻检了1949年以后出版的《史语所集刊》等杂志,复印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唐史和敦煌学方面的论文。我还复印到许多散在港台杂志中的陈祚龙先生抄录的敦煌文书。
对于我来说,汉学院图书馆更有价值的,就是西文书刊。固然北大图书馆因为有北大和燕大图书馆的底子,1949年以前有关汉学的西文书并不算少,甚至五十年代困难时期,西文书仍然是无间断地购买,这大概和向达先生担任馆长不无关系。
但六十年代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北大的西文书奇缺,甚至连西文定期刊物,也往往缺少这些年份的。借此机会,我不仅可以通检有关汉学的杂志,如就在莱顿汉学院编辑的《通报》(T’oung Pao),还可以系统浏览数十年来西方汉学或者说中国学的主要成果。
《通报》第1期封面
汉学院图书馆的馆长是从美国来的马大任(John Ma)先生,他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任职时,曾走遍全球,搜求汉学资料。我当时正收集有关敦煌、吐鲁番写本的收藏信息,从他那里得到不少资讯,在与欧洲一些图书馆联络时,也得到他不少帮助。
我时常和他谈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曾从罗马的梵蒂冈教廷图书馆(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复印回一本伯希和编《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Inventaire sommaire desmanuscrits et imprimé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的稿本,因为我当时志不在此,只是找出来翻阅了一遍,并未特别措意。
到1991年我重访莱顿汉学院时,马大任先生早已离开,知道这个稿本的人恐怕不多。当时正在调查明清时期流散在外的中文古地图的北大同事李孝聪先生、正在编辑意大利所藏汉籍目录的京都大学高田时雄先生也都在莱顿,我们一起参观汉学院图书馆。
当我提到这个稿本时,他俩都很感兴趣。我很快凭着记忆,找到了它,他们两位都叹为秘籍。高田先生随后几次到梵蒂冈,据稿本仔细核校原书,终于把伯希和这部遗稿整理成书。我想,如果没有马大任先生的努力,没有莱顿汉学院对这一稿本的收藏,也就不会有高田整理本的出版。
汉学院图书馆虽然是汉学的图书馆,却也收藏了不少有关中亚、西藏的图书,甚至还有更广义的东方学图书。我开始调查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时,有一本可谓是指南的书,即皮尔森(J. D. Pearson)《欧洲和北美收藏的东方写本概述》(Oriental Manuscript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 Survey, Switzerland 1971)一书,我记得就是放在图书馆书库一进门的头一个书架上的,所以很快就被我找到了。
这本书的确给了我很多帮助,不仅提示了敦煌、新疆出土各种语言文献的具体所在,而且我后来查访《永乐大典》,也是从它开始的。
今日莱顿大学校园风光
除了读书之外,我在汉学院图书馆还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荷兰在欧洲是个富有的小国,国人善于经营,且十分节俭。为了节省经费,荷兰政府规定,全国只有莱顿大学汉学院可以买汉文书,而其他大学或政府机关要是收到用汉字写的书,也要寄送到汉学院图书馆收藏。这样一来,就使得汉学院图书馆的书库中留存了大批汉文书刊的副本,而汉学院图书馆中的西文、日文的副本书亦是如此。
马大任先生曾用交换的方式,拿台湾出版物的副本和大陆高校等单位交换汉学院所需要的书,又拿大陆书刊的副本和台湾学术机构交换,他说有一年,没有花任何钱(莱顿大学实行邮资总付制),就为汉学院图书馆添置了不少的中文图书。
我浏览过这些副本书,其中不乏对我有用的书刊,于是和马大任先生商议,希望用低价购买一些副本书。这一想法很快得到汉学院领导的认可,于是我在密集书架中爬梳了一遍,挑选出我要的书籍,当然,我更看重的是在中国更为难得的西文书和日文书。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买书的单子一时也找不到了,环顾四周的书架,还可以看得到的书有:
苏远鸣(M. Soymie)编《敦煌研究论文集》(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sur Touen-houang)第一集是法国汉学界第一本集体研究成果,我步入学界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文字,应是发表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上的《法国科研中心敦煌文献研究组的研究工作》,其中就有关于此论集的介绍,但我却一直没有这本书。
虽然我的那篇小文章,早已为敦煌学界所遗忘,可我当时还是买下了这本书,因为对我而言,它多少有些纪念的意义。
《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在国内时记得只有中科院图书馆有,使用起来非常不便。大概是因为被看作是汉文书籍的原因,汉学院图书馆竟收有四套副本,我得到了两套,把其中一套送给了张广达先生。
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虽然国内早就有郑元芳的中译本,且我所获的这一册并非1931年的初版,而是1970年弘文堂书房的新装版,但是属于限定发行的第279册,特别是图版印制精美,彩图尤其好看,远胜中文本。
《铃木俊先生古稀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出版。铃木俊先生是研究唐史的大家,但我当时之所以买这本书,更重要原因还是在于考虑到1975年这样的年代出版的日文书,在国内一定很难寻找,所以先买下来再说。果然不出所料,国内确实很难寻觅。最近,张国刚先生来信,问我是否有池田温教授的《开元二年十二月河西节度都押衙王文通牒——十世纪敦煌的土地争议之一例》,此文就在这本《论丛》当中。
伯希和与韩百诗(Louis Hambis)合著《圣武亲征录译注》(Histoire des campagnesde Gengis Khan. Cheng-wou Ts’in-tcheng lou)。这本书和我当时的研究无关,除了伯希和师徒的名气外,书中的签条表明是Prof.
Dr. J.J.L.Duyvendak(戴闻达)的藏书,所以很有纪念意义。西方小的专业图书馆往往不存副本,但图书馆员在撤下副本书时,常常把值得纪念的书当作副本处理掉,我后来在巴黎也曾遇到过这样的事。
这本书折合在一起的书页还没有裁开,表明戴闻达根本没有动过,很不好意思的是,我买这本书也真成了纪念品,因为我这次翻开它时,折合的边也还没有裁开。
此外,当时所得还有袁同礼与渡边宏合编《新疆研究文献目录(1886-1962)》、森鹿三《东洋学研究·居延汉简篇》、小野川秀美《晚清政治史研究》等书,还有收载严耕望先生考证唐代交通路线系列论文的若干《新亚学报》等杂志单本。这些书刊虽然没有什么珍奇之处,但却是我获得的第一批值得珍藏的图书,而且大多数是有用的书。
我喜欢莱顿汉学院的图书馆,但我更喜欢汉学院的读书环境。
汉学院是传统欧洲学院式的布局,中间是个大天井,顶部是用玻璃全封闭的,下面铺着红砖,中间是花坛,天井下面摆放着一些圆桌和椅子,老师和同学们可以一边坐在天井里聊天,一边喝咖啡。老师、同学、图书由此在同一个不大的空间里,上课时可以随时从图书馆提取要用的参考书,课间喝咖啡时,可以随便向老师请教,也可以相互交换意见。
作者与南洋史家韩振华先生在汉学院天井交谈
这样的教学效果,比起我们的那种教室里没书,而图书馆又没有老师的情形,当然要好得多。这也使我想起有不少先生都回忆过,陈寅恪先生上课时,总是用个大包裹皮包一大堆书到教室,或许就是因为教室里没有办法拿到书的缘故吧。
汉学院的这种布局,不仅对教学方便,对老师们的科研也很方便。每个老师在自己的研究室做研究时,只需把自己常用的书放在手边即可,其他书可以随时走进图书馆参考。这里的教员不像中国的先生那样自己大量买书,而是充分地利用学院的图书馆。说实话,他们每个人都拥有这个图书馆的每一本书,所以数量甚至质量上比我们自己买的书要多得多。
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的是,汉学院图书借出的书,有明确的归还期限,而且被借走的书的原处,有一个塑料夹夹着纸条,说明该书被谁借走,何时归还,这样急于使用这本书的人可以从借书的人那里找来看一下。
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汉学院的老师也常常把别人赠送给个人的一些图书,捐给本院的图书馆,因为这和放在他自己的研究室里,并无太大区别。我在汉学院图书馆里,就看到我们中古史研究中心寄给许理和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这样一来,虽然没有定性的要求,但每个老师每天几乎都来“上班”,在自己的研究室从事研究或备课,这自然又促进了教员间学术的交流。
我回到北京以后,去拜访了我们中心的主任邓广铭先生,汇报我在外面的见闻。我和邓先生开玩笑地说:“你买这么多书放在家里,是封建式的经营;而人家汉学院,是资本主义式的经营。”
邓先生点头。我接着说:“像您这样知名的权威,自然可以照此方式经营下去,因为宋人的著作您缺的不多,而海内外研究宋代的人,都把研究论著寄给您。可我们年轻人就不可能这样了,既要购买必要的史籍,又要搜集相关的研究著作,要达到您这样的程度,恐怕是相当困难的。”
邓先生说:“我之所以创办中古史研究中心,就是想把研究者和图书放在同一个空间里,让大家每天都到这里来学习和研究。”
欧洲的学院,是知识的渊薮,是图籍的宝藏,也是人才辈出的地方。莱顿大学汉学院,就是一个欧洲学院的缩影。
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