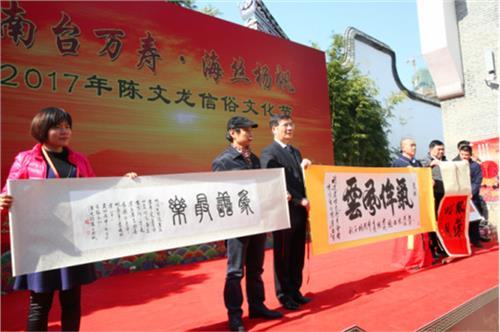万尼亚舅舅剧本汝龙 评《万尼亚舅舅》的二次解构:庆祝无意义
(搜狐文化·舞台特约稿文/娜小眼)此次人艺决意排演契诃夫名作《万尼亚舅舅》,并发声“人艺再不排新戏就完蛋了”,将剧作家契诃夫重又安置在诸多目光下。导演李六乙对文本的二次解构建立在“完全尊重原著,绝不本土化”的理念之上。两百年前的俄罗斯窘境与当代人的困惑殊途同归,然而眼前的万尼亚舅舅却高高在上令一票观众仰颈兴叹望而却步,是喜是悲?
《万尼亚舅舅》是契诃夫的代表作之一,写于1897年。而当时距离自己的另外一部作品《海鸥》演出失败仅有一年只差。《万尼亚舅舅》的立足可否看作是契诃夫的不甘和反抗。同样是小人物的悲剧,对《万》的一般化解读是:用更多的笔触表述了生活的无意义,人生的疲乏和困顿。
故事发生在一座小小的庄园内,平静的生活被教授及妻子的归来打破,一方面万尼亚将教授(自己的姐夫)当神一般供养,却发现教授的平庸伪善,令自己万分绝望;一方面他沉迷于教授年轻美丽的妻子,陷入痛苦的深渊。
而教授的女儿苏尼亚似乎面临相同的困境:她被自己的父亲带来的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负荷压得快要窒息,又深深迷恋着绅士范儿的乡村医生而求之不得。当所有人几近崩溃时,教授提出要卖掉庄园去换取自己自由的都市生活,万尼亚终于拿起了枪反抗,这令教授及妻子不得不离开庄园。
生活似乎重又归于平静,但无止尽的劳累和重荷还未停止。于是最直接的见解“we shall rest(我们应该休息)”的字样被贯穿全剧始终,悬于舞台后方的幕布之上。契诃夫到底要表现何意?在日常看似平凡的对话里和安静的戏剧表面下。
李六乙的舞台清爽干净,从安提戈涅到俄狄浦斯王,演员缓缓穿过舞台,带着形而上的仪式感。《万》剧并不例外:一个空的空间,舞台两侧的进场口和下场口被台上的所有演员“封锁”,演员从开始到结束实行全场不下台,即使文本里人物缺席,所有演员依然在各自的空间里完成舞台动作,即使是暗处一角。
在这样一个密闭的空间里便是契诃夫笔下的庄园,压抑,空虚、漫无目的、惶惶不安,正如所有人各怀心事,空空荡荡又互看不见。这一版的舞美设置淡化了契诃夫的现实主义色彩,以高低错落的白色座椅有序散落而代之以往庞杂的实景,舞台后方正中高耸的座椅,颇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象征,平庸的小人物穿梭其中,观众深谙角色的无力。
舞美背景压抑的围墙扑面而来,仅留矮小的一扇门。
钱钟书先生有言,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李六乙似乎也不打算让这帮无聊的人出去,他残忍的将他们挤在一间庄园里,每日抬头要面对不得的爱情,如今已化为虚妄的崇拜,面对无意义,仍然要带着手铐和脚镣,庆祝这般无意义。






![汝龙书法 [书评文论]关于汝龙及汝龙译契诃夫的不足](https://pic.bilezu.com/upload/8/98/8983b71a1d37cae35d1da38edc2e102a_thum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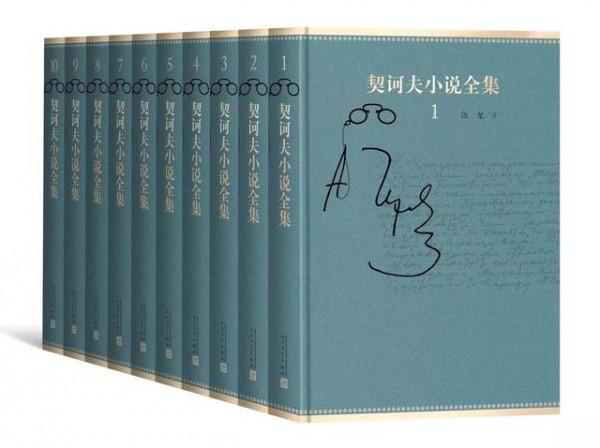



![>复活草婴汝龙 《复活》((俄)托尔斯泰)草婴译 扫描版[PDF]](https://pic.bilezu.com/upload/1/3f/13f3d4a06717bcab2027852a01c219c6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