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简介 卞之琳之妻青林简介
从母亲1952年在《北京日报》发表第一篇小说《名字》,到1988年收官之作,前前后后发表了几十篇短篇小说。1964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圆圆和她的朋友们》,还被译成多国文字。1984年《人民文学》35周年短篇小说选还选登了她一篇小说《怀念》。
母亲是一位非常正统本分的人,正统到不是党员完全按党员的要求去做。文革期间因向党交心而获罪,遭到攻击和迫害。本来就有严重失眠症的母亲,在下放三年期间得了抑郁征,曾割脉自杀,经抢救幸免于难,53岁就病退在家。
晚年她的身体一直不好,我回京时,她就让我帮助整理整理文稿,不少篇什都是她到农村体验生活后写的东西,无论是人物的刻画还是细节的描写都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态。
对于描写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学生的题材,挖掘得也很深刻,充满了真情实感。母亲在文学创作上是下了苦功夫的。曾与母亲在文学研究所共过事的徐凌云教授就曾对我说过:“您母亲很有才气,当时是青年女作家。1958年我们下放到唐山农村时,除了劳动就开会,很辛苦,而你母亲除帮县里写革命回忆录,还写了烩炙人口的《沙河故事》。
”我手头至今还保存着一本母亲的读书笔记,其中不少是学习苏联创作理论和写作体会的。不过也难为母亲了,因解放后一边倒,文艺界的思想改造风起云涌,整风运动不断,光凭热情和才气是不行的,要想发表作品,当时学习苏联老大哥也不乏是一种选择。
出版社多次劝母亲将这些作品结集出版,母亲追求完美,一拖再拖。1983年四川出版社曾希望花2000元为母亲出集子。
心高气傲的母亲一口回绝:“花钱出书?不出了!”。母亲去世后,我曾多次奉读母亲这些清秀的文字,作为那个时代过来人,有的事情很熟悉,有的情节也让我感动。但这些作品已明显不合时宜,都留有深深的时代印痕,正如当时的不少作品一样,现在一印出来就变成了废纸,谁又再去理会它呢?母亲去世前,曾抱憾自已这个作家名不符实,一再想拿起笔来写点好东西。
可他们那一代人,禁锢久了的大脑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可怜我母亲为找寻灵感,曾尝试找她学生帮忙,学着去卖担担面、做红叶书签和绣荷包出售,甚至不辞辛劳地到农村褓母家去体验生活,也写出了不少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我真感谢母亲是一位作家。正因为她是作家,才使我今生不会与母亲错过相认的机会。
母亲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官宦之家,我有五姨八舅,母亲排行老大,天资聪颖,人又长得漂亮,很得我外公的宠爱。我母亲从小喜爱文学,在中学念书时曾参加《平原诗社》的写作活动,受老师芦甸的影响,曾二次离家出走,想北上延安参加抗日,半路都被外公截回来。
我外公主张科学救国,只许孩子学理、工、农,不准学文、史、哲。当成都中学保送我母亲到华西大学文学院,外公坚持不让去,找朋友帮我母亲报考了当时内迁到宜宾的同济大学电机系,由于母亲生性喜好文学,不安心学工,开学不久就转入生物系。
我父亲比母亲高二届,先毕业留校当助教,是我母亲的德语辅导老师。校园里的爱情,是不允许要孩子的,但校园里的浪漫终于有了我。未婚先孕,对于父母在当时所承受的生命之重是不言而喻的。
孩子是要还是不要,苦苦地折磨着年轻的父母,最后母亲讲:“我要孩子。”已经念到大三的母亲为了我,不得不休学。好在我祖父与外公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很平静地度过了这场婚姻危机。
或许是当时大环境的影响,祖父母几乎从未给我讲过有关父母的事情,自幼性格内向的我也很少发问,似乎从小就习惯了无父无母的生活。渐渐长大,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父母年轻时的照片,父母的形象就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台湾绕道回来探亲的人多了,我的天性萌发出寻找父母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几乎找遍了亲朋好友,还向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投过稿。有一次听亲戚讲,母亲没去台湾,可能跟了一个叫文怀沙的人到了北京。没去台湾?在北京?这么多年母亲为什么不找我?内心的难受和怨恨,没有消减我对母爱的渴望;前后四、五年,多方托人毫无结果,也没有动摇我寻找母亲的决心。
我母亲是个敢于追求理想和爱情的人。上华西文学院的理想被外公扼杀了,到上海后外公鞭长莫及,她毅然放弃同济的学业,转到上海戏剧学校研究班就读。1947年有一天,我母亲回家哭丧着脸对父亲说,她真是苦恼极了,因为自己爱上了学校的一位教员,不知如何是好?母亲对父亲毫不隐讳,坦诚得如同小妹妹求兄长指点迷津。
父亲痛苦至极,也矛盾至极,苦思一夜,认为真爱妻子就应爱其所爱,表示她可以充分行使自由意志。第二个周日,母亲从戏校回到家里,屋里静悄悄的,一切收拾得格外干净,就是不见父亲的身影。
她有一种不安的预感,生怕……只见桌上留下一封信。“青,看来怀沙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我们还是好朋友。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辞去教职,应一位同学之邀到台湾新竹化肥厂谋职去了。至于儿子,你就放心,由他爷爷奶奶管着,我也会常去看他。”当母亲读着这封信时,眼泪就下来了。她深知,在上海,女权主义虽然已时兴了二十多年,我父亲也不是一位思想保守的人,但他是死要面子的人,自感在同济是呆不下去了,只好躲得远远的,眼不见心不烦。
母亲则生怕自己的任性伤害了兄长般地呵护她的丈夫。她决定追到台湾去好好安抚一颗失落的心。
这封已发黄了的信封上有父亲亲笔写的“面交怀沙兄”几个草字。展开这封伤痕累累的信纸,可见父亲面对婚变的无奈,“心中塞着许多话,实在说不出来”。对“无可了结的感情”,他理智地表达,竟与新文化先驱们的观念高度一致。
“怀沙兄:我这样称呼你,是完全表示诚意的谅解你,在不可捉摸的感情演变下,以及成全兄及述麟完成某一种有意义事的情况下,我勇敢的毅然答应述麟的要求,我和述麟三年来的兄妹生活,至今已谋得名义上的决定。
愿你们踏上征途,向光明的大道迈进。……”据母亲讲,后来她与文分手时,曾气得把信撕成一条条。因心中的渴望、美丽的梦想和自己的执着,结果都化作了泡影,还伤害了真爱她的父亲,她怎么不恨?但她舍不得把信丢掉,想着有一天见到父亲时再还给他。事后母亲用整张纸把撕成一条条的信纸重新粘贴好,一直珍藏着,“文革”中都没有销毁。
母亲离开《工人日报》一年多又回到了《工人日报》。1952年春《工人日报》介绍母亲到新大众出版社工作,同年秋天转到北京市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组长,后调市文化处工作。有了安定的工作,母亲就想慢慢实现自己的作家梦。
她除完成日常工作外,还坚持学习文艺理论,阅读文学作品和下乡体验生活,陆续写了一些作品。这一阶段她也常想到自己的儿子。正巧天津的二姨来京,母亲说:“毛毛该上小学了。”二姨问:“你不打算把毛毛接回来?”母亲沉默了半天说:“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一个人连铁狮儿(文思小名)都养不活,还送回他上海的奶奶家,抽空还想写点东西,等过几年再说吧。”这一点,也是母亲最难过的地方,二个儿子先后都丢掉了。
北京的冬天是寒冷的,特别是傍晚时分的北京站站前广场,北风打着忽哨,一阵阵地刮起地上的雪粒。我们一家四口,出了站门,雪粒和寒风直往脖子里钻,妻子给二个女儿紧了紧围巾。我看见不远处灯光下站着一位老妇人,端庄清秀,厚厚的黑头巾上已洒了不少雪粒。
不用问,她就是我的母亲了。我上前喊了声:“妈!”只见母亲眼泪就下来了,拉了我的手上下打量着说:“毛毛都长这么大了?”与妻儿见过,母亲就搂着二个孙女说:“我们回家吧。”回家?记得女儿小时候问过我:“家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妈妈就是家”。
到家见过卞伯伯、妹妹,其乐融融。孩子是第一次出远门,旅途劳累,妻带她们先睡去了。潜意识里的“恋母情结”让我全然没意识到自己已是四十岁的人了,就这样整夜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听母亲讲过去的故事。母亲抱着我,泪流满面地说:“妈妈见到你心都化了。
感谢你奶奶历尽艰辛替我抚养了你,我对她老人家深感抱愧。”我任母亲的眼泪沾湿了我的衣襟,尽情享受着迟到的母爱。听母亲谈宜宾李庄校园里美好时光、重庆歌乐山生我时艰难的岁月和辗转上海、台湾、北京感情生活的磨难……母亲端详着我半天说:“你现在的模样和我记忆中的毛毛完全联系不起来了,我觉得应该叫你的大名了。
”母亲搬出已发黄的相册,我们一页页地翻捡失去的岁月。我们看着互换的一模一样的我周岁时的照片,都笑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人高马大的男子汉?母亲忆起往事,问我:“乐生:学校放假时,我还回安庆看过你,一进门就呼着你的小名,可你坐在石阶上,自顾自地唱着‘罗拉’,不喊‘妈妈’。
”我说:“我那么小,哪能记得这些事。”本来嘛,一岁多点的孩子不是母亲带,时间长了对母亲的印象有些淡漠,也是情理中的事。但当时母亲面对自己的孩子把她当成陌生人而特别难过。她说:“临走上大轮,汽笛一响,眼泪就下来了。
”母亲要我从相册里挑几张照片,我挑了三张照片,一张是母亲年轻时在校园骑自行车的照片、一张是抱着我的照片、一张是1947年她和父亲在上海照的照片。母亲说:“你怎么尽挑我年轻时的照片?”我说:“这些都是我印象中妈妈的样子。
”“妈妈老了。”母亲眼中闪过一丝悲凉。是的,岁月的风霜过早地染上了母亲的鬓发,但我觉得妈妈依然漂亮。我说:“妈妈不老。我爱妈妈。”妈妈把我搂得更紧一点说:“孩子,由于妈妈从小立下的志愿,想搞文学,想当作家,因做编辑,后来教书,工作较忙,都是业余时间写东西。
退休后,自己给自己安排的任务是写作,也确实尽了很大的努力,但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写出来。”我说:“我为找到一个作家妈妈感到骄傲。”1988年当我读到母亲发表在《现代作家》第一期上的《雪夜》时,儿子也成了她生活中的原型,怎能让我不骄傲?十二年的耳濡目染,也使我爱上了文学。
回家第二天,妈妈把我和妻喊到一起,慎重地交给我一张存款单说:“这三万元,是我的一点补尝,务必要收下。”我说:“妈,我找到妈,比什么都高兴。我们要钱干什么?”看着妈有点不高兴,妻忙上前劝道:“妈存点钱也不容易。
我们俩都有工作。乐生找妈时就曾说过,若妈生活不好,我们还得承担起瞻养的义务。”可是母亲总想给我们一些钱或帮我们添置一些什么,每当我们回绝时,她就不高兴;若要顺着她,母亲好像心里就好受点。可能我遗传基因里携带有执拗的禀性,往往为此惹得母亲难过流泪。
记得一到北京,母亲就张罗着要带我去买大衣,说什么在北京,冬天没大衣是不行的。我就是不肯跟母亲上街。她见我不愿去,也不睬我,拖着我妻就走。回来,妻对我说:“妈妈在王府井百贷大楼为给您买这件呢大衣,含着眼泪请一位跟你差不多高的营业员试穿合身后才拿回来的。”结果我总是拗不过母亲。母亲临去世前,还是把那三万元的存单由妹妹转送给了我。
作为医生和院长,我的工作是非常忙的,很难经常回去陪伴妈妈。有时信少了,母亲总是盼着我的只考察报告言片语,有时写得多了写得长了,母亲又耽心影响了我的工作和休息。她要我:“善待病人,善待医生和护士,也要善待自己的身体。”
当时安庆到北京还没有直达列车。等母亲的病情稳定后,我乘车到合肥,单位派车接。不知为什么,车到半路突然爆胎了。单位又派了一辆新车,有那么巧事,没行多远又爆胎了,二百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一天。回到家里,我跟妻子讲起这件事,妻说:“妈妈是不想让你回来呵。”果不其然,一周后,我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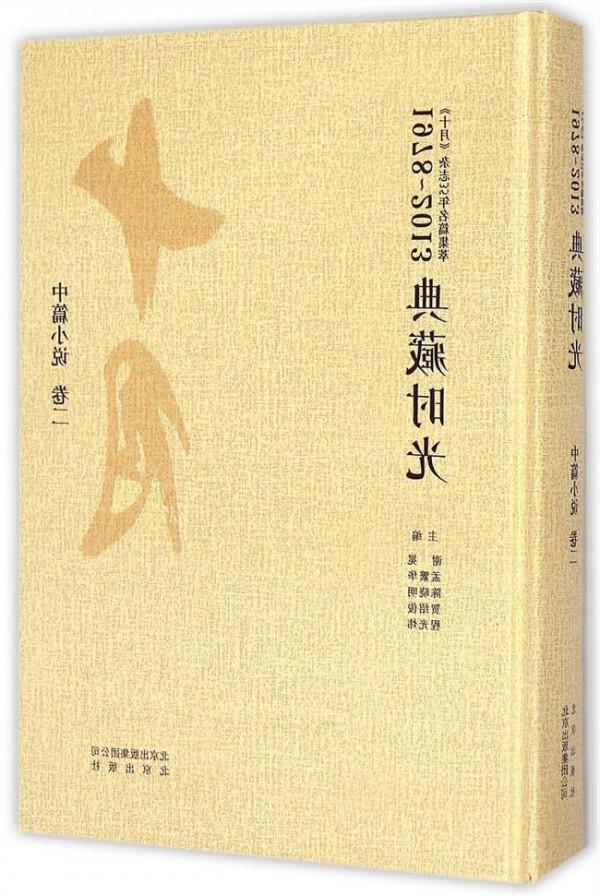
![>张充和和卞之琳 诗人卞之琳诞辰105周年:师从徐志摩苦恋张充和[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f/4e/f4e9b421e83904b95cf27c2217eb8d1d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