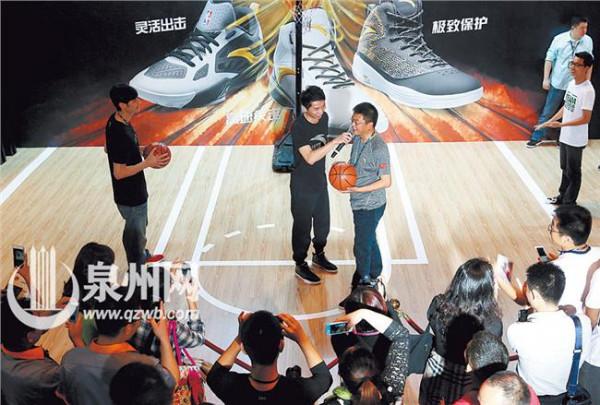居廉国画 在自由与局限之间——由居巢居廉撞水撞粉之法说起广东花鸟画
花鸟并非是中国文人画家所乐于追求的绘画体裁,但花鸟画却是实现笔墨情趣和变化的最可能性画种。广东画人在花鸟画的创作上取得一定成就,但是由于花鸟画自身可能性意义的局限,使得广东美术史不能得到普遍重视。
广东籍画家居巢居廉兄弟继承清初恽南田的没骨画法,创造性地利用撞水撞粉之法对岭南风物写真,在广东画坛产生深远的影响。出现了像容祖椿、李野屋等诸多艺术成就颇高的继承者,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得到,甚至是广东美术史研究者的关注。另有居廉弟子高剑父等人,游学东瀛之地,在花鸟画的创作上实现了对“水”的探索,从而使广东的花鸟画出现了截然不同于北京地域的发展状态。
花鸟画&广东美术
纵观尚未完整梳理的广东绘画史,很多美术史研究者注意到其与传统文化中心的地域差异。传统文化的重镇如京津、沪宁杭地,擅丹青者最为注重山水画。山水在中国文人的笔下富含诸多意味,为文人所崇拜的神,甚至比世俗的伦理道德更超越。
尤其是宋代理学、心学的促进,山、水在中国文人的笔下是神灵和仙人的居所。文人们相信通过绘制山水画可以达到通灵的作用,辅之以冥想可获得超脱。也因为山水文学的创造力,山水画逐渐脱离了绘画而成为性灵的表征。
所以宋元以来中国绘画史的主题就是一部山水画史。其它的绘画门类如人物画,见诸隋唐之前的绘画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很多人认为人物画的兴盛原因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开篇所述之“成教化、助人伦”,并且从现存可考的作品来看也似乎如此,但是亦未免有失更可能深入的论证。
隋唐之前,由于中国绘画理论尚未得到系统总结和阐述,绘画的精神也一直没有能够得到所谓正统文人的承认。人物画之所以能够被接受就是因为其具备“成像”的功能,即其更多是满足了普罗大众的信仰崇拜视觉要求。
“成教化、助人伦”应属于官方的叙述文体,其并没有满足解决问题的要求。相对于山水和人物,第三大题材应以花鸟为重。花鸟画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上处于弱势,这不仅仅因为其没有前两者的精神、教化优势,更在于其装饰趣味过于浓重,与民间工艺太过于接近,以至于很多文人不愿意探索。
由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心在于探索中国绘画所体现的文人精神本质,所以对山水画的探讨最为集中和深入,对于人物画方面,其更多注重于美术史与考古及交叉学科的综合论述,对于花鸟画,则一直处于探讨花鸟画技法、整理花鸟画家生平信息的状态。
之所以产生这种区别,即在于上述三者在中国文化史行进过程中的变化有关。
民国之前的广东绘画史基本上是花鸟画史。很多研究者提出广东美术应该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基于上述的论点看来是难以如愿。之前以为广东一直被北方学者所忽视的原因是传统对广东为“南蛮之地”的偏见,现在看来可更深入来理解了。
诸多学者如朱万章先生等不断发掘出广东人在山水和人物画方面的成就,但是比及传统文化重镇来言,尚不能举之以重要角色。而花鸟画,这种传统文人不甚重视的绘画种类,广东画人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因其过于注重技法探索,而忽视花鸟画与文人气质的关系,以至中国美术史对广东的花鸟画的评价一直处于尴尬的状态。
关于广东的花鸟画史研究,陈滢女士曾做过详细的梳理工作。[]于此种种,笔者不意再做杂陈,仅想从居廉、居巢开始的广东现代花鸟画来谈广东花鸟画对水的探索。
这是因为“二居”是晚清时期广东影响最大的画家。究其原因,大约有三:第一是画好,题材、技法有新意;第二是交游广;第三,弟子多。[[ii]]本文认为,“二居”及其继承者的“撞水撞粉”技法具有十分明显的没骨成分,当属于没骨画技法的变化形式。文章的也将谈及现当代水墨艺术实验的批评词汇延展,给予了“没骨”更为广阔的理论延伸和生存空间。
关于没骨的想象
清初画家王翬在《清晖画跋》中言:“北宋徐崇嗣创制没骨花,远宗僧繇傅染之妙,一变黄筌勾勒之工。盖不用笔墨,全用彩色染成,阴阳向背,曲尽其态,超乎法外,合于自然,写生之极致也。”徐崇嗣为徐熙之孙,其继承和发展了徐熙的“落墨”写法。
徐铉云:“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也。”[[iii]]徐熙的绘画风格因没有作品传世所以无以为证,至于何为“落墨”,研究者只能凭其文字和经验来猜测。但依徐铉所言,徐熙应该还是用笔来绘制花鸟草虫物形,然后以杂彩敷色来表现:只是用线墨色淡薄,通过快速敷色以致于其隐迹于色彩之中。
徐熙自撰《翠微堂记》云:“落笔之际,未尝以傅色晕淡细碎为功。”更可见徐熙并不着眼于谨细的描摹,“落”字在这里有快速之感,有后来之泼墨大写意之味。
相对于当时宫廷中盛行的黄筌一派细致、富丽的审美情趣,喜以新细的笔线来勾勒,然后重点是敷色以微妙生动的工致之作取胜,徐崇嗣在宫廷的表现技巧必然造成新奇的印象。
笔者认为,后学所言徐崇嗣创作出的没骨技巧,其画法和黄筌一路所区分的主要一点在于徐氏不着眼于对细节的肯定,而是表现一种大块面的“写意效果”。宋元时期正值中国文人画审美标准建立之初,徐熙这种偏于“自由”的创作样式正符合文人“自娱”的绘画价值观。
徐崇嗣继承先志,“绘制花鸟画乃全不用墨笔而直接用彩色绘成花卉”,薄松年等先生认为“或系偶然为之”[[iv]]。从现存徐氏的作品来看,并不能合上述之言。可能徐氏创作了一些我们现在认为是没骨风格的作品,但是历史久远,很难得到较为肯定的认证。
历史留下只言片语却没有图像信息可供参考,但是我们获得了这样一个确定的信息,即注重用墨来表现的花鸟画已经开始了有益的探索。这也成为宋元以来文人画审美情趣不断修正的可参考资源。
没骨技法在此时应该并未形成,只是没骨风格的滥觞时期。其实它应该是一种相对于“工笔”的“大写意”画法。现在能够流传下来的书画作品,多是历朝历代宫廷组织创作或收藏的,五代、两宋尤其如此。两宋时期山水画创作注重了皴法的构成元素,尤其是斧劈皴的创新。
在此之前人物画主导画史之时,画家创作用笔一般比较细密,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墨的表现力。马远和夏圭在表现山石时敢于大笔皴擦,甚至是水墨淋漓,将笔与墨的感受率意呈现,这种画法也促进着中国画偏向用笔用墨结合的实践道路。
与没骨说相关的南宋人物画家就是梁楷的“减笔人物”。幸得梁楷有作品传世,即为《泼墨仙人图》等[图1]。梁楷系南宋宁宗嘉泰时画院待诏,画史记载他豪放不羁、嗜酒自乐,号称梁疯子。
不少的研究者在研究酒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将其也作为一个案例,还有就是狂草书和诗歌。《泼墨仙人图》是以简洁的笔墨、写意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个性,尤其是墨色的浓淡变化,非常有趣。没骨作为一种表现技法,在这里也由花鸟画转向了人物画,在一定形态上具备了可比性。
传统中国画最讲求用笔,这不仅因为笔是书法和文字的载体,更在于“笔”有气力和饱含风骨之意,所以关于笔法的理论贯穿于中国绘画史始终。这一状况在明末才发生了转变。白谦慎在以傅山为个案研究晚明书法史时指出了晚明文化尚“奇”的文化观。
[[v]]17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不仅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发生变化,而且整个文化的价值观都在改变。尤其是王阳明的心学统领着16世纪的思想界,他提出“心即是理”,即本心就是通向真理和贤哲的根本之道。
这一强调本心和个人直觉的理论,为晚明的泛神论、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性。[[vi]]此时的书法创作改由传统的帖学向碑学转变,出现了一批“新奇”和“怪异”的作品,形成古拙朴质的审美思想。
审美趣味的自由化,增添了书法艺术的表现性、戏剧性和娱乐性,这种变化在绘画上出现了如陈醇、徐渭、八大山人、恽南田、李鱓等擅长大写意的文人画经典图式创作。至此“写意”的概念才真正得以确立,之前所出现的实践也是后来研究者乐于追述的东西,所以才有了关于徐熙、徐崇嗣、梁楷等人的追踪。
在这里,我们必须弄清楚没骨和写意的关系。没骨是一种绘画技法、写意指的是绘画风格样式。写意一般与写实不同,没骨作为一种技法也不影响恰到好处的写实之作。
写意一般相对于工笔而言,而没骨亦与重勾勒和敷色的工笔相对;试观没骨和写意的作品,它们具有相当大的重叠区间。尤其是徐渭的写意之作,所使用基本都是没骨技法。恣意的笔墨必然不需要勾勒之笔,此时的写意风格就是没骨技法塑造的。中国画史明确以没骨画家著称的画家是清初恽南田。
清方薰《山静居画论》曰:恽氏点花,粉笔带脂,点后复以染笔足之,点染同用,前人未见此法,是其独造。谭天先生曾指出这种创造,就是近代岭南派花卉中常见的“撞水”、“撞粉”之法。[[vii]]恽寿平的作品相对比较恬静,构图、笔、墨皆显得完整而秀雅,没有徐渭那种大胆泼辣的奔放之感。
这与清末广东籍画家居廉居巢的作品有相似之处。至于其技法相似之处,居廉高足高剑父曾著文《居古泉先生的画法》对撞水撞粉有仔细描述:以粉撞入色中使粉浮于色面,于是润泽松化而有粉光了。
在一花一瓣当中,不须着意染光阴,惟以浓淡厚薄的本身为光阴。此与印象派专欲再现以色光的结果暗合。且色中每有带一点粉的成分,尤以紫黄二色含粉较多。有粉则其色显而不焦,又较和谐一点。
[[viii]]从两者的表述来看是极为相似的画法。高剑父在此文指出居廉师从其兄居巢,而“居梅生(巢)作风远宗崇嗣,近仿南田,而造成其独特的风格”。在若波《居巢的画法》一文中对撞水撞粉也有细述:他画的花,华而润,恍如朝露未干,迎风招展,极得花的神采,尤以画梨花的艺术为最好,梨花用淡墨画轮廓,先用薄粉,后以水注入小许,将纸稍微斜倾,粉色一边厚、一边薄,花色特好而有实感。
梨叶则用水墨挞叶,俟半干的时候,又注以水,叶是没骨法的叶,但加了些少的水泽,它的效果,墨色鲜润。
因为撞水、撞粉,画法相当复杂,写得很慢,一日只能画数花数叶……[[ix]]若波在此文又指出,我国花卉画法分两大派,一是勾勒派,一是没骨派,勾勒派是以线条勾勒轮廓为主,没骨派是以色彩点染而无线条轮廓的,居氏的画法,是采用没骨法,偶然也有用线条画轮廓的,这是很少数,它的特点是每画一花一叶,将干未干之际,注入少许的水,或注入少许的粉,使花或叶的边沿,有了很轻微的轮廓线,这轮廓线,不是勾勒出来的,而是撞粉或撞水造成的,居氏对撞水或撞粉的方法,特别的发挥而加以利用。
由此可见撞水撞粉之法并非二居所草创,但是通过二居的作品我们也知道,二居的确熟悉掌握和使用这种没骨技法,并将其发扬光大。
但是由于这种技法所造成的写真效果,使广东花鸟画家在一个时期都在追求形,而没有将精力投入到题材和趣味的创新,使这些优秀的作品显得保守而缺乏创造力,局限了广东花鸟画的发展。
撞水撞粉的继承与延展
在朱万章先生《居巢居廉研究》专论中,考证认为居巢在道光中期流寓广西时的可能问画于江浙籍画家宋光宝[图2—6]和孟觐乙。而宋孟二人从广东省博物馆藏的少数作品来看风格是细致和工整,居巢早期的作品也颇为工细谨致,而后期作品风格兼工带写,撞水撞粉的绘画技法也成熟起来,朱万章先生通过比较认为其晚期作品已能“极得恽南田之精髓”。
居廉画学的主要成就即是将撞水撞粉发展到恣意控制的程度,现藏于东莞市博物馆的《岁朝清品图》[图7],显示了居廉娴熟的绘画技巧,画面轻松而不乏工致。
同样藏于东莞市博物馆的《绣球小雀图》[图8],使用了最为典型的撞水撞粉技法,控制得当的水和色墨在纸面上留下偶然而有趣的痕迹。[图9—11]由于居廉的弟子门人众多,所以在岭南地域有一大批画学后辈继承了这一技巧,撞水撞粉在广东甚至有“居毒”之称,以此也可看出这种没骨技法在广东花鸟画发展中重要位置。
其中如高剑父等更能在中国现代美术史独当一面,更使居廉的名气大增。
高剑父潜心临习居氏此没骨技法,通过数年的基本功训练,使撞水撞粉一法在岭南有了大批的继承者。高剑父后来游学日本,倡导所谓折衷中日两国画风的“新派画”,后来的研究者多认为其“中”的基本就是居氏的画风。当然在高剑父绘画生涯的后期,他也去印度等南亚地域考察,亦准备研临中国古代书画传统,但是事实上高剑父前期行迹画坛的根就是居氏绘画。
据李伟铭先生论[[x]],“二高一陈” 后来形成的画风,主要受到日本竹内栖凤、望月金凤、桥本关雪、山元春举等京都系画家的影响,这些画家皆是日本当时鼎新的倡导者。
尤其是竹内栖凤致力于折衷日本画和西洋画,通过对柯罗绘画的研究,创作出《晚鸦》[图12]:在富于东方特征的水墨挥洒中,融入了西洋的光影效果……这种近似当下我们热衷于探讨的“水墨实验艺术”,是不是也可被认为是“没骨”的技法风格呢?李伟铭先生认为对高剑父为首的“新派”画家更具吸引力的乃是日本画家横山大观致力于用色彩表现空气、光线的“朦胧体”。
这种“朦胧体”的绘画近似于中国传统绘画的泼墨大写意,其更多注重对于“水”的使用。从事绘画实践者尤可感知此点,在书写和绘画的过程中加入水的剂量能够调节墨色的变化而后获得各种效果和肌理。
明末以来文人画理论成熟,对“墨”的发现和理解逐渐与笔取得相等的地位。传统的笔体现作品的力道,而墨使绘画和书法具有了“韵”。但是关于“水”这种调和角色一直没有受到个体论述,可能是因为它与墨无法区分所致。
横山大观的“朦胧体”使用大量的水来淡化墨色,使画面处于一种稀薄的透明状态,最适宜表现雾气和光影,这远非西方油画所能塑造。高剑父及其弟奇峰,另有陈树人并称“岭南三家”,他们都擅用色彩或水墨渲染,以此来制造朦胧的气氛。
这种渲染使原本生硬的轮廓线淡化,也统一了整体格调。其实这种加水产生浅淡墨色的创作技法是否是没骨呢?在这里毛笔没有了笔的特征,其仅仅是实施的工具而已。而当时的中国画正处于一种论争的状态,北方文化重镇更潜心于对传统的守望,尤其是京津地区的画家虽然也着意于探索笔和墨的关系,但是没有如高剑父这般如此使用水来营造画面气氛。
所以高剑父在不经意间提前发现了水的作用,这种绘画技法笔者以为应当属于没骨一路。
中国画自古至今都在使用水,但是使用的目的和程度不同:更是因为时代的审美观念束缚着对于“水”的探索,所以直至今日,“水”、“墨”艺术才开始自由、独立开来,追求现场感的行为水墨、追求视觉效果的痕迹艺术纷纷出席。
这种有水和墨参与的艺术,无传统对“骨力”的崇拜,是中国画的继承,或者是颠覆?其实这种颠覆在明末清初就已经得到很好的体现,只是当时的泼墨大写意还追求形和神,而如今的水墨实验艺术追求的仅仅是行为的快感,追求一种所谓的探索意义。
高剑父学习了这种“朦胧体”的绘画技法,与其在居氏门下学习的撞水撞粉有相似之处,可谓驾轻就熟。但是高剑父的实践经历并非如此顺利,其不断受到注重用笔和用墨的传统派的批评,并且高剑父处于一种先行探索者的状态,并没有合适的理论能够支持他的尝试;更由于其有抄袭日本画的嫌疑,作品所受到的诘难可想而知。
高剑父后来走向了回归传统之路,也逐渐放弃这种对水和墨的尝试,倾心研习用笔技法,状况可见一斑。高剑父弟奇峰,受其在留日之前的绘画影响较大,创作了不少撞水撞粉技法作品,其广收门徒,其弟子赵少昂将此技法习得在香港地区传授。以至现在仍然有人学习和探索。
居巢居廉的作品面貌,与宋代宫廷花鸟画有颇多相似。二居并没有抛弃中国传统的笔和墨,他们的创作基本上是结合以撞水撞粉之法来取得“写真”效果,并非一味的撞水撞粉,并且据笔者资历可见,实际上二居撞水撞粉的作品数量并非很多,而且主要用于如梨花、荔枝、树叶等位置。
二居是以娴熟的技艺,通过对偶然效果的恰当控制,获得恬静华润的视觉效果,自然在岭南地域取得瞩目的成就。继承其绘画技法者为数众多,但是大多控制得当,显得工整和细致,并没有如高剑父及其跟随者的豪放与恣意。居廉弟子众多,其中取得画学成就者亦大有人在,其中容祖椿和李野屋的作品呈现出没骨的气意颇值得提出。
容祖椿(1872—1935),字仲生,号自庵,晚号园叟,广东东莞人。其父亲的朋友张惠田介绍他跟从居廉学画,朱万章先生考证容祖椿为居廉中期弟子。其幼年便聪慧好学于书画,在居廉门下时能“久侍古泉丹青笔砚间”[[xi]],故“古泉每于人前称道之”[[xii]]。
在居氏门下期间结识同窗伍懿庄,伍懿庄家境富裕,藏有不少的书画,容祖椿得以观摩众多名画。更有伍氏戚友曰太平沙孔氏、旧豆栏余氏、二十甫苏氏,皆富藏书画,容祖椿获得研究古画的机会。容祖椿的作品清丽干净,但一直以来鲜为人所知。[图13—17]
李野屋(1899—1938),号尘外,野仙、荒山,番禺沙湾司渡头乡人。李健儿《广东现代画人传》言其“耽吟咏,学画通古人意,习花卉草虫,远法恽南田、陈白阳,私淑居梅生古泉兄弟,山水略仿倪云林,体貌清瘦,字如其诗,诗如其画,画又如其人之秀。
”[[xiii]]李健儿记述了李野屋曾“戏绘花卉草虫伪古泉名印,纳典肆,押钱得高价如居氏真迹”。李野屋作品风格较二居显得更为恣意、雄壮,而不乏情致和工整。在表物时用笔、敷色时更饱满和秀雅。岭南美术出版社在1984年曾出版《李野屋花卉册》,可使我们对其有更直观的了解。[图18—27]
朱万章先生在《居巢居廉研究》的结语中谈到,居廉作品因其清新的风格、娴熟、具象的写生技巧、雅妍的视觉美感,而备受人们推崇,尤为难得的是不同层次的人——不管是文人墨客,还是樵夫野叟,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市井俚俗,都能在他的画作中找到自己所好。
据说到了晚年,画名日盛,求画者踵接,居氏无奈只好找人代笔,为后世鉴定居氏作品者提供了很多值得玩味的课题。他的画风在当时影响极隆,有论者称其为“隔山画派”(或“居派”)。
光绪末年,除居廉的拜门弟子外,在广东学居派的也极多,到处可见撞水、撞粉,花鸟草虫,很多画家徒得其形而失其神,流于刻板,一时流风所至,画风萎靡,故又有“居毒”之称,更受到一部分文人画家之攻讦。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居氏画艺之魅力。
[[xiv]]居氏及其创立的撞水撞粉技法,也是广东现代花鸟画史的主要部分。相较于同时期花鸟画大家齐白石雄健烂漫的画风,追求活泼和生动的趣味,居氏及其弟子的画风倒是显得有些保守,这也是当时广东花鸟画的现实面貌。
由此延展出用水来参与绘画得过程,逐渐成为广东地域花鸟画的特征,并且花鸟画一直是广东画人热衷于探索的画种。其实花鸟画一直是中国画笔、墨更新率最高的画种,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抑或是“写真”还是“表现”,花鸟是一种极富趣味性和探索性的题材。广东地域花鸟画创作的“没骨”因素,颇多论者认为其与广东地域的气候和风土有莫大关系,笔者亦认同。
余论
“没骨”的概念在整个中国画行进过程中从探索到审美认同经历了漫长的准备和等待,由于其模糊性的所指,所蕴含的意义必然获得延伸。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没骨的元素确实主导和实现了中国水墨艺术的“现代化转型”。在广东地域取得瞩目成就的撞水撞粉之法,现在看来正是这种变化的中间状态,尽管当时的画家们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对水的使用是特征,也拓展了没骨的形态,使其具有了更为广义的研讨观念。现当代水墨实验艺术将中国传统的笔墨放置于更广阔的空间,由于艺术家要控制更为巨大的画面,笔在行走的痕迹感越来越强,更由于艺术家不能够将笔划定置于一己的活动空间,可以说对水和墨的敏感更多替代了笔的存在感。
当水和墨确实在主导画面之时,线条感消失。当此时仍然以写意来概括时必觉得概念不够涵盖力,没骨水墨艺术正处于一种勃兴的时态。
[] 陈滢《广东花鸟画流变(1368-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
[[ii]] 这是李伟铭先生为朱万章先生著《居巢居廉研究》所作的序言,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10月。
[[iii]] [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四,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2005年11月第3次印刷,第94页。
[[iv]] 薄松年、陈少丰、张同霞《中国美术史教程》,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179页。
[[v]] 白谦慎《傅山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4月。
[[vi]] 同注5,第10页。
[[vii]] 谭天《中国美术史百题》,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5月,第345页。
[[viii]] 高剑父《居古泉先生的画法》,载于《广东文物》1941年,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出版,第696页。
[[ix]] 若波《居巢的画法》,载于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编《艺林丛录》第三辑,1962年,第81页。
[[x]] 李伟铭《图像与历史——20世纪中国美术论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87—89页。
[[xi]] 李健儿《广东两画人:黎简与居廉》,载于《广东文物》,中国文化协进会刊行,香港西南图书印刷公司承印,中华民国三十年出版,第700页。
[[xii]] 李健儿《广东现代画人传》,香港:俭庐文艺苑,1941年,第5页。